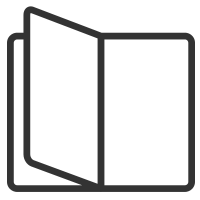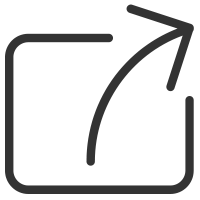满族民俗:疙瘩头烧炕,一宿热到亮


主编 | 孙树发
选自《长白山民俗百怪》
老 头 歌
俺们村东头,
有个老刘头;
头戴破帽头,
身穿棉袄头;
腰捆绳子头,
手拿大斧头;
脚穿乌拉头,
捞个爬犁头;
来到南山头,
去打疙瘩头;
回到家里头,
烧个热炕头。
这首《老头歌》,在关东山里家喻户晓。讲的是关东山里的小老头,上山打疙瘩头,烧热炕头的故事。

关东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
关东山里人家,冬天猫冬时,习惯吃两顿饭。下午三点多钟吃完饭,到晚上睡觉时,烧火做饭烧的那点火,炕就不怎么热乎了。睡到半夜炕就巴巴凉了,非把人冻醒不可。
防止冬夜炕凉的唯一办法,就是睡觉前架把火烧烧炕。
烧炕最好的柴禾,不是二劈柴,也不是大木 子,而是疙瘩头。
民间有句俗语,疙瘩头烧炕,一宿热到亮。
真是不假,惟有疙瘩头子烧炕,一宿热到大天亮。
疙瘩头子烧炕,不像毛柴烧炕,忽拉着起来,热一阵,不长远;也不像二劈柴和大木 子烧炕,火硬把炕烧得滚烫,不能睡热炕的人,被热炕烙得总翻饼,睡不着觉。
疙瘩头子烧炕,炕热得温乎,一宿热到大天亮,而是越到天亮越热乎,热得不烫人,睡得特舒服。
关东山里人家,每家有个柴火垛,还有一个疙瘩头子垛。柴火垛是做饭用的,疙瘩头子垛,是冬天烧炕用的。
关东山里人家,大部分都睡对面大炕,疙瘩头子烧炕,从炕头热到炕梢,整个大屋子夜里都是暖暖的稀罕人。

疙瘩头子烧炕,也特省劲,做完饭填上一炕肚子就不用管了,让它自己慢慢着,不起火苗不能把疙瘩头子一下子烧了,慢火不断,一直烧到天亮。
疙瘩头,也叫柞木疙瘩。不是所有的柞木都有疙瘩头。胡柞没有,青冈柞才有疙瘩头。也不是所有的青冈柞树下有,特殊情况下才长疙瘩头。
青冈柞树一把多粗割下后,它从旁边丛生,越割根部长的疙瘩越大,年年割,年年长,长到一定程度,疙瘩头不再生长,开始渐渐腐烂。这时,手拽细枝头,用斧头轻轻一敲,大疙瘩头就打下来了。疙瘩头是这么打下来的。
打下的疙瘩头子,连细矮的枝条一起,不好装爬犁,不要枝头,只把疙瘩头子用爬犁捞回家。
早年的关东山人家,谁家有大柴火垛和疙瘩头垛,谁家就被称为“根本人家”和“正经过日子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