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书信中的水晶、唐文标
 2021-04-26
2021-0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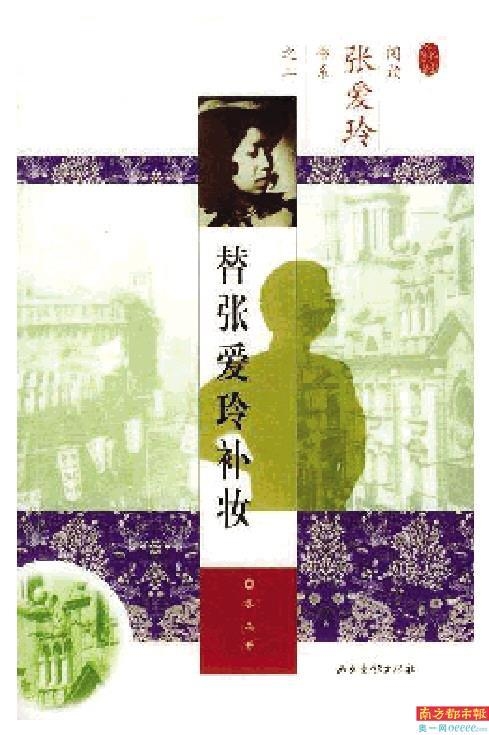
《替张爱玲补妆》,水晶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21.00元。
□ 张宪光
去年九月,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的往来书信集被编为《纸短情长:张爱玲书信集1》《书不尽意: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以下简称《书信集》)二巨册问世了。这书不仅让我们对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及其与宋氏夫妇的友谊有了更具体、深入的了解,其中也有很多猛料,臧否时事,月旦人物,煞是好看。张爱玲在公开场合很少“发恶声”,有古风,看她给胡兰成的回信,决绝的态度也以冷静平淡之语出之,不曾撒泼开骂,私人场合则往往很犀利;宋淇是文弱君子,打起笔仗来却不含糊,像个“病关索”,在人情世故方面比“祖师奶奶”老道得多。“张迷”们向偶像致敬的言论比较常见,张爱玲如何评价他们却不多见,这里姑且将《书信集》中有关水晶、唐文标的部分摘出一部分,想对了解作者、代理人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1
台湾最著名的“张迷”之一——水晶先生是很自负的。他在《为张爱玲补妆》的序言中说:“说一句不够谦虚的话,如今海外若有学者专家讨论张氏的作品,没有不援引上列这两本书上的心得意见,尤以第一本《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为最。”事实是否如此姑且不论,张爱玲对他这本书就很看不上。以前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张爱玲的态度,有了这两册书信,一切都很清楚了。
先拿那本水晶引以为傲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来说吧。宋淇对这本书没好感:“这两天有人借了一本水晶论你的书给我们看,听说他考博士论文失败,心境很坏,下笔火气很大,得罪了不少人。他这本书是典型的研究比较文学而走火入魔的作品,不知你有没有心机从头看到底?”(1975年1月9日信)这本书的确“火气很大”,对前辈名家几乎都是恶评,钱锺书被说成“雀儿捡高枝飞,鸟瞰众生相对高级势利作风”,郁达夫“形容猥琐”、文体“矫揉造作”,如今将这些话拿来形容这本书倒挺贴切的。张爱玲回信云:“姚宜瑛来过许多信,我也是因为不愿意与水晶的那本书在同一个地方出版。书只翻了翻,乌烟瘴气看不下去。‘走火入魔’是的评。”(需要注意的是,这封信被误编在1974年1月17日,恰好早了一年。)一年多以后,宋淇还说唐文标骂张爱玲等人没有社会意识,水晶“用一套新文评的jargon,什么象征、神话”捧她,“二者都莫名其妙”。这大概主要是指向那篇《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神话结构》。水晶生吞活剥,用“神话结构”来解读《倾城之恋》。过了没几年,这些文字害得水晶不得不自我解嘲:“西方批评界,也多的是‘读过了头’的人物,将福克纳、乔伊斯、或者亨利·詹姆斯倒过来读,弄得这些作家,个个变成了《封神演义》中三头六臂的哪吒,仿佛他们创作的时候,是一架复杂的电子计算器,而不是血肉之人。老实说,连‘下走’用这种所谓西方皮毛法则去剖析张爱玲,有时候都会不知不觉,犯下‘读过了头’,或者‘读昏了头’——有位香港文友,直陈这是‘脑子里出苍蝇’——的毛病。”他曾将亨利·詹姆斯《仕女图》与《第一炉香》进行过比较阅读,尚有见地,可是二十五年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两篇作品“不能(也无法)比”。可见用西方的批评行话来解读中国的作品,虽然常常会有一些新发现,但究竟是一件危险的事。
一个人所受的训练,常常让他采用不一样的角度看世界,但也容易将世界窄化,只看见他想看见或者那些理论书籍让他看见的东西。虽然对自己使用西洋批评技巧解剖张爱玲作品的方法有一定的自省,但是水晶先生还是不自觉地运用这样的方法,反复在张爱玲笔下每个细节寻找“微言大义”。《色,戒》发表以后,他写了篇《生死之间》,尚无大谬。可是在“补遗”中,一则把开头的那个场景当成“在魔窟中刑讯王佳芝的一幅残酷写真”,再则把“蜀腴”川菜馆当作“蜀狱”的双关,“影射胜利后一网打尽,统统下狱”,“挤不下”是骂重庆气量小。虽然用的是问号,也有点想象力过于丰富了,西方的象征与反讽理论还是在那里公开地或隐隐地作祟。书评发表以后,水晶两次给张爱玲写信表功,说《色,戒》只有他懂,恐怕宋淇、夏志清都不懂。张爱玲给宋淇写信说:“《联副》上水晶的《色,戒》书评看得我呲牙咧嘴,真是宁可没有。看了想提前写我那篇《色,戒》的,再一想不行,他会又再写一篇,像关于‘药转’一样的没完了,末了一篇无聊得瞭都没瞭一下。”(1978年5月26日信)宋淇的回信也说“又是好笑,又是心酸”。
张爱玲对水晶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觉得那是自己的一点老本,有人制造些热点总是好的,同时又觉得他是“所有认识的最多疑的人”。水晶在报上写文章,说张爱玲推说没看过《肉蒲团》,不给他的论文提供意见,张爱玲去信解释,《肉蒲团》不像《金瓶梅》那样常见,“听见是李渔著,就没去费事找来看”。(1983年8月7日信)但还是介绍他与宋淇见面,二人一见之下,相谈甚欢。宋淇说:“凭良心说,他对你除了崇拜之外,还非常关切,世界上难得有这样的人,可能他的好意令受者吃不消,但为了你,我觉得有敷衍他的需要。他为人很健谈,……为人倒也直爽,口气中对其他文人都不怎样恭维,但也没有发表任何自大狂的言论。”(1983年9月18日信)也就是在这一年,张爱玲开始了她的“抗蚤”传奇,居无定所,不断迁徙,而水晶稍后在洛杉矶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教席,开设了“张爱玲作品选读”课。1985年3月之后,宋淇有四五个月失去了张爱玲的消息,非常焦急,于是向水晶求救,希望他可以就近联系,提供帮助。宋淇随信附上了张爱玲信件的一部分内容,在没有告知各方的情况下水晶写了那篇《张爱玲病了》,征引了两人信件的原文,一石激起千层浪。邝文美的信上说:“这次看了水晶那篇文章,Stephen和我都难过到极点,他自知闯了祸,懊丧得无法形容,这两天寝食难安,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我一边埋怨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大错,一面担心你不知失望而气愤到什么地步。”(1985年9月27日信)次日宋淇作书,回顾此事,自责不已:“我对他的看法是以前一直不得意,有怀才不遇之感,所以时常有牢骚,而且有点自卑感。这几年他总算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觅到了教职,同时写文章和公开演讲也受到欢迎,可以说是扬眉吐气,以前的不安全感理应一扫而空。何况我同他做过一次长谈,他既受过博士训练,理应对运用资料有所认识。(这是我单方面的自解之词,一个人的天性如此,积习难改,对他认识错误,完全怪我不识人头。)”作为超级“张迷”,水晶想的是快速做出一个“独家报道”,分不清什么是个人隐私,显得幼稚与自私,而宋淇夫妇作为全权代理人想的是如何保护张爱玲。
张爱玲忙于“抗蚤”大计,对此倒是没放在心上,轻飘飘地说道:“如要广播,乃可告诉水晶。”
2
唐文标是一个“特别”的“张迷”。一般“张迷”立足于追捧,唐文标立足于批判,是“黑粉”。
唐文标是数学系教授,交游广阔,不治产业,人送外号唐大侠,却靠文学批评名噪一时。这个人精力太旺盛,对现代戏剧不满意,对台湾历史的研究不满意,对张爱玲不满意,这里一枪,那里一炮,喜欢严肃地捣乱,惹得大家都不开心。他说,好的地方自然要赞扬,但真正的批评“不应是盲目乱捧,尤不应是狼群蝇党的一味推崇”。这本是常识,可是真正敢于打破文苑一团和气的人很少,唐大侠不管不顾,兀自傲然前行,一通乱枪放过去,林噪鸟飞。他很早就开始读张爱玲的小说,中学时代买到的多是盗版书,读后也未曾放在心上,1972年回台北后才开始起意研究张爱玲,或许还受到了水晶那篇访谈的影响。他既是张爱玲佚文最早的、系统的发掘者,也是比较严肃的批评者,但他非要将所收集的集外文付梓出版,给张爱玲添了不少堵。
1973年起,唐文标写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还将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盗墓出土,在当时的台湾文学界引起了一阵小轰动,夏志清等人都很关注。宋淇给张爱玲写信说:“‘盗古墓’的人,再加上水晶和唐文标的瞎起哄,把你弄成一个大热门。……可笑你动也没动,经我稍微写两封信,就此其门若市,真是大转其运了。”(1975年9月11日)。可是宋淇高兴得太早了,没想到唐文标趁着《张看》的发行也“兴风作浪”:“听说唐文标出了一本《张爱玲杂拌(碎)》,我正想托人去买。这次叶珊来港,罗青、余光中、黄德伟等聚在一起,拿他大骂,说他对外总说自己是数学专家,其实是个三流大学的助理教授,拿不到tenure(教授终身职),口口声声说爱国,回国服务,瞎发议论,对别人的诗和小说尽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提起来莫不深恶痛绝。水晶虽荒谬,到底还是念文学的。”(1976年7月7日信)过了不到一个月,书到了:“唐文标的杂碎我买了一本,真是杂碎,而且他一脑门子小说必须为国家社会服务,……承他在迅雨一文后,云见到林以亮文中说迅雨即傅雷,尚待考,我想你再考也考不出来,告诉我的是迅雨本人。书的tone大致上还算客气,因为他对白先勇和其余各人也不满意。”(1976年8月2日信)张爱玲对此似乎不放在心上:“唐文标的《杂碎》早寄来了,我那几天不舒服,没下去拿,已经耽搁了,就没退回。唐同时寄了本《今生今世》来,我只翻了翻,看这次出版有没有添写点关于我的。添了些,我也没看。”(1976年8月15日)《张爱玲杂碎》这个名字让人很不舒服,不过唐文标没有恶意,因为他自己也出了一本《唐文标杂碎》,只不过格确实不高。宋淇写了一篇《唐文标的“方法论”》,毫不客气地批驳了这位数学家不够精密的方法论。
令人惊讶的是,唐文标打算将盗墓出土的张爱玲旧作据为己有,公开出版,委实让张爱玲、宋淇恼怒,也让他失掉了朋友们的同情和支持。唐先是重版了《杂碎》(改名为《张爱玲研究》),接着出版了《张爱玲卷》以及《张爱玲资料大全集》,虽不违法,却是悖理。他给庄信正的信里说:“张娘大怒,唐某大乐”,无赖相十足。张爱玲收到庄信正的信,请宋淇想办法(1982年8月2日信,《书信集》误编在1979年,此类误编时或有之),宋淇也说此人“居心不良”,只能打起精神与之周旋,抢先在报上将部分作品重新发表,然后拿去重新登记。唐文标当时已患癌症,有些一意孤行,非要将这些破烂公开,或许也趁机捞些医药费。宋淇说:“唐生病要医药费不成其为excuse,如需要,请大家帮忙,连我也会解囊,虽然我不齿其人。”(1983年3月20日信)十一月份的信中再次写道:“此人无耻已极,文章没有一处无毛病,应该入文章病院,而丝毫没有自知之明,还自己觉得为中国文学史创造了奇迹,真是天晓得。”由于几篇作品已经预先登记,《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涉嫌违法,被迫收回。唐氏在搬运剩余书籍时病情发作,于1985年6月去世,这幕闹剧才告结束。南方朔为纪念集作序,最后也提到唐的矛盾:“他对抗日期间的孤岛上海缺乏理解,因而难免用错了标准。不过,由张爱玲其实也反映了唐文标的矛盾,那就是他一方面爱张爱玲至极,因而发动了一切朋友的力量来寻找张爱玲的断简残篇,编成《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没有这个大全集,我们对她的作品和时代就无法像现在这样熟悉;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张爱玲铺陈出俩的那个黑暗社会充满了痛恶,遂将痛恶转嫁到了张爱玲身上。”这个评价大体公允。
3
水晶与唐文标属于两种批评家,一采仰视之立场,一采卑视之立场,均非批评家所应有。仰视让人目盲,卑视让人失真。水晶说张爱玲的房间里有许多强光灯泡,是为了便利换行头,在穿衣镜前打量自己,所谓“顾影自盼”,简直是昏话。张爱玲晚年皮肤病恶化,几乎没有治疗的好办法,只好照强日光灯,但晒多了又伤皮肤,对耳朵也有害,进退皆难。水晶的猜想真是太罗曼蒂克了。这种情况下,批评者小于作者,以小窥大,恐怕很难入其堂奥,要被作者笑话了。卑视常常使批评者占据有利之位置,至少可以在精神上与作者处于平等之位置,从而较为客观地言说利弊。但是倘若暗藏了先入之见,便容易将作品变成了自家观念的奴婢,欲向左便左,欲向右便右,完全任批评者打扮了。看起来批评者大于作者了,其实还是小的。连水晶都说,唐文标那一套社会功利论要作者成为先知,给社会开出药方,这种文学的“器识”太偏狭了,幸好如今持这样观点的作者、批评家和读者都不多见了。
回过头来看,我们需要的还是傅雷那样切中要害的批评。张爱玲虽然在《自己的文章》里一再辩解,但她后来如此看重语言和细节的精确性,凡是要写的东西都要亲眼看过或者做过仔细的调查,很少再使用文言套话,毋宁说那篇评论的确影响到了作者的写作,而这样的例子是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