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嵱覠评《沈曾植书信集》|海日神锋照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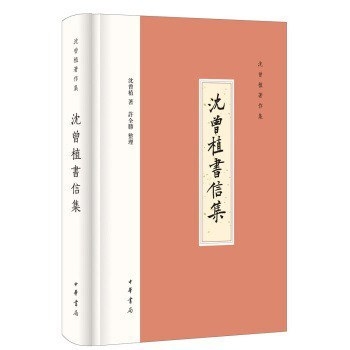
《沈曾植书信集》,沈曾植著,许全胜整理,中华书局2021年1月,465页,88.00元
沈曾植是一个在近代书法、学术、诗词乃至政界均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其诸多方面的成就均为世人所瞩目。书法方面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章草,对后世如王蘧常等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学术方面,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里做出了恰当的定位。诗词创作方面,则是别人眼中的“同光体之魁杰”和“词中之玉川、魁纪公”。在政治方面,其人于庚子事变后风雨飘摇之际,参与了东南互保的活动,为清政府保住东南半壁江山出了一把力。
对沈曾植这样一个“十八般武艺高强”的大人物,许全胜先生多年之前的博士论文《沈曾植年谱长编》“上穷碧落下黄泉”,差不多将与之相关的各方面材料都一网打尽了。其后许先生仍然矻矻穷年,锲而不舍,除了不断修订《年谱长编》外,还开展编辑、出版沈曾植全集的浩大工程,不愧海日楼之功臣、沈寐叟之后世子云。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许先生整理的《沈曾植书信集》,这是许先生前后搜集整理二十年、校稿一年的成果。他从各种文集、报刊、手稿乃至拍卖材料等处汇集来的八百八十封寐叟书信(很大一大部分是根据手稿一个字一个字辨认、录入)是一个大的寐叟资料宝库,经过其精心考订、系年之后,更加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我一直都喜欢看名家的书信集,因为在这种更为私密的交流中,写信之人更容易坦露自己的心扉,不讲、少讲冠冕堂皇的套话、官话,多讲、全讲直言不讳的真话、实话。最近新出的《沈曾植书信集》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形象更立体、性格更丰满的海日楼主人。看一看百余年前大佬在政治、文艺方面的见解,对我们更好地感悟当下,未尝不是提供了一面值得借鉴的好镜子。

沈曾植像
书信中《与张之洞书》和《与陶模书》,乃是集中、充分体现沈曾植政治见解与主张的文字。经历了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的连番风吹雨打之后,清政府已经准备再次扬起新政的旗帜,沈曾植在正月二十五日来到江宁,为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拟复奏新政摺,“其目凡十,曰设议政,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重州县,设警察,整科举。稿凡八九千字”(详见《与陶模》)。之后,自称“倡言变法,远在甲申、乙酉之前,在戊戌被排以黄老之讥,在庚子见绌以儒书之诮”(425页,《与张之洞》,其一)的沈曾植分别给新政的积极参与者、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的陶模各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在新政方面的主张。宦海沉浮多年,又经历了这么多前所未有的变局,沈曾植对时局的认识是比较清晰和深刻的,“政府至于今不能无作新之态,而决无择善之长”(307页,《与陶模》),“不能无作新之态”,一语道破了当权者的心态与心事。“世变至今日亟矣,体大者不可以狷怀理,事远者不可以快论撄,中西之法虽殊,所以行法者,知及仁守,庄莅礼动,纵千古,横四海,无异理也。”“以今日国势言之,譬之病后,形神尪瘠,而又欲治其痈疽,痈疽不免刺割,不免痛楚,固也。……当预讲止痛之方,而后得尽其刺割之术。”“宫府积弊,官吏各习,大痈疽也。变法,大刺割也。事失故业,官失定位,旧德亡,先畴改,隐心以言之,不得谓非天下一大痛楚也。”他主张开新去旧、兴利除弊要分开来,“开新与守旧二说不必并提,兴利与除弊二事不可并进,新既开,不忧旧不去,利既兴,不忧弊不除,此事理之自然。若嚣嚣然日以诟谇之声闻天下,人匿其情,而争心并起,则无一事可行,行而可成者矣。以开新为乐者,文明之象也;以除弊为快者,野蛮之习也”。想来沈曾植写下这些言论的时候,是针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至于新政应该如何来实施呢?痛定思痛,他提出“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愤时疾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矣。戊戌之败,本原在此”(以上见426页,《与张之洞》,其二)。
类似的主张、观点,在给陶模的信中也有体现,而在关于戊戌变法方面的反思,则谈得更为多些。“戊戌议政之权在小臣,故事杂而言厖,利未行而害已先至。苟议政之权在大臣,则同治以来兵政财政制造局诸事,创行变格之举多,曷尝有讹言繁兴、物情骇异者乎?今之从政,诚无足当此艰巨者,然当立法在以待人,不可因人而废法。苟主兹事者,休休有容,一切商各行省督抚而行,略如同治朝政体,亦可以徐为布置,七年病蓄三年艾矣。”(307页,《与陶模》)这段话中,对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可说是讲得非常到位,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与新进的、在朝中毫无根基的几个军机章京谋划举国变革的大事,变法诏书一颁再颁,各种变革举措层出不穷,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除了“讹言繁兴、物情骇异”,最后又有多少实效呢?其实,对戊戌变法,沈曾植一开始便不看好,“在上者苟无日月双悬之临照,寒暑迭代之机权,发宪求善,亦未必遽能如志”(312页,《与汪康年》,其四)。此札作于1898年6月16日,于变法之始,已能洞见其弊,不待百日之后才有事后之明了。“议政之权在大臣”云云,让人想起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的类似表述,陈宝箴以为“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论荐张之洞总大政,备顾问”。陈宝箴父子希望有一位大佬在朝中来主持变法,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是张之洞。虽然沈曾植在这里说“今之从政,诚无足当此艰巨者”,但是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熟思世事,自非壶帅入都,殆于更无他法”,“和调新旧,泯绝异同,虑终非秀才学究所能为”(312页,《与汪康年》,其四)。戊戌年如此,辛丑年也是如此,可惜清政府大用张之洞已经太晚,终不免“君民末世自乖离”了,“和调新旧,泯绝异同”,以“调停头白范纯仁”自许的张香涛也不免赍恨而终了。接下去,沈曾植谈到当年的刚毅和康有为,也可谓极具洞察力,“世知刚(案:刚毅)、康(案:康有为)之行事为反对,而不知刚、康之立志为同原,刚之末流流入于拳,康之末流入于票。无惑也,彼二人议论,尝与官吏为仇。凡匪皆仇官,则固有水流湿火就燥之相会者矣。海上谈风,大都此辈,近且倒灌京师。切齿之叹,不平之气,托于忠愤,滋启杀机,某窃奭然忧之。新政固平生延颈而望者,顾一误岂可再误”(308页,《与陶模》)。
沈曾植在政治方面的其他主张,在《书信集》也时时流露。比如,谈到尊孔,“吾党尊孔本意,在求万民之治安,非仅一姓之兴废。无君臣则无尊卑,无上下,无秩序,无法律。(暴徒昌言军士服从,是有法律时代之言,今为无法律时代,无所谓服从。政府非日日言法律者乎?而谓之无法律,历史心理,于此可见)”(第2页,《与陈焕章》)。“吾党尊孔本意,在求万民之治安,非仅一姓之兴废”,这话去戊戌年康党的罪状“保中国不保大清”也不远了。只不过世易时移,民国期间还来谈“无君臣则无尊卑”,也只能在认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如王国维类遗老诸人中得到共鸣了。又如谈到民权,认为“民权乃为盗权之代名词,可为长叹息”(53页,《与金蓉镜》,其十三)。在给吴庆坻的信中又说,“鄙人向持德日国家主义,且妄谓西人立宪以限制民权,谓限制君权者表面语耳。此语自谓窥见彼中政治家隐微,质之高明,当非河汉”(347页,其四)。在寐叟这辈人看来,所谓立国之本,“凡国所以立于天地间者,宗教一也,文字二也,伦理三也”(35页,《与丁立钧》其八)。而有宗教便有邪教,“邪教靡不起于乡曲陋儒,空腹斋心,荒经蔑古,以之饰智惊愚,其流弊遂无所不至。近溪、心斋,退儒者而进游侠,其末流可以成秘密社会,非必其初意,推诸山阴,则荀卿、李斯之论,恐儒林未肯公仞也”(55页,《与金蓉镜》,其十六)。
书信中不免月旦人物,沈曾植在戊戌变法之前劝康有为韬光养晦的事情比较为人们所熟知。戊戌变法之后,谈起康梁,寐叟尚不免怒形于色,大声疾呼,“康梁之说,邪说也;其行事,则逆党也。事状昭然,无可掩饰。彼且讳饰其邪逆,觍然自称新党。其狡狯之计,不过欲以此名强自解于天下,而又冀污染海内士流,误朝廷而斵丧国家之元气。海上妄人沿而称之,都中士大夫沿而称之,岂非重堕其术中,而为逆徒张之焰乎?彼其伎俩,东人近亦看破,闻有送诸美洲之议。弟尝谓,今日不能莅石厚,未尝不可锢栾盈,此于公法固无碍,惜无深思静气者为此事也”(47页,《与黄绍箕》,其三)。此札作于光绪二十八年戊戌十二月十二日(1899年1月23日)。此后,沈、康二人还是不免继续来往,后来更是联袂参预“丁巳复辟”,时过境迁,不知寐叟是否还记得起昔日自己对康梁逆党的观感。梳理一下沈、康二人的交谊,当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对极为看不起康有为的章太炎,沈曾植也并看不上,“闻章炳麟至伯华会所听讲,此君是‘鬼车见,即有旤’,孙少侯可鉴也”(156页,《与李翊灼》,其三)。
沈曾植在诗的方面曾自称“诗学深”,可惜书札中谈诗的部分不是很多,就如同郑孝胥在日记里也很少谈诗一样。寐叟谈诗的书札,比较集中在其弟子金蓉镜部分。提出的诗学“三关”说的《与金蓉镜太守论诗书》已经成为近代文论中的名篇了。在与金蓉镜其他的书信中,也还有一些谈诗内容。同光体当然绕不开陈后山,“后山出世当庆历相持之日,其晚年则为元祐党人,其文字渊源在南丰,而知遇在苏门,故其持论常立于不激不随之地,不犯正位,有微意焉。而其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之笔妙,遂适与不来不去、不增不减甚深般若冥合,故山谷之诗多禅观策进语,而后山乃颇有教家行证语,于诗家参法理,乃政可于此密辨之。至其晚岁同游,大多乡里后进之差知信向者,程度相去甚远,自寇国宝外,其他似尚不及渊明栗里,仅可比老杜夔州。而酬酢俛接,终不作一溢分之语,此其诗品之洁,尚友者,千载之下,有余忾焉。排比铺张,后山终身盖未尝遇此题目。仆尝拟后山为韩门之孟、欧门之梅,杨风子壁书千古,固不必别有丰碑大碣也”(61-62页,《与金蓉镜》,其二十六)。于后山其人其诗所论可谓精细入微,而“酬酢俛接,终不作一溢分之语”,这句话不免让人想到当代与寐叟同样“博学多识”的大学者于后辈往往奖掖逾分的故事。又比如涉及韩昌黎的两段议论,“晚唐诗沿波张、贾,张、贾系出韩门,北宋诸公无不染指晚唐者,于格无伤,第如南宋江湖专以此为事,则禅家所谓没意智耳”(53页,《与金蓉镜》,其十三),“陈陶在五代,峣然秀出,其人不凡,宜其诗亦不凡耳,要亦远承韩系。公胃气近韩,故拟之即似,如文通拟二谢,其相似仍从自分得也”(54页,《与金蓉镜》,其十四)。喜欢考镜源流,读诗不漏小家,容安馆主人不也是如此吗?
晚清时期,张之洞的幕府可谓各类人才的渊薮,其中擅长诗文、书法的不在少数,沈曾植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有趣的是,这些幕僚往往在诗文、书法方面与抱冰老人意见相左。陈散原菲薄巨公、元老的言论不必说了,即使沈曾植和张之洞也有很多分歧之处,比如谈到诗,张之洞是不满六朝的,在七古《哀六朝》中有过集中的表露。而在寐叟的“三关”说中,元嘉是其中一关。对魏晋诸人,寐叟有着同情之理解,“郁结之症,则关于心理,理恕情遣,非取材内典,无以释此结也。魏晋人寄情庄老,及今乃知其身世之感,不得不然”(197页,《与罗振玉》,其十七)。而对六朝诗,也有着深刻的感悟,“六朝诗之高者,大都以玄理胜”(52页,《与金蓉镜》,其九)。
海通以后,西洋事物纷至沓来,国人可谓大开眼界。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劝慈禧太后喝咖啡的镜头,不知道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樊增祥误把咖啡当作鼻烟的故事,经钱锺书写入《围城》之后,传播海内外。寐叟的书札也时不时提到咖啡。比如,好朋友陈石遗要来拜访,要预备什么饮料招待呢?以茶相待还是以酒相待?都不是,款待以咖啡,“公意畏酒,请备加非以待”(第6页,《与陈衍》其二)。有趣的是,寐叟一度把咖啡当作止泻药品来用。在给夫人的信中,写到“鄙近体甚好,可慰远系,昨腹泻一日,仍服咖啡而愈”(107页,《与李逸静》其二十)。可惜药效可一不可再,“鄙前日伤于酒食,腹泻两日,服咖啡不得力,平胃散一剂而愈,足见咖啡止能助运化,不能消停滞也”(109页,《与李逸静》其二十一)。在给友人的信中,也不免再抱怨一番,“加非昔以治腹疾极效,今无效矣”(70页,《与康有为》其二十)。现在人说到咖啡的功效时,往往会说其有刺激排便的作用,恰好与沈老夫子相反了。
沈曾植去世至今将近一百年了,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总有些认识是放诸四海、传之万代而皆准的,“至于士君子之知识胸襟,皆奴隶于外界粗浅之浮言、简单之俗论,甘放弃其神志之自由,而犹沾沾以教育政治文其愚蔽,亡国大夫,可谓寒心”(185页,《与罗振玉》,其八),希望我们能够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