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回首人生九十年,学会选择而使生活重燃火焰|此刻夜读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乐黛云先生的人生充满了坎坷曲折。中年之后,她重新焕发学术活力,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一书以回忆散文的方式,先生将自己一生的真实经历、真情实感、真切体察用隽永的文字娓娓道来——九十年历经沧桑,却始终坚韧如初。她在新书中写道:“生活的道路有千万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是选择。”

今年3月新书发布会上的乐黛云先生
闲顿与转机
我们一家凄凄惶惶地回到了贵阳。原来的房子已租给别人,我们无处可去,只好挤进“老公馆”。所谓“老公馆”,就是祖父去世前与他的五房儿子共居的处所。老屋很大,共有六进,从一条街进去,打从另一条街出来。
当年祖父去世,五兄弟分家,有的分了田产,有的分了商号,父亲放弃了其他一切,只要了祖父晚年刻意经营的小小的后花园。

8岁的乐黛云
父亲与乐黛云

我记得当时的“乐家大院”是一座很长的大建筑,横穿两条街:大门开在普定街,后花园出口是毓秀里。房屋有五进:第一进是办公待客的地方;第二进是祖父的书房,这两处后来改建为伯父临街的诊所;第三进是祖父原来的起居室,祖父去世后,设有乐氏族宗的牌位,由祖父的姨太太掌管,每天按时进香、敲磬、祭祀;第五进是一些无人居住的旧房。穿过这些荒凉地带就是后花园。
花园里原有一座带飞檐的旧楼,挂着“湘雪堂”的牌匾,有许多玉兰花、紫荆花和古老的银杏树,还有一口养金鱼的大石缸。父亲对这个花园进行了彻底改造,他买来许多外国建筑和室内装饰杂志,自己设计了一幢美丽的小洋楼。那还是1930年代初期,在贵阳确是绝无仅有。父亲对自己的杰作满意极了!他常常举行周末家庭舞会,宾客云集,华尔兹、狐步舞、探戈都从这里传播开去。他们在里屋舞兴正酣,我们几个小孩则在外屋把准备好的糖果点心吃个够!

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可惜好景不长,政府决定要新修一条马路,通过毓秀里,直达体育场。后来父亲告诉我,曾有人来联系,说是只要自愿出一点“捐赠”,马路就可以绕开一些,不一定从父亲的花园穿过。父亲认为如此公然让他行贿,简直是奇耻大辱,不仅拒绝,还把来人大骂了一顿。据说原来计划修的马路并非像后来那样,就是因为父亲坚决拒绝行贿,惹恼了父母官,一条大路硬是从我们的花园中央蛮横地穿了过去。花园中的这个厅,那个楼,当然全都被拆得七零八落,林木花草更是一片凋零。父亲已不再有钱修复破败的花园,只好将房子和地皮都交给当时正在发展的“信谊药房”经营。相约八年内由他们使用,八年后他们占一半,交还父亲一半。
“老公馆”堂屋旁边还有间空屋,我们一家四口就搬了进去。和原来的大花园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
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记得有一次,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片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旧货市场去卖,但人家不愿买,说了很多好话才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更难堪的是,当时已是贵阳名医的伯父,事业非常发达。他的私人医院占据了大部分老宅,而且修缮一新。许多权贵都来和他结交。就在同一院内,他们家天天灯火辉煌宾客盈门。我的六个堂兄弟都穿着时髦,请有家庭教师每天补习功课。我和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玩,每到下午三点,就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外发糖果点心的时候。这时,母亲总是紧关房门,把我和弟弟死死地关在屋里。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真是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一谈之下,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说起花溪,也真是有缘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四周青山环绕,处处绿树丛生,离贵阳市中心四十多里地,但多少年来,这块宝地却不为人知。

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四年,喜爱爬山越野的父亲就发现了这一片世外桃源。那时这里还是一片不为人知,只是仲家族聚居的荒山僻野。如果你不能步行四十里,就绝无可能亲自领略这一派人间仙境。父亲一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想在城外拥有一间幽静的别墅。他花了很少一点钱在花溪(当时的名称是“花格佬”)买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有三个房间长的房子,前面有宽宽的阳台,两边有小小的耳房,走下七层台阶,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周围镶着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间,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跨过草地,是一道矮矮的石墙,墙外是一片菜地,然后是篱笆。篱笆外便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它是大花溪河的一道小小的支流,把大河里的水引向脚下一大片良田。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有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后来,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用上厕所作掩护,读父母不愿意我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草地的右侧则是一间厨房和一间储藏室,父亲雇来看房子和种花草的一个孤单老人就住在这里。

这次重返花溪的机缘简直使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他的别墅离贵州大学足有十里之遥,他也宁可每天步行上课,而不愿住进大学的教师宿舍。后来他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和母亲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我们兄弟姊妹都在北京念书或工作时,他忽然得了脑血栓,人事不知,昏迷不醒。那幢别墅修建在土家族聚居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离镇上的小医院还有十多里路,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一时间更叫不来帮手。母亲怎么把父亲弄到医院,父亲又怎么能全无后遗症地恢复了健康,对我们来说,始终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因为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她担任的课程是美术和劳作。她教我们用白黏土做小器皿,并用铜板磨上淡淡的绿色。我知道这是为了纪念那位被枪杀的年轻美术教师吴夔。母亲还教我们用粗毛线在麻布上绣十字花,她也教我们铅笔画、水彩画、写生和素描。总之,她的教法是相当新潮的。她非常爱艺术,也爱她的学生。据说她和父亲结婚的条件就是婚后送她到上海读书学画,但是由于过早地怀上了我,一切计划都不得不付诸东流!后来母亲和父亲吵架时,总是恨恨地骂他毁了她的一生。其实父亲也并非不感到内疚,在我两三岁时,父亲曾带着我和母亲到杭州,让母亲在那里上了著名的杭州艺专。但是不到半年,由于我不知道的什么原因,我们一家又回到了贵阳。
总之,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只是这里的集市要比乌当大得多了,父亲又开始快乐地唱起他那些永远唱不完的老歌。
山城中学生活一瞥
抗战初期,我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一位“下江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叫朱桐仙。她也不愿住在学校附近,就在我们家那座小山上,比我们家更高一些的地方,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子。她单身一人,家中却很热闹,常有许多年轻的来访者。母亲不大喜欢她,常在背后指责她走起路来扭得太厉害,有故意卖弄风情之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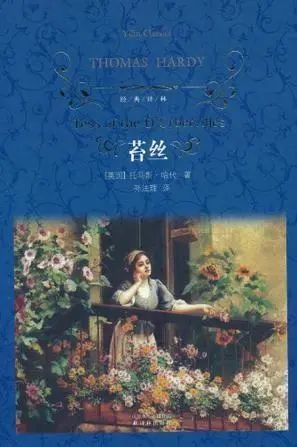
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造句和课文之后,就给我们讲小说。一本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时我们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当时还在上海,《德伯家的苔丝》正是他的最新译作。朱老师讲故事时,每次都要强调这部新译比旧译的《巅丝姑娘》好得太多,虽然她明知我们根本听不懂翻译好在哪里。在三年国文课上,我们还听了《微贱的表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几乎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
我们的国文课越上越红火了。大约在二年级时,朱老师在我们班组织了一个学生剧团,第一次上演的节目就是大型话剧《雷雨》。

我连做梦都想扮演四凤或繁漪,然而老师却派定我去演鲁大海。我觉得鲁大海乏味极了,心里老在想着繁漪和大少爷闹鬼,以及二少爷对四凤讲的那些美丽的台词。由于演出相当成功,朱老师甚至决定自己来创作一出歌剧。她在课堂上大讲中国京剧如何落后,意大利歌剧如何高超。她终于和一位姓李的贵州农学院的讲师合作,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可以称为歌剧的歌剧”。在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李先生几乎每天都来朱老师家,他俩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李先生会拉手风琴、会弹钢琴,朱老师构思情节并写歌词。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于是,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每逢李老师过我家门口,母亲总是对父亲悄然一笑。有一次母亲还一直熬到深夜,就为看看李先生究竟回家没有,我也使劲撑着眼皮,但很快就睡着了,到底不知结果如何。
不管怎样,歌剧终于完成,并开始大张旗鼓地排练。朱老师要求全班都学会唱歌剧中所有的歌,我们大家每天都得练到天黑才回家,这些歌也都深深刻进了我们年少的记忆。记得演出时,帷幕拉开,就是伯爵登场,他轻快地唱道:“时近黄昏,晚风阵阵,百鸟快归林。荷枪实弹,悄悄静静,沿着山径慢慢行……”他随即开枪,向飞鸟射击。一只被击中的小鸟恰好落在树林深处伯爵夫人的怀里,她于是唱起了凄凉的挽歌:“鸽子呀,你栖息在幽静的山林,你整天在天空飞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一些儿阻挡;鸽子呀,你哪知凭空遭祸殃,可怜你竟和我一样,全身战栗,遍体鳞伤,失去自由无力反抗。”正在此时,一位流浪诗人恰好走来,他唱着:“异国里飘零,流亡线上辛酸,这生活的滋味像烙印般刻在我心上。每日里,痛苦鞭打着我,我饱受人间的冷眼讽言。我只能忍气吞声,我只能到处飘零。如今,我不知向何处寻求寄托,何处飘零?!”当然,两个不幸的人立刻同病相怜,随即坠入情网。
后来,当然是伯爵一枪将诗人打死,伯爵夫人也就自杀身亡。
当时,这出“千古悲剧”真使我们心醉神迷!虽然所有角色照例都属于漂亮入时的“下江人”,但我们对于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却是十分尽职尽责。记得我当时负责管道具,为了打扮那位伯爵夫人,我把母亲结婚时用的银色高跟鞋和胸罩(当时一般女人不用胸罩)都背着母亲翻了出来。演出当然又是非常成功。露天舞台设在高高的土台上,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松林,当年轻美丽的伯爵夫人穿着一身白纱裙(蚊帐缝的),头上戴着花冠从松林深处幽幽地走向前台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我就是这样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
乐黛云/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1年1月版

稿件编辑:张滢莹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摄图网、出版书影
1981·文学报40周年·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