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庆邦《堂叔堂》:“我”和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


刘庆邦
刘庆邦的最新长篇小说《堂叔堂》,回忆了作者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既有大叔刘本德作为台湾老兵回乡的故事——从亲情的角度,表达了渴望两岸统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记赚钱的乡村老师刘本魁的故事——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心波动;更有刘楼村第一位党员刘本成讷于言敏于行的故事——展现了基层党员宝贵的质朴无私精神。
通过群像描摹,勾勒出人与土地、人与权力、人与时代的关系,展现了中原地区百年来的时代变迁,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和人性脉络,以及命运嬗变中不变的民风和人情之美。
值此新书出版,分享会也在北京举行,作家、《堂叔堂》作者刘庆邦,作家梁晓声,评论家贺绍俊,以及作家、《堂叔堂》编辑韩晓征,围绕长篇小说《堂叔堂》分享父辈们的人生故事。
刘庆邦,著有长篇小说十部,译成外文作品集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七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 《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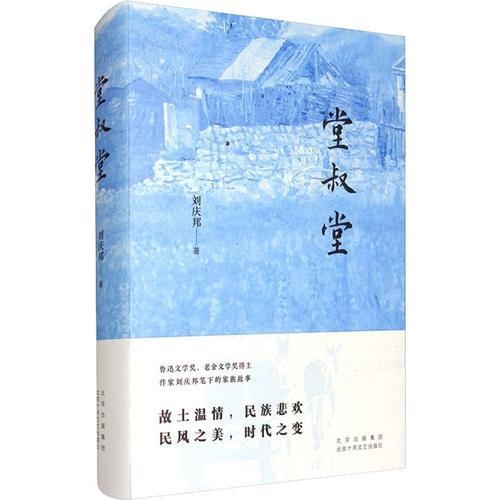
只有写到人,才能承载起历史
作家刘庆邦首先阐明了他关注平民的写作立场:“我是从底层出来的,可以说我们都是来 平民,对这个群体关注了解得比较多,直到目前我们还是一直在写平民的生活。现实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写平民的,而且是以悲悯的情怀关注平民。”我们写人有一个很大的向往就是我们作家要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保留历史,特别是扭曲的历史,苦难的历史,我们要通过写作保留下来。
有了这种深切的向往,在创作中他十分注重构造历史和人的关联,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历史的细节、历史的载体。我们的历史总是宏大的,和历史比较起来,每个人都显得很渺小,所以说每个人都像个历史的人质一样。但是虽然渺小,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必须看到人,如果看不到细节等于什么都没有看到,所以说作者的写作肯定离不开历史,因为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你要是看到历史了,你就必须看到细节,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他总结道。人也是历史的载体,他是生动的,是活泼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写历史的,但他都是写人,没有了人,历史也是不存在的。
正是因为关注和重视人与历史的关系,刘庆邦一直坚持“贴着人物写”的创作理念。
这个“贴”字很有讲究,不是推着人物写,或者拉着人物写,或者拽着人物写,“贴”起码表现了作者对人物的尊重,注重有主动性的发挥,并不是牵着人物的鼻子走,也不是随心所欲改变他,首先尊重贴近他的心理,然后才可能理解他,才可能写好他。另外,从虚实关系看,小说在材料上是“实”的,比如小说写了十四个堂叔,只有一个名字是改变了的,其余十三个都是真人真名,其中的情节都是作者的人生经验支撑的,但是从艺术上看又是“虚”的,写作要调动记忆,但这个记忆是有选择,是主观的,是不可靠的,不可能跟照相一样完全是现实,其中蕴涵的情感也是一种主观情绪化的输出,写作所用的文字更是高度抽象化符号化的表达。

“著文白浅显,行事常平衡”
而梁晓声认为,在中国这种“总和”要分城市和农村两部分来看,这样有助于全面理解1949年以来大陆的历史进程和华丽转身,因此“如果小说包括其他的文学作品,或者就说一本书它具有了时代和历史的认识价值的话,我觉得这并不只是对他文学性的肯定,甚至是对这个书的价值更加的肯定。”我们总会觉得人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但实际上随着对于人的理解的加深,可能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关系网的中间节点,同时你也可能是一个关系网发散的分子,人性里包含了文学的、社会学的命题。
“著文白浅显,行事常平衡。”梁晓声认为老朋友刘庆邦在做文和做人两方面都能做到通达平衡。梁晓声说,刘庆邦文字属于朴素的一种,但是有美感,让人联想到唐诗中,有些诗虽然很浅白,比如“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但是很有味道。他的新书《堂叔堂》贴着人物写,把人物写得非常精彩,可以作为教材范本的读物。
谈及作品的“白浅”,它是朴素中有美感的表达方式,这本书对人物的刻画,可以作为短篇小说构建人物形象的范本,在行文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农村历史的发展过程,比如文中直白地写出奶奶对童养媳曾经虐待过,后面又加上一个“这种对童养媳的态度在农村是普遍的,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当写到自己的亲人的时候,能如此冷静客观地写下来,这就是作家对人物、对历史、对我们所说的历史再现求真的一种立场。
作者在处理作品时不光是对自己的行为有内省,即便他是男性,也会出于同情女性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同样是乡间的风流事,一旦女性失去贞节,受到的打击会是非常大的,甚至影响到婚姻,可能影响到医生的命运。但是,如果是男性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男性几乎没什么事,这里作者的女性主义视角是很温和、很宽厚的,而且他是有相当的深刻性。
在家族小说之外找到了另外一种处理家族资源的方式
贺绍俊认为,这部作品实现了对“家族小说”的创新。中国过去的农业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家族基础之上的。由此家族小说是特别发达的,具有浓浓的乡土特色,内容其实就是作家处理家族相互之间的关系,家族和历史的关系。比如,巴金的《家》放在城乡交界的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现代化刚刚冲击到中国,冲击到封建文化,作家把家族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来写;传统的家族小说往往都有很大的野心,希望通过这个家族来概括中国的历史,大部分都是宏大的叙事。
刘庆邦有一百个堂叔,这个家族是非常庞大的。他不是从家族小说的模式去处理的资源,他把它看成是他重新认识历史或者人生的一种方式,他把每一个人看成是历史的细节,历史的载体,他的每一个堂叔,虽然性格各异,都跟他们的经历、都跟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密切的关系,都跟他的性格、遭遇有关系。实际上他们一生的经历也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某一点来。所以他不是企图通过家族的这些堂叔来建构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他要把每一个人物跟历史的关系,历史是怎么样塑造人物的这一点来表现出来。
作品背后还可以看出作者所坚持的历史观。历史都是讲述出来的,建构出来的,甚至绝对的说,没有一个绝对客观的历史,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关照历史,用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去描述图景。所以,不同的人虽然讲的是同样的一个历史事实,讲出来会不一样,历史真相这四个字往往会打出一个的问号,一个作者只有有了正确的历史观,才能够很好地去处理历史,书写历史,不是说没有历史真相我们就可以乱写,对此他高度评价作品的意义,“平民立场从比较政治的概念来说,就是人民立场,自古以来,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果没有一种人民立场的话,他就不能很好地去书写历史。人民性从一定角度来说是个永恒的东西。”《堂叔堂》的12个章节,重点写了14个叔叔,我们就可以通过每一个叔叔的故事,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不同的认识,他的丰富性就在这里体现,可以指向不同的社会层面。
《堂叔堂》还写到了乡村社会伦理和情感之间的关系,写到亲情和人的利益欲望之间的纠葛,怎么去处理,使我们对中国这种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其实每一个讲叔叔的故事,都会落脚在伦理亲情情感之间的纠葛上,这种伦理关系、这种亲情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值得写的东西,这也是它的独创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