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一席故乡的月光佐酒——读费新乾诗集《野孩子》有感

“从前的雪”已经融化,“野孩子”们在晒谷坪上狂奔,陪烈日一起“晒谷子”。山野里的“大湖”,银白色的波光粼粼,似刚从“雪夜归”来,姐姐“出嫁”后,故乡的“老屋生尘”。此时,人们在城市的灯火里眺望“窗外”,咀嚼自己的“酸甜苦辣咸”,占卜自己的“金木水火土”……
翻开费新乾的诗集《野孩子》,那一场久远的大雪扑面而来,记忆里的鸡鸣犬吠、腾腾炊烟和雪地足印无比清晰,熟悉的故乡、亲切的童年裹挟着雪花,清冽、纯洁、美好,直冲击到人的心灵深处,睹物间百转柔肠,思人时梦萦魂牵。

费新乾为八零后,祖籍湖北,现移居深圳。自2005年来到这座城市,一晃已过去15年,在《特区文学》杂志社安静耕耘的他,似乎远离大城的时代潮汐,静伫于文字的净土。
曾经,费新乾痴迷于诗歌写作,初中起即开始写诗,大学时更名噪江城,小说领域也曾有多部出品,然至深圳之后,在故乡和南国之间徘徊的新移民歇笔良久,童年遥不可及,人群熙熙攘攘,城市活色生香,个体随波逐流。
人,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安放自己的灵魂。
当个体的体悟郁积到一定的厚度,诗歌便成为了费新乾用以抵达生命最初起点的载体。2019年,他重新拾起那支遗失在岁月深处的笔,浣洗、注墨,记录故乡的远山、田野、河流、人物等林林总总,以充满温情的文字构建起城市新移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2020年的春天,费新乾被困湖北故土数月。期间,久远的、熟悉的场景如灶膛里的火,熏透寒冷的冬天,让生命慢慢地回温,直到新芽遍野、燕子归来。当他归来深圳,诗集《野孩子》在岭南这座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城市里萌芽、面世。
《野孩子》,这是一个趣意盎然的书名。曾经,我们都是一个野孩子,在山野间找寻快乐,曾潜入故乡河流的水底,“做一枚会呼吸的银钉”。也在所生存的城市里,如“大鱼逆着水流,一次次起飞”“也能跳出水面,朝着龙门奋力一跃……”只是,离家千里万里的我们,一次丢了魂、迷了路,再也回不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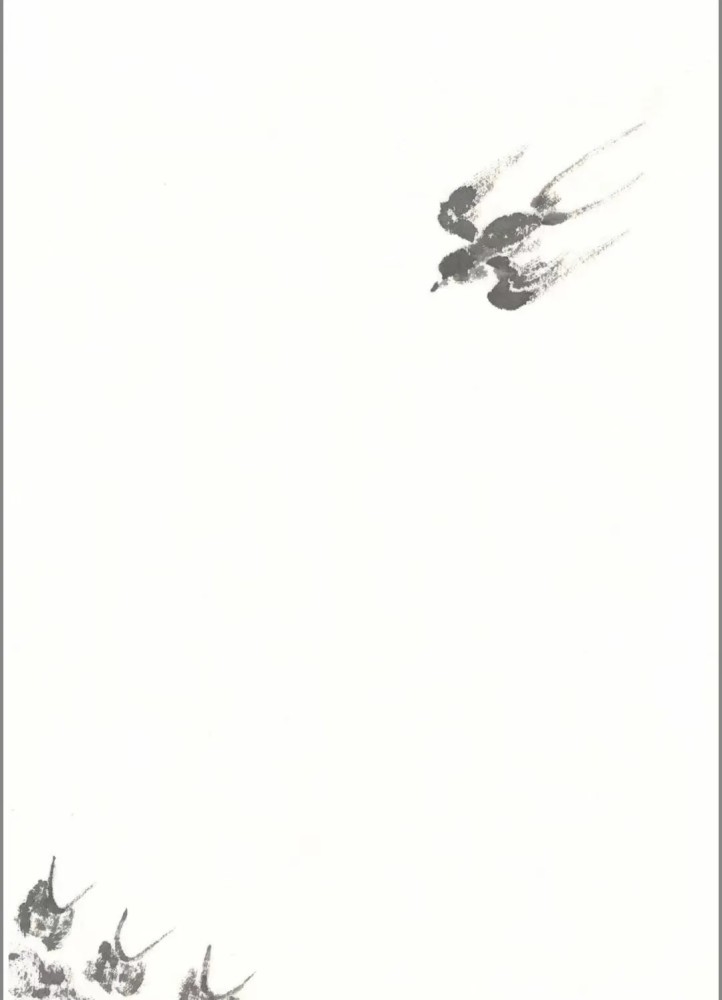
如许多人一样身处无法归去的迷茫与困顿之中,费新乾着眼个人童年记忆与情感体验,对故土和童年进行了深情细致的回溯。在《野孩子》里,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刻意的悲悯,那些诗歌语言如此简洁朴实,有如邻家叙话。而那些诗歌的辞格却如此具有审美性。
如《挖地基》一首:“挖第一下地基时/妈妈就感觉到阵痛/来自大地浅层/却深入她的腹部深处……多年后他写下第一行诗,就像妈妈挖出第一锹土……”这隐喻如此朴实,却如此回味悠长;如《一亩二》一首,“稻谷低垂着头/迎接阳光的爱抚/风吹起金黄的蛙鸣/蜻蜓择一禾而栖……”在费新乾的笔下,稻谷、蛙、蜻蜓等一切事物,都是如此的富有生命力,让人情不自禁,与稻穗同时低下陷入思考的头颅。

这些诗歌语言与流行诗歌的晦涩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却处处能让人体悟到冲淡、自然、疏阔之风,具自然美,也具人为美,其空间美和时间美自然混合,静态和动态相得益彰,不炫技的形式下内容质朴可亲,丰富多样的辞格如零珠碎玉撒满整本书的角落,不时点亮读者的眼睛,让人情不自禁沉浸到那些瞬间闪耀的岁月光芒里去。
《野孩子》的百首诗歌,除了描述故乡山河、人与动物、湖泊与大地,描绘生机与希望,也不回避灰暗与死亡。
如《对面林》一首里,“他们又矮又小/荒草丛生的坟墓”;如《辣》一首里,“奶奶的辣去了深山/一场胖雪一口瘦棺/大地艰难咽下/无数烟火熏黑的辣”……是啊,土地本就在进行无穷的代谢,有死亡,有新生,世界在无止无休的轮回里充满生机,如野孩子们在一个坟头到另一个坟头之间收集的蜡烛,那些来自死亡的光源点亮山野孩子自习的课桌,带领着野孩子们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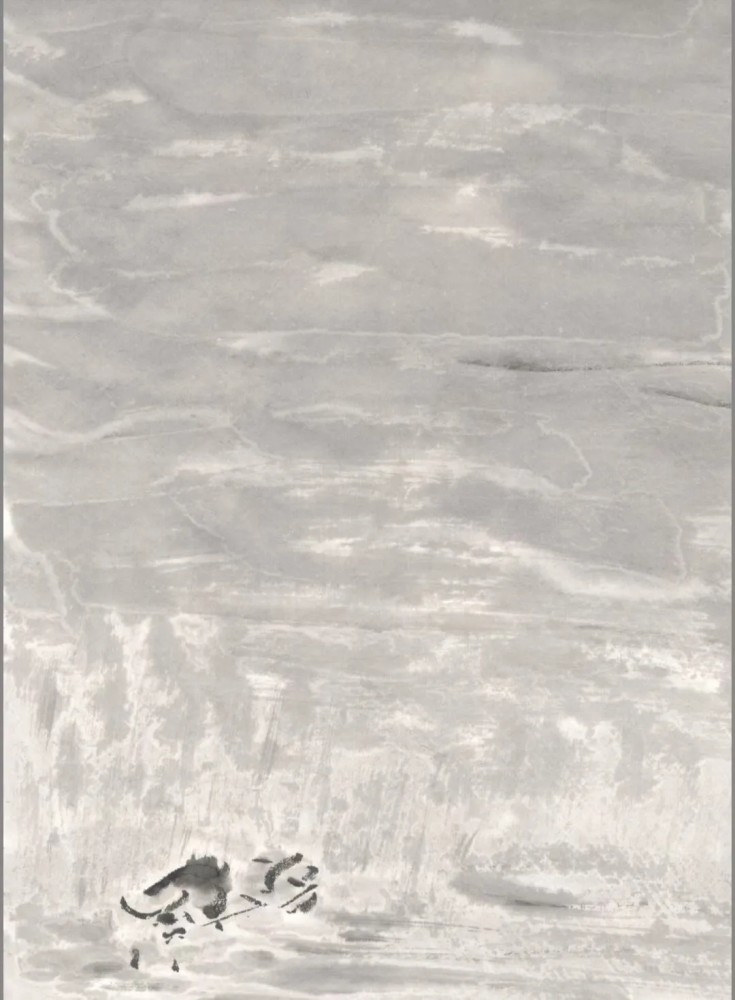
曾经,诗歌是先民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共同认识。在《野孩子》里,亦能惊喜地发现诗歌类似的质朴基因,它如此简单、朴素,却又直戳那些漂泊着的人们的痛点和乡愁,尝试着为他们构建起一如旧日的家园。它所表现的客体不仅是人,但是它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在这个过程中它如此朴素,朴素到天地明朗、至情至性,让许多离开故土经年的人,在《野孩子》的诗歌国度里,似忽然饮下了一口门口老井里的水,那种平淡、甘甜及回味之后带来的绵长思索,让人如此满足、踏实。
若撇开其诗歌之语言、之寓意、之美感、之返璞归真和纯粹,《野孩子》还兼具了难得的“诗情画意”。作为一本现代诗歌集,《野孩子》给读者的惊喜不止于文,更有图。这本书里,有100首诗,还有100张图。画者水去先生以极简的笔墨,勾、皴之间见田野广袤,几笔勾勒见乡人自在独行,浓墨浅绘间孩童河面嬉戏、林木下鸟雀腾跃,点染之间更有稻草垛立野,才出壳的鸡嫩弱却怡然自得……画面衬托下,诗里的每个文字似欲飞入那山野那莲舟甚至那装满收获的箩筐里去。

《野孩子》是现实的,也是梦幻的,是真实存在的,也是乌托邦的。《野孩子》里的诗歌,字里行间充斥着对快乐和幸福的追求,也敢于直面生命的愚昧和痛苦、死亡和新生。
细细读来,那些在每个人心里潜藏经年的记忆纷纷苏醒,在文字里变得如此鲜活。让人只觉,自己就是那些“点着火把上学”的野孩子们中的一个,“将天烧出一个洞”,沐浴着那个洞里漏出来的阳光,从乡村的闸门奔涌而出,横穿过麦地与果园,在城市里以诗歌认领属于自己的庄稼。
冬去了,春又来,万物又重新生长,野孩子们,正取了一席故乡的月光,在异乡佐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