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书评|文坛另类奇葩张书林的《白日梦》,梦想成真的别样方式
 2021-01-26
2021-0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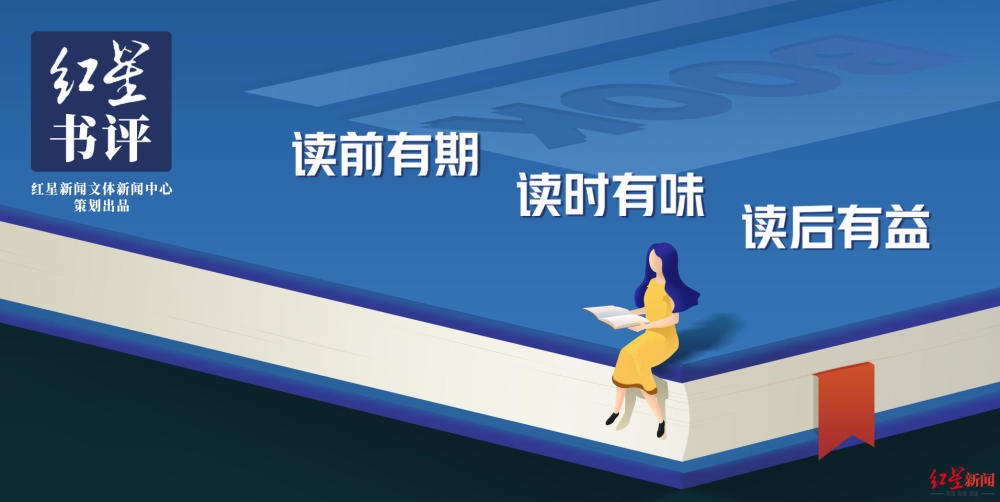
我以为这本书在五年甚至十年前就该出来。那时候我刚刚认识她,一个连投稿格式都不懂但才华难掩、自称裁缝却颠覆了我对服装设计认知的作家,我相信她很快就能横空出世,成为文坛一朵另类奇葩。
事实证明这只是我这种深陷文本的人一厢情愿的奢望。她和大部分天赋异禀的艺术家一样,出道的波折似乎是命中注定。所幸这本书终究还是出来了,而且在这之前她的《寻绣记》一书已经得到读者和市场的双向认可。两本书内容迥异,格调脱俗却是一样的,且互为映衬,也是意外之获。

《白日梦》我大概看了三次,每次看感觉都不一样。在反复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位背负现实压力又不弃文学之梦的人难能可贵的坚持和严谨。她总是一遍遍改,又对自己的艺术观点一再坚持,她言行和词语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作品的品质,精神品质和文学品质。在快速获取认可和坚持个人艺术追求两条岔路之间,她一直想选择后者。这在今天其实是不多见的。
夜黄镇,一个太阳从不落山的地方,是作者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一干人物在此演绎一场虚构中的虚构故事。我之所以重复用“虚构”二字,是因为小说中几乎每个人都为自己在真实之外重新设定了一个新形象。这个新形象在夜黄镇切割了过去的人生——逃犯、小姐、瘾君子,或者只是为了逃开困顿现实的诗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夜黄镇,太阳永久照耀,但虚妄无需暗影,他们演罢利欲情仇,却躲不开生死劫数。能写到这种痛处的作家不多。
什么是好小说,昆德拉说小说要有新“发现”,毛姆说小说要有“较普遍的人性”,卡佛说喜欢小说中有“危险感”,冯唐说小说有一根金线。我断章取义引用这些,无非是说,无论是传统写作,还是先锋实验,关于好小说,最根本的元素是不可剥离的,是有普遍共识的。比如故事好,语言好,叙述方式好。如果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能提供新鲜的经验和思想,让读者有艺术享受。我以这些标准衡量张书林的小说,逐渐认定了她小说的品质。

张书林
和很多作家的书斋写作不同,张书林有着丰富的现实经验。身为画家、外文编辑、哲学博士等五个优秀妹妹的长姐,她以楼上的拉姆这个品牌服装作为持生之道,生活留给她个人的梦想空间是有限的。正是这种现实与心灵的龃龉给了她无限的文学空间,精神世界的暗黑操练,情感生活的无依之惑,锤炼着一位敏感又务实的女作家,使她能在表面的承平故事中,不动声色地埋藏着两性关系、城市与乡村、人类的精神出路、人性的复杂等丰富的阐释空间,能把凶杀、外遇、劫匪等通俗元素写出纯文学的境界和味道。
我还想说说张书林小说的诗性。“土地是我们的,天空也是我们的,天和地之间的铺子与河流中的水都是我们的!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你们汉人像蚂蚁围口水一样围过来,一夜之间租铺子开满了全镇!”这段对话写出了夜黄镇当前的现状,这种比喻和腔调,使小说的市井之气也充满了诗性之美。“见过她的人都说她瘦得像一株干硬的梅花”,在为文人所乐道的梅花和巴五母亲的瘦之间,两个意象的叠加使小说的叙述空间无限展开,每一个字都有着令人心痛和心醉的复杂感情。类似这样的语言比比皆是,小说的“艺术魅力”就在这一点一滴中锻造而成。既收留着边远小镇的传奇魅力,又展现着作家创作的天赋和信心,让我们从读故事的快感,不知不觉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艺术享受中。她从容地驾驭着文字,像播撒鲜花的仙女,制造着这个神秘、野性,又触手可及的幻境。

我经常看她的微信,她晒出那些她设计的头饰、衣裙和她生活中那些有味道的瞬间。我知道她是一位生活者,生活者的写作像是一条奔涌的河流,新鲜、独特,不会枯竭,她是独一无二的,她不复制别人,她的写作也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抵御着别人的复制。这很难做到,但她做到了。
“从最初的陌生,到后来的熟悉,张书林和我说得最多的是她对文学的执着。她一再强调,她可以干别的活挣钱养家糊口,但文学,永远是她最纯粹的精神家园,她终归是要回来的。”这是几年前我在写给张书林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现在,她带着这本设计别致的《白日梦》回来了。此梦非彼梦,这个梦优雅、深邃,是文学这条忧伤河流之上荡漾不羁的轻舟。(王秀云)
王秀云: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22届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出局》《飞奔的口红》等,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钻石时代》《我们不配和蚂蚁同归于尽》等。
编辑 李学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