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庚子读新书举荐十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
也许这是我很久以来读书最多的一年。除了教学需要所读的专业论著以外,从春天开始比较随意地翻看各种跟我的专业工作沾边不沾边的书,多是前几年出版的佳作,如黄裕生《权利的形而上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袁凌《寂静的孩子》、徐晓《半生为人》、陈冠中《香港三部曲》等等。不过这里要谈的是
2020年出版的面向公众的新书,也许因读得多些,受益且印象深刻的也较多,这里循旧例只推荐十种。
1)彼得·德默兹《布拉格:黑色与金色之城》,张帆译,北大出版社

我把这本书归入旅行文学,当然它比一般的旅行作品厚重得多,实际上更接近历史。
2020年翻译引进的旅行文学好书真不少,塞巴尔德《土星之环》、保罗·索鲁《旅行之道》、苏科图·梅塔《孟买:欲望丛林》等,都值得推荐。我在这里特别举出彼得·德默兹这一本,是因为我觉得此书超越了怀旧和乡愁,以历史批判的冷峻扩展了旅行写作的限度。引一段序言里提到的作者
1948年在查理大学的经历:“那时我是个学生,不无惊奇地发现,一些我最崇敬的老师在执政党更换后迅即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以免一不小心荣幸地成为不走运的反对派。在此期间出版的为数众多的学术著作,每一本都是一个关于它自己的故事——或是甘心为奴,或是妥协,或是自我羞辱,间或有一些少见的反抗。”每个城市故事的流行版本都致力于隐藏、混淆以及单一叙事,而一个好作者有责任揭示多层次的过去,既描画初日的美丽金光,也不避寒夜的惊悚黑暗。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作者是如此博学而深刻,读起来感觉自己重新变成了一个渴望新知的青年学生。
2)刘子超《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文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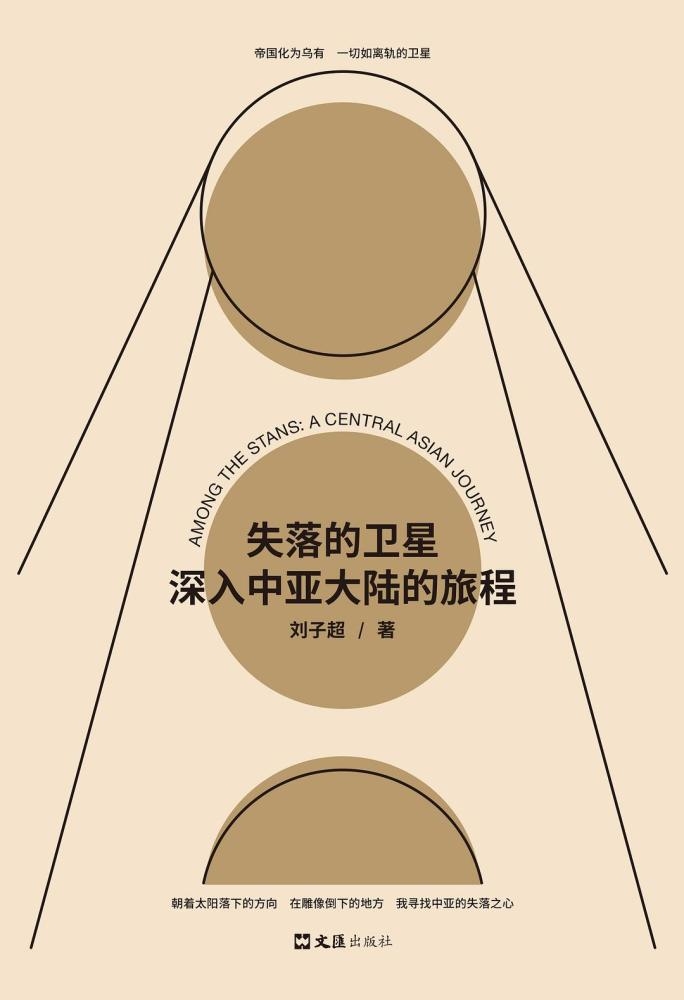
2020年所出中文原创的旅行写作我读的不多,其中刘子超《失落的卫星》和胡成《陇关道》印象最深,因为都是我关心的题材。比较而言,《失落的卫星》在旅行难度和写作技巧上更突出。此前我似乎还没有读到中国人写的长篇中亚游记,读刘子超此书自然格外仔细。我感觉,刘子超这本书受英国旅行作家柯林·图布朗(ColinThubron)同一主题的《亚洲的失落之心》(TheLostHeartofAsia,1994)影响较大。但两人在中亚旅行的时间相差二十多年,恰好是中亚各国急剧转型、快速变化的时期,对读二书很容易看到独立至今的社会文化变迁。我自己在中亚旅行较多,而且关注中亚史,读近代西人的中亚旅行记较多,忍不住会把《失落的卫星》放在这些作品中去比较,从而对各书的长短特点略有体会。刘子超这本书示范了旅游与旅行的不同:旅游是看名胜古迹,旅行是看日常生活;旅游主要看景,旅行主要见人;旅游是在远方见识陌生,旅行是在他乡寻觅熟悉。刘子超的中亚,不是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些古代建筑,而是后街暗巷那些小酒馆,是一般游客接触不到的普通百姓。我一直觉得,好的旅行作家是苏菲诗人与探险家的合体,刘子超正走在这条路上。
3)基思·罗威《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朱邦芊译,社科文献出版社。

近年翻译引进了不少上佳的面向公众的历史读物,我读过的如伊恩·莫蒂默《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查尔斯·蒂利《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等。
2020年也不少,比如丹·琼斯《圣殿骑士团:崛起与陨落》、托比·格林《一把海贝:从奴隶贸易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罗纳德·赫顿《巫师:一部恐惧史》、托马斯·阿斯布里奇《战争的试炼:十字军东征史》等。我在这里特别推荐基思·罗威的《恐惧与自由》,是因为此书把以上各书的一个共同特点张扬到了极致:不满足于讲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服务于作者的思考,历史写作因此而饱含智慧,有强大的逻辑力量,以及令人警醒和回味的思想洞见。说到思想,这不正是中文原创作品的最大不足吗?和基思·罗威上一本大受好评的《野蛮大陆》一样,《恐惧与自由》也是关于二战遗产的深刻反思。随手摘几句书里的话:“二战的最大悲剧在于,它不但把有精神病倾向的人推到了拥有巨大权力的位子上,还在社会制度中培养和放大了这种病态,以至于连普通人都既有能力从事邪恶,又都热衷于从事邪恶。”“二战不仅把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偏见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还为那些偏见变成仇恨、仇恨变成行凶提供了机会。”话说回来,有思想的历史书也必须讲故事,基思·罗威正是讲故事的高手,他的书让人一读就放不下,好奇他怎么搜罗到那么多天南海北的奇崛人事。
4)袁凌《生死课》,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有不少直面现实的好书,有的呈现为社会学调查报告,如胡嘉明、张劼颖《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还有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第三部《物流商、装卸工、女性卡车司机》(其中最特别的当然是女性卡车司机这一部分)。有的像是新闻随笔,如黄灯《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带着看得见的呼吸、烟尘、脚步还有凝视”。在这些勇敢而真诚的作品中,我特别推荐袁凌的《生死课》,因为我认为他和他的作品(不要忘记《寂静的孩子》)在当代中国太独特了。我为这本书写的推荐词一点也不是过誉:“世界至少有一半掩映在阴影之下,人类感官却天然地倾向于仅仅捕捉光亮。回避阴影也许可以使我们更容易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但自欺只会让真相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无从认知,越来越不可理解。在少数勇于探究阴影世界的作家中,袁凌以他独有的冷峻与从容讲述这个世界的另一半。或许,一时半会儿能接受这个道理的人还不多:袁凌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刻意回避的生命故事,并不是历史的素材,它们就是历史本身。”引书里的一段话,可见袁凌的叙事风格。他探望那些脑部受损不能自理的儿童,陪伴其中一个绝不出声的男孩:“他顺从地让我握着这只手。我本来想试着说两句话,后来放弃了,只是这样沉默地一直坐着。坐久了,感到和他成了一个人,无法表达自己。”
5)王笛《显微镜下的成都》,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读过王笛2018年出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今年他的《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底层看历史》出了修订本,另外还出了《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都很好。我这里推荐的《显微镜下的成都》其实是他过去有关四川的几部作品的选粹,通过解读四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街头、茶馆、袍哥、麻将),把史学之光投注在小贩、茶客、堂倌、市民等小人物身上,以档案、口述史、地方志、小说、歌谣、新闻报道、图片等多种资料,再现往昔成都的日常。此书基本上可以反映他在城市微观史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与实践。必须特别说明的是,此书有一篇理论性很强的《导论》,介绍自己研究理论方法的取径、对中国史学状况的观察、以及对某些学术观念的剖析和批评。王笛提出中国的历史研究与写作要有一个民众转向(相对于传统的精英视角),从大众生活理解社会的连续与断裂,从民众日常观察国家对地方的宰制以及地方对国家的抵抗,宣称自己的历史观“总是站在弱者一边观察问题,同情下层弱势群体的遭遇”。对地方的微观研究可以揭示权力的复杂性,既要考察看得见的权力,也要考察看不见的权力。他指出中国历史学的痼疾包括偏爱宏大叙事、沉迷定性史学以及对规律神话的持久崇拜。他说:“我们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了历史的审判者,而非冷静的研究者,我们的研究充斥着政治名词,但又经常对这些名词缺乏学术的限定。……历史研究除了诚实公正、言之有据、独立思考外,真的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清规戒律吗?”他发现,中国很多历史学的从业人员似乎并不理解,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其实是现代史家的职业道德。在王笛看来,中国史学的以上痼疾还具体表现为一些学者对微观史学“碎片化”的忧虑和批评。他明确表示,中国历史学并不存在“碎片化”,事实上“在整体旗帜下,存在大量空洞化的重复研究,其内容不过是人云亦云,了无新意……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细了,而是太粗犷了”。
6)马克·霍尼斯鲍姆《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谷晓阳、李曈译,中信出版集团。

大疫之年,流行病病毒学知识在全世界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普及,网络当然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而与瘟疫史相关的书籍也借机畅销一时。据说威廉·麦克尼尔1977年的经典《瘟疫与人》是今年全球范围内被读得最多的书之一,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并驾齐驱。必须特别表彰中信出版集团,他们的“见识城邦”在推动大历史和环境史方面独树一帜,流行病史也在他们的光照之下。
2018年“见识城邦”推出了《瘟疫与人》的中译本,由医学史专家余新忠等担纲译事。同年,他们还推出了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名著《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郑明萱译),这本书的一半内容涉及新旧世界的病毒与细菌交流。
2019年中信出版集团又推出沃尔特·沙伊德尔《不平等社会》,这本在我看来足以代表当代历史学向不平等宣战的书,概述自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实现程度降低、烈度减弱,把瘟疫视为这一过程的四大杠杆之一。
2020年5月,中信再出马克·霍尼斯鲍姆《人类大瘟疫》,机缘巧合地响应了时代,同时又是对中信传统的秉承。这本书以生动简约、引人入胜、堪比新闻报道的写作风格,梳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遭遇的十次大瘟疫,警示那种以为科技发展已使人类征服流行病的狂妄之见,指出人类未来必须做到更合理地与致病微生物乃至自然和谐相处。正如评论者所说,如果说过去100年的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无论科学变得多么复杂,我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被新的疾病和病毒株所困扰。亲身经历过2020新冠大流行,我们对历史上瘟疫冲击人类社会的深度与广度终于有了想象的基础。不过,无论是考察古代的瘟疫如黑死病,还是近一百年的瘟疫如西班牙大流感,抑或当代的SARS或新冠,我们最大的收获还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死亡阴影下)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人与社会。
7)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张守进译,汉唐阳光·陕西人民出版社。

人类对暴力的迷恋似乎不会完结,各个社会的历史写作都把最大篇幅献给暴力的最高级形式——战争。看看每年新书中有多少是关于战争的吧。战争是群体之间的暴力宣泄,对战争的组织者来说,战争是谋取政治利益的一个选项,对战场上的普通官兵来说,战争是合法谋害陌生人或者被陌生人合法谋害的机会,而投入这种血肉祭祀的各方都深信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讨论战争,很难不对人类个体与群体的理性前景深怀疑虑。因此,当演化人类学家彼得·图尔钦借助人类一万年来的无数战争以观察人类社会的成长与合作时,他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和图尔钦先前已由中信引进的《历史动力学:国家为何兴衰》一样,《超级社会》是以文化演进的视角观察战争及其后果。他把第四纪冰期结束后的人类历程视作一个完整连贯的历史,是单数的而不是复数的历史,从而抛弃了已日渐陈旧的文化、文明两阶段划分的历史观,以及分区域、分国家的近代历史观,以文化演进这门新学科的方法和立场研究战争,指出冲突和战争大大提高了卷入战争的各社会内部及它们之间的合作水平。人类合作能力及合作规模的演进才是历史的主 线,而战争是隐藏着的决定性机制。这本书对战争如何推动人类文明、如何推动平等主义,有说服力很强的论证,包括许多可量化的历史数据与模型。群体演进的基本理论立足于图尔钦对人类合作天性的信心,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对基因自私性的批判意味深长,因为人是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复合体,如果一定要说自利是基因内定的,那么人类的特别之处正在于许多个体都可以看到超越性的长远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人会为了他人而牺牲自我),这才使得人是决定人类命运的第一要素。
8)埃利亚斯·卡内蒂《群众与权力》,冯文光译,上海三联书店。

群众或大众不仅是一个现代概念,也是一个现代现象,与中文常用的老百姓有极大的不同。老百姓是被领导的、分散孤立的,与政府的关系是上下垂直和单向的,群众和大众则是集体的、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的,与政府的关系是双向的,即有能力向政府施加自己的影响。很显然,近代以前只有老百姓,没有大众或群众。剥离了大众的动员与参与,近代世界历史就无法讲述。当托马斯·杰弗逊写下“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话时,他说的人人,即使只在美洲范围内,一定不包括奴隶、女性和印第安土著,要知道他们的人口占比要大得多;更不用说在世界范围内,不会包括非洲、亚洲的绝大多数阶层与人群。然而当《独立宣言》以“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前提把殖民地的革命者与英帝国的统治者平等对立时,这一前提的潜力甚至注定了二百年后民权运动的伟大胜利:原理(特别是在成为法律条文后)的普适性早晚会成为所有人的武器。只不过,当大众苏醒,对精英来说,一切开始变得相当不确定,显得容易失控。大众动员及其运动当然是由精英组织的,但精英之间的竞争开始受制于大众,大众不再是被动的财源、兵源和劳动力。这一历史变化引发精英对大众的深刻疑虑,古斯塔夫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等书是极好的反映。经历了近年世界性的社会撕裂,在因特网和智能手机时代,撕裂几乎遍布所有的群体和家庭,反思大众议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为此,埃利亚斯·卡内蒂《群众与权力》值得推荐,他对群众/大众探讨的广度令人吃惊,而他的焦点也不都是那么令人不安。无论如何,未来不再是少数人的设计。
9)罗伯特·勒纳《天使时间:康托诺维茨传》,宋宁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家一般不会成为传记写作的对象,以历史学家为传主的作品更不容易进入公众阅读的视野。世界范围内只有很少的例外,中国有陈寅恪,我一直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如何被热议,“对科学院的答复”是如何脍炙人口。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无论他们的专业成就多么高,其人生故事只有同行和弟子热衷谈论。根本原因在于,正如我的老师田余庆先生所说,“太平淡了,既没有参与什么时代大事,也没有跟什么大人物周旋往来”。对于学者来说,平淡一生未始不是幸运,陈寅恪一定期待安安静静的学术人生。但总有例外。罗伯特·勒纳是一个中世纪史家,他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中世纪史家康托诺维茨所写的传记《天使时间》,就完美诠释了这一例外。但凡读过《国王的两个身体》,都会对康托诺维茨产生谜一样的疑惑。据说他早年为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所写的传记是纳粹领袖们最喜欢的历史书之一,甚至激发戈林元帅在1943年夏天把腓特烈二世的遗骨从意大利转移到德国。这个曾以德意志为傲的犹太学者,是怎样经历了一生多个过山车般的大角度转变?他的传奇故事之一,是194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拒绝签署效忠声明而被开除——想想我这个年纪(也许还有别的年纪)是多么害怕失去教职和退休金。《天使时间》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有多少知名学者的一生能比得上这样一部戏剧:他曾在凡尔登战斗,在慕尼黑交锋,他是为斯特凡·格奥尔格效力的骑士,发表过反对纳粹主义的演讲,他躲避了‘水晶之夜’,领导了一场反对奉行麦卡锡主义的大学董事会的斗争?有多少知名知识分子从右翼转到左派,而不是正好反过来?又有多少是如此值得借鉴?一部传记不可避免。”对于关心史家如何度过那样激荡的时代的人来说(特别是今天,当我们面对也许会骤然激荡起来的未来时),阅读这部传记也是不可避免。
10)陈映真《陈映真小说全集》(包括《夜行货车》、《赵南栋》、《将军族》共三册),理想国·九州出版社。

陈映真的小说慕名已久,以前只读过两三个中短篇,捧读新出的这三本,才知名不虚传。“华盛顿大楼”系列是现代都市的命运缩影。只因陈映真的平民意识如此强烈,他对小人物内心与命运的关切才如此动人。“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这句话最好可以混进满街的口号标语里,让每日上班的人看得到。那些黯淡的城市后街,环境崩坏,文化失据,被异化的生活、被压抑的梦想、被辱没的尊严、被无声伤害着的心。他说:“我写这些故事,其实就想告诉人,人的精神水位曾经这么高过。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梁文道评价他:“他带给读者的不是说教和灌输,而是刺激你不断地反省、怀疑、提问。这才是一个左派应该具有的批判精神。左派的爱,指的是去爱那些在社会上所有被侮辱、被伤害,同时还发不出声音,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人。”有个朋友给我写信推荐陈映真:“文学,为受侮辱的人重新找回尊严。”我想,历史学也是如此,我们有共同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