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角的春天》:流亡文学,或“去流亡化”的书写|书评

1948年1月13日,智利诗人聂鲁达做了反对维德拉军政府的演讲,此后不久,为了躲避刺杀被迫流亡,经历“盲鼠的一年”,东躲西藏,落脚墨西哥。
聂鲁达写过一首诗:现在,春天,请告诉我有什么用,对谁有用,幸好我还记得/你有什么用/我觉得是用来拯救落在任何一口深井里的人/那个词本身即是青春的仪式/对谁有用,好吧,依我拙见,你对生活有用/比如,我只需念出“春天”这个词,就会感到生命力、勇气和活力。
这首诗出现在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小说《破角的春天》临近结尾处。被关押五年之后终获释放,圣地亚哥在飞机上祷告,轻轻念出“春天”这个词语,他想:春天就像一面镜子,但我的那一面有一个角破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经历了无比充实的五年之后它不可能保持完整/但即便有一个角破了,镜子也依然可以用,春天也依然有用。
撰文 | 林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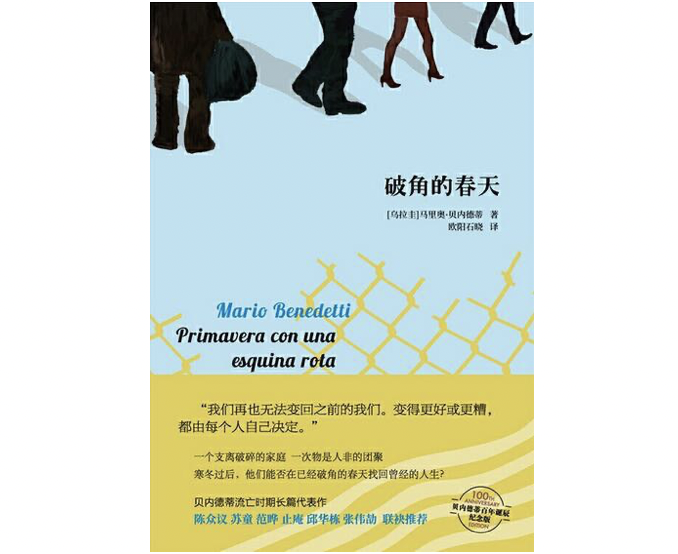
《破角的春天》,(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著,欧阳石晓译,S码书房|作家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经验是想象力的出发点
马里奥·贝内德蒂于1920年9月14日出生,童年起就对文学感兴趣,后来他当了记者,做访谈,撰写旅行笔记和评论文章,担任过著名的《前进》周刊的文学主编,再后来,他创办了哈瓦那美洲之家文学研究中心,曾任教于乌拉圭共和国大学人文系。
贝内德蒂关心政治和民生。他于1960年在美期间加入支持古巴革命的知识分子团体,写作描写乌拉圭经济、政治和道德没落的作品——《麦草尾巴的国家》,踊跃地参与政治、军事活动,领导左翼政党“三月二十六日运动”。1973年6月27日,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贝内德蒂离开祖国,长达十二年流亡在外,辗转阿根廷、秘鲁、古巴和西班牙。
《破角的春天》出版于1982年,在乌拉圭公投前一个月。贝内德蒂写作这部小说时的心境,与聂鲁达写下诗歌时的心情,必定产生了共鸣。经验是想象力的出发点,是想象力通过奇妙的思维调和伸向虚构的跳板。回忆的线索经过作家精心的编造,构成具有独创性的文学活动,事件转化为文本的时候也经历了一番深刻的变动,从而获得更普遍的价值。
流亡,在名为“自由”的监狱
《破角的春天》是一部特别的多视角小说。主要人物包括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的妻子格蕾西拉、女儿贝阿特丽丝、父亲拉斐尔和圣地亚哥的朋友即格蕾西拉的情人罗朗多。在圣地亚哥坐牢期间,拉斐尔带着格蕾西拉和贝阿特丽丝流亡异国,得到圣地亚哥旧友的照顾。这些人物的活动、对话、占很大分量的内心独白,构成小说的主干。独白是一种容易引起读者共感的方式,有助于理解人物各自的想法和立场。
书中还有一些斜体字的章节,这些章节是贝内德蒂自己真实经历的描述,或其他乌拉圭流亡者的遭遇的讲述,这部作品以虚实相间、相互印证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与叙事、记忆与书写的转化与表达,而真实经历像《破角的春天》这座虚构房屋的坚实地基,让整部作品更有现实感,更有力。不同人物、不同形式之间的自如跳转,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艺和语言的掌控能力。多线并发,组成复杂又清晰的全景图像。

《破角的春天》外文版书封
圣地亚哥服刑的监狱名叫“自由”。这座监狱真的存在。乌拉圭大作家加莱亚诺曾经描述,那里关押着很多政治犯,气氛肃穆,未经允许不准说话、唱歌、吹口哨、打招呼。图书不能有鸟儿、情人、蝴蝶、星星、孕妇等图案,因为它们代表着希望、爱情、自由、光明与生命。监狱是剥夺自由的地方,名之为“自由”,是荒诞的现实,类似虚构的悖谬,不可理喻的证明。据说,有五岁的小女孩去“自由”探望父亲,她带着的图画是一株大树,树叶上画着一些圆圈,女孩悄悄告诉父亲,那是藏在叶间的鸟儿的眼睛。小说里,寄往“自由”的信件都要审查,人们发明一些暗语,小心翼翼地绕过暗礁,偶有消息传递成功,必须抑制喜悦,不可表露于外。
在墙内,独自一人,熬过一个又一个重复的日子。监狱生活的特性,空间的缩小和时间的延长,在圣地亚哥的感官里变得格外鲜明。月光是奢侈的,在最初的两年里,连月亮都看不见,圣地亚哥仔细观察墙上的污迹,在污迹中想象面孔、动物、物体。对家人的思念,是他最深切的实在的拥有,他回忆与妻子的爱情,怀抱对父亲的歉疚,想象他那出生不久就分离的小女孩的成长,担忧父亲的缺席会对她造成的影响。在冬天里,他等待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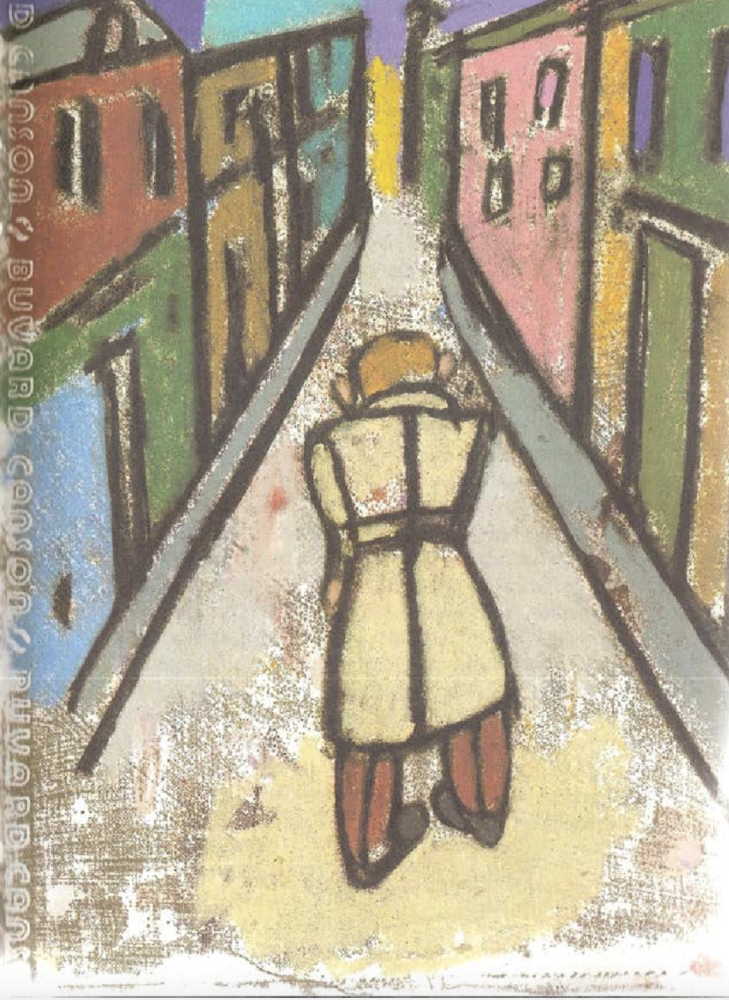
贝内德蒂小说插图
拉斐尔是一个典型的流亡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圣地亚哥的引领者,与监狱之外的社会观察家,或者说,作为贝内德蒂本人的主要投射对象,拉斐尔有强烈的漂浮感,觉察到原生文化的风化与无法重组,但是,他在因流亡导致的“残疾,遍体鳞伤,身体的一部分被挖空了,并且失眠”的煎熬中依然不肯放弃:“我们这些老人都是灵车,……灵车还依然可以行驶的人,将帮助他们记起他们曾看见的东西,以及他们未曾看见的东西。”
格蕾西拉和罗朗多,代表了脱离家国之后的新一代移民的本地化,他们打算开启新的生活。流亡的原意是“跳到外面去”,跳跃进入新的生活,无可厚非。而且,也许,就像书中所说,融入另一种生活是对流亡最好的反抗。
新的社会,新的希望,更多地被寄予在贝阿特丽丝这一代人身上,尽管她与父亲从未谋面,在蒙昧的状态里,她已经在承袭,在探寻父亲与祖父的理想,什么是“政治犯”“自由”“祖国”“赦免”,为什么一个人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会被投入监狱,她以孩童的方式解释那些难以捉摸的貌似庞大实则空虚的概念,在词与词之间,女孩以自己的文体创造着世界。
去流亡化,不能朝现实关上门
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里写道:问题的实情在于,一个人脱离了专制,则只能流亡至民主。由于他前世的生活,他能远比民主制度下的居民更强烈地体会到民主制度的社会优势和物质优势。然而,恰恰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主要的副产品是语言上的障碍),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在新社会中扮演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角色。
拉斐尔想: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够适应那个转变后的国家,那个此刻正在禁锢的密室中孕育的国家。是的,也许“去流亡化”会跟“流亡”本身一样艰难。
去流亡化,一直是贝内德蒂写作的核心命题。

流亡,它表现为自由的特质,是向着自由而去的决心的履践。人在躯体上离开故乡,位移进入不同的文化语境,精神上也要经受洗礼和考验。流亡,在情感取向上,又指向怀旧的自我束缚。怀念之情帮助作家驻守在他的故园,在流亡的旅程中领悟往昔的可贵、命运的无常,流亡因此也常常会被浪漫化。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作家还要思考自己的作用意义,反思性的怀旧的立足点是当下和未来,要探索国家和族群的潜在机遇和未完成的许诺。
卡彭铁尔说:“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马尔克斯说:“不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罪过。”贝内德蒂说:“不能朝现实关上门,如果天真地试图把它关在门外,也不过是白费力气,因为现实会从窗户跳进来。”在拉丁美洲,写作与政治,从来无法分开,也不能分开。
在《百年孤独》《族长的秋天》等作品里,马尔克斯用一种我们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独裁者,贝内德蒂的写作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路径,注重描摹生活细节场景,在写实的基础上作结构、形式的创新与对人物内心的深入刻画。贝内德蒂的另外两部小说《休战》、《感谢火》,都借助主人公的观察和感受呈现碎片化的日常,也都曾经被批评为琐碎与庸碌,贝内德蒂在拉美作家中长期被低估,在近年的文学回归潮流里,他的重要性方才日渐凸显。
1973年政变之后,乌拉圭成为全世界政治犯密度最高的国家。这就是乌拉圭人的现实,现实比小说更魔幻。《破角的春天》所表现的现实,将一个家庭的分离与国家的问题熔为一炉。作品更以文学的形式揭示了,人类总是监禁和流亡在自身之内的困境。虚构小说是拉美民族的私人历史,它比故事走得远,也比历史走得远,它赋予全人类一道分享的崇高与不幸。
它说:“没人能将春天从我的手中夺走。”
撰文|林颐
编辑|张进、宫子、李永博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