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昊苏评《晚清政治小说》︱瓶与酒之争:世界性文学何以在地
 2020-12-24
2020-1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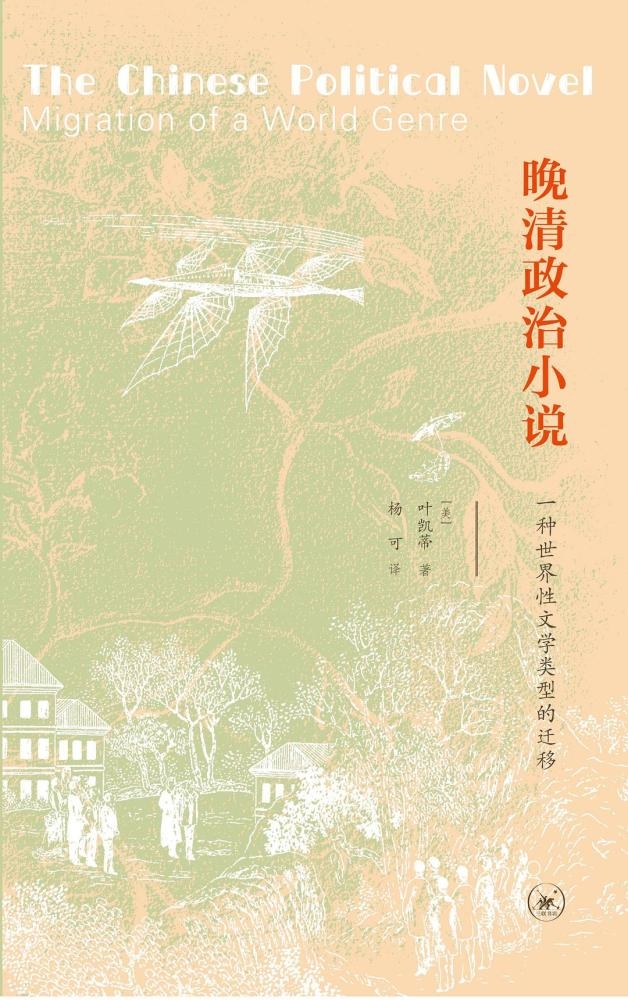
《晚清政治小说:一种世界性文学类型的迁移》,[美]叶凯蒂著,杨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9月出版,353页,定价45元
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中国现代文学”,时间的迁转当然是因素之一;而更重要的则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实际上为“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文学”(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而此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与创作体制都是相对西化的。在这一现代化的进程中,“瓶”与“酒”的不尽对应尤其凸显——小说这一类目,初则在史、子两部之间游移,及后不但有文言、白话之殊,更于近代出现传统“小说”与现代novel的不同;而小说史书写中,对具有政治意图的“目标驱动”型小说究竟应如何评价,也是一个不可绕过的核心议题。
叶凯蒂的《晚清政治小说:一种世界性文学类型的迁移》,正有助于对这一话题的深化认知。作者系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其学术旨趣在于探索文学、文化、艺术观念的跨国流动,并长期着力于从“世界性文学”这一视角观照政治小说,本书系在其博士论文Zeng Pu's "Niehai Hua" as a pol-itical novel—a world genre in a Chinese form(哈佛大学,1990)的基础上,拓展领域、深化研究而成。
全书分为上下二篇。上篇二章,重在追踪政治小说在欧美的生成及其向东亚的迁流;下篇六章,主要探讨这一文学类型与中国语境互动过程中的重塑策略。在重申政治小说世界共性的基础上,本书在结论中指出:“我希望本书已经证明,以文学作品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文学领域的武断区隔来指导研究的方法是富有成效的。只要我们接受跨文化互动是文化特征的原则而非例外这个提法,立马就会观察到明显的关联和互动。”(页316)而书中所述内容的延展性,其实不仅停留于晚清政治小说研究的具体学术议题,对省思当下小说史研究的分科与理念亦有裨益。
按现行的学科划分,晚清小说(某种程度上,这个话题可以扩充到“近代文学”)恰恰处在“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从事本领域研究的学者,其“学术出身”容有差异,研究理念亦不尽相同。如果做一个粗率且可能有些夸大的划分,也许可以这样说:面对晚清小说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某一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寻找历史的一贯性与连续性,善于考索晚清作家借鉴经典白话小说的那些文学资源;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长于关注及欧美、东亚小说发展的重要文学类型与文学体式,关注其“世界性文学”的一面。举例来说,在研究武侠文学这一特殊文类的时候,流行的论著常常上溯中国经典中的“武”“侠”理念与相关书写,但对于“武侠”一词的日本背景,以及日本所流行的武侠、剑客等类型小说缺乏更详尽的阐发。而从另一方面看,某些学者在论述近代小说叙事模式或小说家知识背景等问题时,对于古典小说中所提供的文学-文化资源亦常常简略带过,这也极易导致某些评价不够笃实确切。毫无疑问,两种研究视角应当兼顾,互相补充。但这在实际研究中却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作者在书中提示:“我们不能只把这种与世界的关联扔在脚注里,而是要充分地进行挖掘”(页6),并且关注到了“为了保证新东西能让人感觉亲近,晚清译者、作者、读者所熟悉的文学想象和以往的实践往往要回到传统的套路上”(页245)、“中国传统文学模式提供的熟悉的设置给读者期待设置了一个假定的框架”(页277)。提出文学类型的世界化,又顾及世界性文学在地发展的特殊规律,这一学术理念当然是非常通达的,而且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
众所周知,戊戌前后的时新小说已经颇涉当代议题与现代思想,此类作品多在租界区报刊连载,自有不少新锐论调。1895年傅兰雅(1839-1928)公开举办的“新小说”竞赛无疑当属先声。而梁启超(1873-1929)明确讨论了政治小说这一世界性文学类型引入中国的问题,并高度评价其具备“救国”的社会价值。从文学形式而言,这一时期提倡的“新小说”与传统白话小说也有较大不同。本书清楚地梳理了这一文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历程,并详细介绍了政治小说及相关理念是如何影响到中国学者的:以新型小说传播思想道德观念,并达成改良社会的功用,梁启超的这一观念渊源于日本,又与朝鲜、越南的政治小说提倡者产生了呼应(页98)。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高度关注到此类“新小说”的特殊性,所谈“晚清小说”起讫、范围不妨略有不同,但多数研究基本不以政治时段上的晚清为标志,而是以清朝最后十年具有新特征、新理念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参阿英《晚清小说史》、欧阳健《晚清小说史》)其中,政治小说的地位尤其重要。
何为“政治小说”?在著名的《佳人奇遇》序中,梁启超如是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乳,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以个人的阅历、见闻为小说,并希望以之转变社会风气,盖为梁启超所定义的“政治小说”。但这一定义实际上并未被类型化,“政治小说”何以区别于“谈政治的小说”,似乎并非泾渭分明。本书尝试进一步将政治小说的概念凝练化,认为政治小说乃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旨在为当下与未来提供发展方案,主要目标为描画国家理想政治前景,推向文明线性进化轨迹的一种特殊文体,并试图将政治小说与早有渊源的时事小说、谴责小说拉开距离。毫无疑问,此类写作样式与书中的政治理念均为古典白话小说所无,但这一趣味却并非仅有赖于舶来——晚明、晚清流行的时事小说,以及清代部分才学类、世情类小说,均有发挥政治议论,希图影响社会的创作旨趣。就本书所主要涉及的政治小说来看,其写法多数具有融汇“世界”与“在地”的两层面,而“在地”的文化资源,尤为本书下篇着力研讨之处。
政治小说中乌托邦书写的时代背景,固然有以未来回溯当今的创作,但亦往往托之古代。这在旧式小说中实属惯常:述古之目的即为讽今。如晚清朴学家俞樾(1821-1906)的戏剧《骊山传》,认为士兵持盾牌滚舞前进,可以战胜火器(第六出)。今天看来其观点虽不足道,但亦属曲园先生历史考证、治理观念的结合品,或可以说“提供了具体的指导”(页207)。复就传统体式的白话长篇小说来看,乌托邦书写也自有脉络。名声不甚显赫的蔡召华(1797-1870)《笏山记》(1908刊)一书融合世情、神魔、才子佳人诸体,属清代白话小说题材融合的典型之作,其核心宗旨是在幻想中的笏山地区实现建国、施政的政治理想。而还珠楼主(1902-1961)的武侠、仙侠小说,其入世部分亦往往涉及政治理念与大同思想等内容。再至金庸(1924-2018)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借武侠世界隐喻政治问题,则章回小说中的“乌托邦文脉”亦依稀可见。若不仅仅关注小说书写,那么“处士横议”和“十世可知”当然亦是上述小说家可以仰仗的重要思想资源。
当然,上述观点并非否认政治小说是一种“世界性文学类型”及其在晚清的创新性,亦并非说上述小说传统必然影响到晚清政治小说的创作。而是希望说明:在以名著为中心的阅读视野下,我们对清代小说创作传统的理解,有时容易稍嫌简略,这可能会对我们的在地视野产生局限。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当然直接渊源于日本“未来记”小说,然而书中对才子佳人情节的淡化,以及“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恰好又与传统小说-史学的复杂关系形成呼应,故其虽为中国新小说之空前创作,但若与传统小说相较对读,亦并非全无联系。晚清所再次兴起的讲史风潮,作者俨然有使之成为通俗历史读本,并劝讽国民救亡图存的创作意图,表现形式自由差别,但文化理念在小说批评史上亦不算特别新奇。是以,进一步探讨政治小说的定义及其在中国的在地性发展时,或许有必要继续考察此前小说创作情况与政治小说的可能联系,方能更好凸显政治小说这一文体的独异性,亦即本书所说的“并没有被翻译成既有的中国小说类型,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文学类型,带有它自己的叙事和编码策略”(页151)。对此,本书列举了丰富且有意义的例证(如文风、回目等),并将论述重点落在了小说楔子这一特殊叙事模式上。在作者看来,“新式楔子被作为一种高于且外在于小说正文的副文本加以改造,让作者得以建立一个将低俗的文学类型和崇高的救国新目标联系起来的框架。”(页305)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这部并未完成写作的小说因设置了完整的楔子,因此“把原来线性发展、结局不定的虚构故事替换成了结局在一开始就被设定好的线性的故事。凭借这种办法,许多刚开始连载、从来没有写完的中国政治小说甚至在故事还没发展完善时就已经收到了政治上的效果。”(页288)不过,《新中国未来记》这样的“未来记”体,虽属新构,形式仍有接近传统之处;而此外如吴趼人《新石头记》(1905)、萧然郁生《新镜花缘》(1907-1908)、陆士谔《新水浒》《新三国》(1909)之类的作品,在表面上依然以经典白话小说的续书为写作形式,这当然也代表了政治小说在地发展的一种特色:以“同人”的续书写法展示政治小说的“新”理念。对新理念和传统模式的融合,本书业已给出了相当多的精彩描述,但诸多文本之间的“互文”研究或许仍有推拓空间——部分议题实际已经溢出“政治小说”类型研究的范畴。
本书的写作似乎还面临另外一个挑战。“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一个假设,即政治目标只会对文学作品有损害”(页5)。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某种程度上亦是“纯文学”研究者的迷思。从小说的历史影响、社会功用来看,相关研究的学术价值毋庸怀疑;而认为“文学经典中排除目标驱动的小说”(页6,注释1),至少不尽切合中国小说的创作、批评理念。一部小说是否必须在政治和艺术之间二选一?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这里且不必多引古今小说批评家言,单举出一点便可作为反例:1980年代流行的“纯文学”“回归文学”之类观念,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表达。文学作品很难抽离价值立场只讲艺术技法;而考虑到宣传效果,作家一般来说亦不会彻底放弃艺术技法而专注价值驱动。而一旦两者同时出现,究竟何为根本意义上的“驱动力”就是颇为复杂难辨的问题了。就本书作者所担忧的问题来说,目标驱动也许并非问题,只有目标驱动而缺乏艺术才能,或许才是其难以成为经典的根本问题。更进一步说,“类型小说”本身即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评价标准,若批评者强行以一种看似普适却忽略各种文体不同特性的方式加以评断,这类理念恐怕过于粗放。
要言之,在本书的详细论证下,昙花一现的晚清政治小说,“成功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潮流纳入中国文学的脉络中来”(封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立基。这一话题看似学界并不陌生,但实际上提示研究者应将更多时间用于探索世界性文学在地发展的动力机制,而非简单地将相应材料置于脚注,不加详细挖掘。而书中所提示的诸多视角、话题,值得深入探索者似乎亦复不少。除此之外,本领域中更有趣味也更难以解答的问题或许是:长期面临名实不尽符合的“小说”一词,在近代逐渐远离四部分类的“小说家”,与纯文学叙事文体产生明确对应。但在这一过程中,古代之传统小说与舶来之现代novel,又在某些层面形成了争锋之势,这一不尽合榫,虽非如古人之“小说观”那样庞杂,但也对相应研究、创作产生了甚多影响。最典型者,如鲁迅(1881-1936)的《中国小说史略》,就在全书开头同时并置了古代目录家之小说观和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小说观;在小说史的脉络梳理和具体文本的分析评价中,也往往兼顾二者,至产生不少内在张力。此类问题似乎仍然影响着当下小说史的书写,若循其本,则当回归百年前的“现代化”环节,寻绎更多的解释可能。这,当然并非本书议题所能涵摄,但本书立足于晚清政治小说的深入讨论,或许足以为这一旧话题提供新的观察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