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松评《莎士比亚论政治》|愤懑还是变革?


莎士比亚(1564-1616)
TIRANT的谱系
起初,“暴君”(tirant)与暴政无关。古法语tirant衍生于拉丁文tyrannus,上承希腊文τ?ραννο?,最早引自小亚细亚的政治语言。赫梯文(tarawana?)、非利士文(séren)、伊特鲁里亚文(turon)存在若干古音近似的名词,泛指统治者,而非桀纣之属。“暴君”作为一个中性词转向负面意涵,最早可在希腊文献中窥见端倪。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批判暴君与暴政之前,“暴君”尚指不经世袭获取王位之人——不论掌权之后仁慈还是残暴。毕竟希罗多德笔下的巨吉斯并非昏君,甚至登基后略有作为,只因受王上胁迫偷窥王后,又听命王后杀死国王,因此在法理意义上,铁板钉钉是位“暴君”。
政治上置身美国语境、智识上浸濡莎学研究的格林布拉特先生,关注的自然是古罗马至近代早期英国的共和主义“暴君”概念。近四十年来,政治思想史家钻研弥尔顿和莎士比亚时代的“新罗马”修辞,形成了近乎公式化的共和主义暴君观。然而,现代思想中的“暴政”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非单指君主个人滥行专权,侵蚀宪政而已。“暴政”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政体:个人暴政、少数暴政、多数暴政。而不正义、不自由与不平等也并不一定在直观上残暴不仁。从托克维尔到密尔,自由主义思想也从未停止怀疑那些看似无害,实则具有高度支配性的社会风气和公众舆论。因此,不单是个人、私党和群体可以施行暴政,观念、文化、甚至是情感也可以“施暴”。诚然,性灵之暴,遗毒余烈亦深。
以全球维度视之,“暴政”也不限于城郭之内。传统共和主义偏执于在泾渭分明的政治区间内寻找合理的制度,往往遗漏了更广阔的正义界域。米诺斯向天父宙斯求法治理克里特,但在爱琴海施行暴政。雅典公民审慎熟虑,为异域国邦戴上枷锁。罗马宪政繁荣,却寄政治生命于征伐之中。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也在大西洋的波涛中为自己觅得了“海洋支配”的政治身份。莎士比亚剧中,正义与非正义的场域不仅是陆地国境,也是政治权威不明的水域——从《错误的喜剧》《雅典的泰门》《伯利克里》和《十二夜》到《奥赛罗》和《暴风雨》。探求航海时代早期的“国际暴政”,势必能为后世的帝国思想史、殖民与反殖民思想史和全球不正义史谱写一篇启人深思的序曲。
暴君的心灵
《暴君》一书的奇文异彩在于政治心理分析。莎士比亚的舞台戏剧一如柏拉图的“对话戏剧”,超越了制度探析,求索灵魂的形态。暴君施暴,源自暴虐的灵魂,如里昂提斯,“把整个国家叠合进自我之中”(108页)。在暴君那动荡的灵魂中,过度自卑与过度自信共存,以致达到了目的“却一点也不满足”(92、87页;Macbeth, 3.2.4-7)。尽管要暴君忏悔比要一尊雕像活转还难,但暴君也会在自白中喃喃:“我其实恨我自己。”(116页、79页;Richard III, 5.3.182–89)
愈是自厌自恋,愈是欲求不满,这是暴君的动机,也是他的负担。或出于受挫的性心理,或源自扭曲的家庭关系,暴君渴望专制权力证明自己。这种病态的自我关系不可避免地投射进社会关系,直到为自己敲响丧钟。暴君模棱两可,爱憎不定,鼓动手下揣摩圣意,却又接二连三过河拆桥,在自家后院树敌,又被敌人的幻影吓得魂不附体,显出原形。麦克白的晚宴上,众人不仅发现“陛下病了”(Macbeth, 3.4.53),更察觉出王上有罪。而昏聩的李尔王在被俘后还幻想连篇,泄露了他有意挫败的潜意识渴望:在小女儿看护下颐养天年(King Lear, 1.1.121)——许下这最后的愿望,他也在为忠魂送葬。
格林布拉特暗示:暴君心理与社群心理之间存在一股纽结,但并未指明其方向。诚然,理查之所以上位,也“取决于他周围人自我毁灭性的反应”,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集体失败”(57页),但其中关节何在?是暴政“直击人的心灵”(62页),甚至也如修昔底德笔下的战争一般,是一位“暴虐的教师”(III.82.2),颠倒了一切意义,“暴君化”了民众?还是广大民众“对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理解迟钝”(162页),所以蠢得上当受骗?民众为何支持暴君?作者承认,在莎士比亚去世七年后出版的对开本《理查三世》中,喊出“阿门”的不再只是市长大人,而是“全体”(68页;Richard III, 四开本3.7.238-219、对开本3.7. 238-239)。事实上,莎士比亚虽然描绘了为数众多的英雄平民——默默无闻的信差、仆人、士兵、警卫、工匠、农民,无名的古代罗马和现代伦敦市民(11、30页)——但他不信任平民,因为普通百姓“太容易被口号操纵, 被威胁恐吓, 或者被小恩小惠收买”(124页),所以不堪重任。反抗暴政,还要着落在菁英身上。
一如其他美国左翼自由派学者,格林布拉特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不愿自恃菁英,重居高临下训斥他的同胞何其愚钝,不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盼望“普通公民积极采取政治行动”,维持那份“可以被压制但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的大众精神”。当他日思夜想的“政治行动”和“大众精神”选上了自己深恶痛绝的特朗普时,《暴君》的作者惶惑了——如此惶惑,以至采取了切实行动:写出了这部书来。他思来想去,得出了一个结论:不是人民愚昧,而是暴君太狡诈,骗了他们。因为贫富差距悬殊,约克“利用最穷苦的人心中的怨恨”掀起了血雨腥风(31页;Henry VI, 3.1.349-357)。普遍而言,“陷入党派政治严重分化的社会尤其容易受到欺骗性的民粹主义的伤害”(160页)。但是社会的脆弱性——不正义的资源分配、党派分化和观念分歧、薄弱的共同认知——究竟何来?在暴君降世的前夕,自命进步的建制派菁英在做些什么?除了承认莎翁笔下的罗马“护民官”也“精于算计”(147页),格林布拉特的矛头对准的是暴君,而非孕育暴君的温床;是病症,而非病根;是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而非一手孕育了“民粹主义”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
暴君的时空
时间和空间维度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精妙所在。莎翁剧中,暴君暴起,但难以长久。一旦掌权,暴君的宏图壮志便堕落成了鼠目寸光,充满傲慢与偏见。他掣肘于反对派之间,因此迅速垮台,社会秩序得以重建。但暴君却满心以为,一旦坐稳宝座,他便能争取到更多,而非更少的时间。时间一旦充裕,他便可以收回阴谋篡政时做出的种种让步,回归自己私欲和初衷。在现实中,政客的嘴巴在竞选期间像一颗圣诞树,挂满了承诺,一旦选上便抛诸脑后。时间能成全正义,也能丢弃正义。
时间线的扩张与压缩是暴政内部的最大张力和隐患。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暴政并非一人独治,而是多流混杂,是在激情和权力的潮涨潮落之间,飘飘浮荡的瞬时政权。莎翁笔下的暴君也是瞬息万变的怪兽。在这种完全不可预测的集体生活中(161页),“时间不再是他的朋友。延迟是危险的”(76页)。暴君疑神疑鬼,恐惧过去;又三心二意,前途未卜。暴君盼愿“同时消灭未来和过去”,但这困难重重(90页)。最终暴君走向了毁灭,但创痕难以抚平,损失无法弥补(121页),永远留在了历史记忆之中。
莎士比亚植根于,但不限于他的语境。他无需沉默,但慎之又慎。时间上,他回归古代;地域上,他远渡他乡,因为与时政保持距离更易道出真相(3-4、19页)。但正因如此,莎士比亚也引入了广阔的地政空间。城邦内部,西西涅斯喊出“没有人民, 还有什么城市?”公民们附和:“人民就是城市。”(148-49页;Coriolanus, 3.1.177-94)这是莎翁在回归“城市”这一空间概念和“公民”这一法理概念的谱系纽带(cives, civitas)。他描述境外势力如何回国策划颠覆活动、国内精英如何与国外代理人秘密接触、暴君如何把国内矛盾转嫁给国际战争(6、40页)。意味深长的是,莎翁个人似也发了昏,以为发动境外战争能缓和国内情势。格林布拉特指出但不批评这一点,大约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存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吧!但为了洗白莎翁,作者猜想是赞助人怂恿了莎士比亚,而非文豪本意。这种臆测并非全无可能,但也剥夺了受资助的作家本人在政治思考中的施为性。将作家的政治动机都归咎于他的“赞助者”是一种拙劣的语境主义实践,其根本正是思想史学者一向怀疑的“唯经济基础论”。考虑到莎士比亚的教育、阶层与社交,他有条件地支持对外开战完全合情合理,甚至可能出自本意。
《暴君》在美利坚
若说莎士比亚是“旁敲侧击的大师”,尤擅“移花接木”“规避方法”和“用代码说话的技术”(3、12、158页),那么格林布拉特先生则完全没有掩饰《暴君》一书的美国政治语境(163页)。作者不但反复挪用当代政治理论家挂在口边却无法定义的“民粹主义”一词硬套近代早期的英格兰(31、143、146、160页),而且对特朗普个人的含沙射影也贯穿全书。在他笔下,叛乱首领凯德成了一具特朗普稻草人:他“承诺要让英国再次伟大起来”“承诺要排干沼泽”“荒谬显而易见,但它引发的笑声丝毫没有削弱其威胁性”(36页),无疑是讽刺特朗普的总统竞选。谈到麦克白时,作者分析暴君受性焦虑的驱使,对带有性暗示的奚落格外在意(83-84页),似乎是在奚落特朗普在初选时过度回应马尔科·卢比奥议员奚落自己的手掌太小。之后,格林布拉特又转向理查三世影射特朗普:“他一直很富有”“他喜欢谈论成功”“他对权力的占有包括对女性的支配,但他对她们的蔑视远远超过对她们的欲望”(46页),也是斯文的美国精英为特朗普贴上的不雅标识。读者读到美国学者对美国政客发泄的愤懑之情不一定产生不了共鸣。亦或许,读者能够想到,特朗普的人性缺点,譬如崇尚物化的“成功”概念,热衷于被世人喜爱——正如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中落魄潦倒的威利——是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过度商业化的产物,而非特朗普一己之疾。这位被本国建制派斥为“不美国”的政客,恰恰是美国社会风气的印证和美国政治心理的讽刺。
然而,这种跨时空的比较常常失准。凯德渴望成为一个富有的暴君(40页),但特朗普是个大富翁。事实上,特朗普自我合理化的主要机制便是反问美国同胞:我已经拥有了一切,现在却甘愿放弃闲适为你们服务,我图什么?这也是雅典贵族从政时惯用的套路。再有,格林布拉特讽刺政客衣冠楚楚,却戴着安全帽参加建筑工地的集会(146页)——这至多是在讽刺鲍里斯·约翰逊,毕竟特朗普出身房地产,理所应当顶着哈佛教授从未戴过的安全帽。作者怒斥民粹主义领袖“大胆又无耻”,发泄心中怫郁,但却搁置了更有意义的对比。譬如,凯德被约克利用,而特朗普上台后也在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中被共和党建制派架空。这恐怕比为了讽刺特朗普不是“成年人”,把英国王权和美国联邦“有足够多的成年人”与否相提并论(58页)更具建设性。
为了拉进与美国读者的距离,格林布拉特大量使用“助力者”“把不正常的东西常态化”这些美国新闻界流行的表述(57页)。许多情况下,借古讽今无伤大雅,譬如说勃鲁托斯自备“新闻发言稿”(129页),再如将莎翁笔下的弄人比作美国深夜节目中的脱口秀演员(100页)。但有时,这种倒植词汇的技艺更显笨拙,例如将约克和萨默塞特与“阿富汗军阀”比较(23页)、将击毙本·拉登与斩首玛丽女王相提并论(第9页),语境相去极远,不伦不类。再如,煽动英国农民出兵法兰西,这是一种扩张主义和军事主义,而非醉心本土利益而不愿涉外的“本土主义”。作者为了讽刺特朗普“本土主义”得到的瞬息快感,不惜用词失准。其实,过去与时下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处处可见。譬如,美国对外“反恐”催生了对内“恐伊”,触发了广泛的穆斯林歧视,大可以与英格兰的反天主教激进主义相互印证。凡此种种,都是可供作者开垦的“时下主义”议题。
莎学硕儒格林布拉特对美国右翼的反感既强烈又模糊。谈到古罗马的贵族党,作者称之为一个“右翼党”——其核心利益是不均等分配的“财政政策”。而米尼涅斯·阿格立巴则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136-137页)。美国大众读之,如览《纽约时报》。即便是为了可读性,这种套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左”“右”概念定义古罗马政治集团的作法也值得商榷。再如,作者谈及凯德不切实际的经济承诺,着力抨击了所谓的“巫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这是美国新闻界对里根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负面称呼。实际上,“里根经济学”与凯德口中既有些无政府自由意志主义,又有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愿景(Henry VI, 4.7.16)大相径庭。更何况,特朗普在前期竞选中一改共和党人的“里根经济学”说辞,转而贬损自由贸易。作者无法抵御嘲讽右翼的诱惑,但他的嘲讽经常打错了靶,甚至时空错置。可见泰斗级文学批评家不一定是富有卓见的政治理论家。
作者丝毫不掩饰对特朗普的鄙夷,挖苦他缺乏“成年人的自我控制力”,展现出“一个大孩子的自恋、不安全感、残忍和愚蠢”(142页)。他虽然承认特朗普对美国民众的吸引力,“我们一次次地被恶棍的肆无忌惮吸引”(69页),但却避谈这种吸引力的结构性导因。格林布拉特只提出了一种玄之又玄的心理分析阐释机制:普通人民受到畸形和丑恶的吸引(71页)。是的,《理想国》中,莱昂提乌斯也忍不住察看令人作呕的死尸(4.440a)。但若说特朗普令人作呕才赢了选举,恐怕太过荒谬。文学批评家立论而不论证,所以我们无从知晓他的思辨过程。“欺骗群众说”也罢,“吸引群众说”也好,格林布拉特无法解释美国大选的结果,却拒绝承认群众支持他认定的“暴君”是受系统性因素驱使、经过审慎熟虑之后的现实决定。因此,格林布拉特对《裘力斯·凯撒》那无可厚非的评价——“深入探索了心理和政治困境,但并未对此提供任何解决方案”(132页)无疑也适用于他的这部《暴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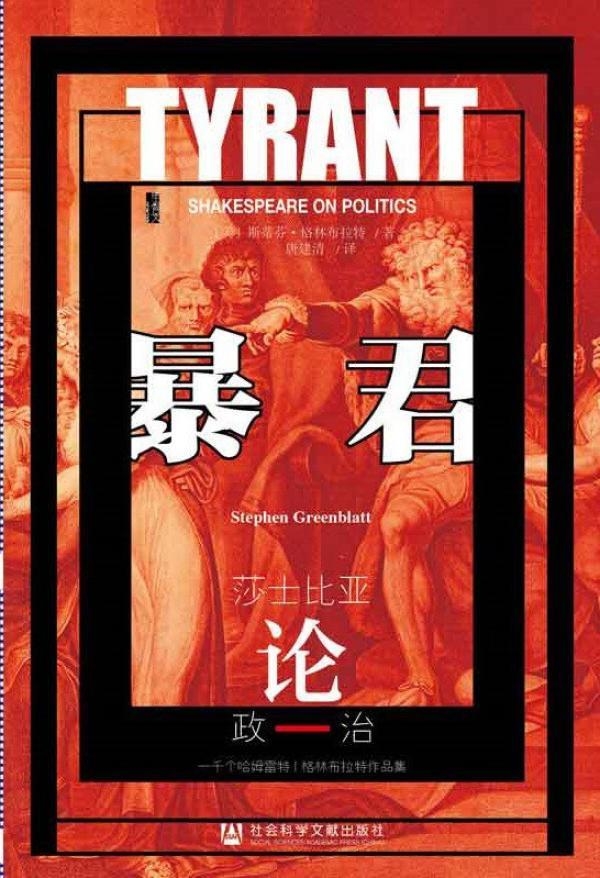
《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唐建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182页,52.00元
莎翁中译
《暴君》译文畅晓,文采可嘉,但亦非无改良空间。必要时,译者注应含纳更多信息,以助读者跨时空、跨语境理解原著。以“米达斯的妻子”为例,译者仅解释说米达斯点石成金(12页),但与“妻子”无关。事实上,作者指的是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之一则:米达斯的浓发之下潜藏着一对驴耳,敦请爱妻保守秘密,妻子忍受不住,一路小跑到小溪边,向水波一吐为快(958-988)——改写自奥维德《变形记》中关于米达斯仆人的一段叙述(11.172-193)。读者若不谙其典,恐怕要像格林布拉特先生读到“银样镴枪头”一般不知所云。此外,译者称米达斯是“吕底亚国王”,实为“弗里吉亚国王”。“驴耳米达斯”应在特洛伊战争之前,而弗里吉亚于公元前695年之后才归入吕底亚。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阿德拉图斯误杀了兄弟,逃往吕底亚寻求克洛伊索斯的庇护(1.35.3),自称祖父是“米达斯”。此“米达斯”非彼“米达斯”也。
译著包罗众多莎士比亚原文,珠玑弥珍。其中名词名句译法大致无差,但也不乏错讹。萨特尼纳斯(Saturainus)应为Saturninus。人名译法而言,译者仰赖朱生豪先生的中译本。朱先生是近现代翻译学名宿,但囿于时代限制,不通古典语言和欧洲语文,译名多可商榷。譬如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Caius Martius Coriolanus),同一译名之内英文和拉丁文发音混杂无章,缺乏连贯性。译著引用朱先生的原著译文,也时有不章。麦克白认为夫人无畏的精神“只应铸造”男性,而非“应该铸造一些”男性(84-85页;Macbeth, 1.7.72-74):“Nothing but males”之排他性是此句关键。“Thou troublest me”(Richard III, 4.2.99)是“你令我烦恼”,而非“我真麻烦”(75页)。“Considerate eyes”(Richard III, 4.2.29-30)是“细察入微的眼睛”而非“鼓起眼珠”。理查在追求到安妮时“沾沾自喜”道:“哪有一个女子是这样让人求爱的? / 哪有一个女子是这样求到手的?”(69页;Richard III, 1.2.228-229),其中“in this humour”并不指追求的方式,而是生理和心理上的情绪——理查见到安妮在积愤鄙夷之余还接受了求爱,也感到讶异。
此外,“schoolboy”概念的诠释也出现了偏差。这个词出现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2.7.139)最著名的一段台词“世界是一座舞台”(All the world’s a stage),本书所引则是《亨利六世》的一句话:“像小学生一样,能受你们的摆布。”(Henry VI, 1.1.36)朱先生对英国文化史语境知之甚少。莎翁笔下的“学校”指的不是“小学”,而是渊源甚久、延存至今的语法学堂。莎士比亚自己在斯特拉福德度过的“schoolboy”生涯近乎是他戏剧创作的全部积淀所在,是一个完整的教育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阶段。
概而述之,在翻译《暴君》这样的当代作品时,新一代译者尊老敬贤固然是美德,但也不必为此搁置校对版本、勘磨译文,甚至审慎斟酌的机会。毕竟后人用功旨在超越前人,而非步权威之后尘。
《暴君》之后?
《诗》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警示暴君暴政不得善终。“阳风习习而熇熇,群生闵懑而愁愦”,格林布拉特先生《暴君》一书充满了“闵懑”和“愁愦”,而没有“大谏”。时下美利坚的“暴君”并非理查三世,也不是麦克白,而是在庞大的民族国家和国际秩序中左右逢源的利益代理人。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变革,申饬暴君再酣畅淋漓,也无济于事。
正如自负而死的安提戈涅与克瑞翁、各执一词的约克和萨默塞特一样,社会中的人偏执于局部真理。格林布拉特先生坚持的是美国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的是他心目中的右翼民粹主义暴君,也是美利坚近乎半数选民认可的执政官。暴君非暴,只是腐朽深渊之前的一面海市蜃楼。抛却现代社会的暴虐诸相,立一具前现代式的暴君稻草人,狠狠抽打,这是直觉上的正义,也是智识上的懒惰。病得久了,病根不除,恐怕连病人也对病症麻木了。
正如所有不具反思性的愤懑一样,或许回归莎士比亚的暴政理论也只是一瞬之思。重掘莎士比亚对暴君的批判,究竟是自命先知的满腹牢骚,还是根本性变革爆发之前的先锋号角?是油然而生的不满,还是澄思渺虑的批判?是反应,还是革命?这是读罢《暴君》,所有灵魂深处都潜藏着暴君,却又在众生相之间抵抗暴君的人们不可避免的一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