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来到美术馆|凌越:沉默也是一种美德

1985年,凌越正在读初二。一天课间休息,他躺在操场草地上静静望着天空,产生了一种轻微的幸福和喜悦之感,几个句子不经意地掠过脑海,他吃了一惊:这不就是诗吗?
回到教室,他已经听不进去课了,于是找出一本作业本翻到空白处,把刚才闯进脑海的句子记下来。
“那首诗肯定很幼稚,但是这个感觉奠定了我成为诗人的基础,是我成为一个诗人最根本的动力。”“是我第一次体验从身体经验向精神世界跨入的感觉。”前不久,在做客上海民生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时,凌越如此谈及他最初的诗歌写作经验。
三十多年来,凌越写诗,写评论,也做翻译。出版有诗集《尘世之歌》《飘浮的地址》,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见证者之书》《汗淋淋走过这些词》,和梁嘉莹合作翻译《匙河集》《兰斯顿·休斯诗选》《赫列勃尼科夫诗选:迟到的旅行者》等,主编“俄耳甫斯诗译丛”。
凌越的诗歌特别注重戏剧性,强调“直接的力量”,追求词语的“颤栗”效果,同时富于创造性和深度,多角度地击中生活的要害之处。他对当代诗歌中过于呈现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保持警惕,也对苦难书写、滥情表达表示不满,而对于很多诗人写到一定阶段后追求“大诗”“长诗”,凌越并没有兴趣。他说自己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要写什么传世之作,他所希望的就是老老实实一行一行写,“写得好的三行诗,比写得不好的三百行诗要好。”

凌越(右)
年少时期,他就知道什么是好诗了
凌越有个比他大20岁的堂兄,曾参加过《诗刊》社“青春诗会”。堂兄为人儒雅,在家族里很受尊敬。每年过年家族聚会时,凌越就在小板凳上听堂兄高谈阔论,听他谈文学典故,无形之中,给他树立了典范:做一个诗人挺好的。
在这种氛围下成长的凌越,经历过初中那次最初的“诗歌震颤”后,1988年他考入了华东政法学院。尽管对法学毫无兴趣,但在华政,他认识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诗人,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朱朱。
一进大学,凌越就开始寻找同道。他问同乡,华政有没有诗社,被告知朱朱搞了一个。凌越完全不知道朱朱是谁,是男是女。顺着同乡手指的方向,凌越看到了一个在操场上踢球的男生,挺瘦的。这是凌越对朱朱的第一印象。
后来,他参加了朱朱他们搞的校园诗歌大赛,拿了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奖品是几本诗集,包括叶芝的《丽达与天鹅》《美国自白派诗选》等,凌越至今保留着,“不是因为这个奖,而是确实是好书。”但是这个奖让凌越认识了更多爱好诗歌的朋友,包括在当时已经名声在外的陈东东、宋琳等。
“很年少就认识这些很好的诗人,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就是我知道哪些是最好的诗人,什么是最好的作品,应该看哪些书。”凌越说。在阅读资源相对不易获取的年代,凌越在大一大二时就读到了史蒂文斯诗集、狄兰·托马斯、艾略特、《美国诗人50家》、《诗人谈诗》、《美国现代诗选》等优质诗歌,让他很快及进入到一种当代诗歌写作语境。
在诗里,他给自己戴上了面具
然而直到在广州工作期间,凌越才留下第一批诗歌作品。
1994年年末,凌越来到广州一所高校任教,有了一间自己的教师宿舍。宿舍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陈旧的单人木床,一个笨重的木质写字台,还有两个高大的储物柜,里面只有书。
在这间屋子里,在那年年末的许多个深夜,凌越写下了自己愿意保留下来的最初的一批诗作,并没有急于将这批诗作示人。它们保存在笔记本里,悄无声息无人知晓,但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然确定,凭借这些诗他打消了“我能否成为一个诗人”最后的疑虑。
不急于示人成为了凌越写作的一个习惯。在他看来,诗歌是内在的、秘密的声音,拿给别人看总有一种裸身的感觉,让他感到不自在。这个习惯,后来与他的写作风格也发生了联系。
如何在诗歌中掩饰这种裸露感,有的诗人喜欢使用反讽来化解过于袒露自我的尴尬,凌越找的方法则是借用戏剧中的面具手法:假装是另一个人在写。“哪怕写得很露,我也可以推脱是别人在说话。”
这种手法国内并不多见,但在西方诗歌中源远流长,比如凌越与其夫人梁嘉莹翻译的美国诗人马斯特斯的《匙河集》,就是一本戏剧独白诗集。
凌越的“面具诗”有些具有明显的标识,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在特维尔大街普希金纪念碑前》,比如《秋瑾出走》,但更多是没有明显提示的,“因为这毕竟是我的诗,那些人物面具不过是我想象力的跳板。”
一开始的目的只是规避个人的内在尴尬,但后来,凌越发现,戏剧面具还可以解放想象力,可以超脱个人身份和经验的局限,化身为工人、出租车司机、大作家,化身为女人、小孩和老人,各色人等,通过想象他们的生活,凌越的世界也得到了无限的延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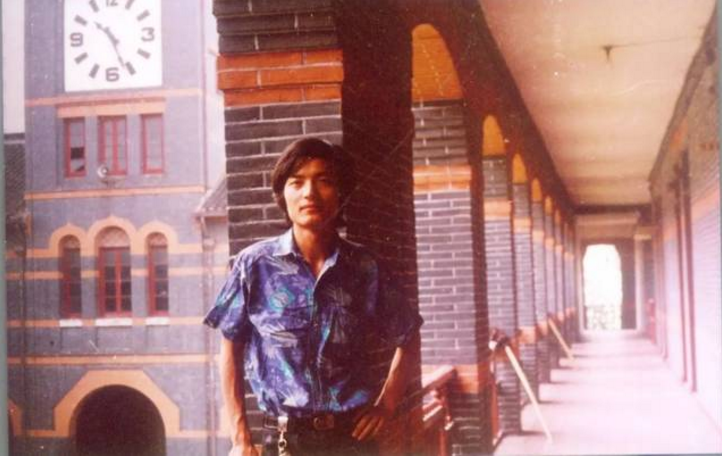
1993年凌越在上海
有些诗人对所有事物都满含热泪,这不对
写作时,凌越在诗中隐遁个人的身影,写完后,他也不愿过多进行自我阐释和文本剖析,但这并不是因为害怕尴尬,而是大概出于一种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的理念:诗写完了,就和作者没有关系了,如何理解,全凭读者。
但对于整体的写作脉络,他说其中一条就是在写热情、直率的诗歌,以至于不少读者都从其诗歌中强烈地感受到真挚和有力。
无论是真挚还是有力,在凌越看来,都是在走不同的钢丝。
“不是我想写真挚的诗就可以写出来,每一个好的品质就是钢丝,你经常会掉下去的,掉到哪里去?真挚的旁边就是滥情,有力的旁边就是粗糙。很多走真挚路线的诗人,写到后来都很滥情,对所有事物都满含热泪,这不对。”
凌越认为,戏剧性与真挚很好地构成了互补:戏剧性化解了真挚肯能带来的滥情危机,而真挚给予了戏剧性以稳定性基础,避免其因为脱离个人经验而带来的不真实感。
对于后者,凌越以艾米莉·勃朗特为例进行说明。艾米莉·勃朗特29岁就去世了,她没有太过丰富的人生经验,甚至没谈过恋爱,但在她在诗歌里,建构了一个帝国,有王子,有公主,有逃亡,有背叛,“丰富得不得了,你能说是编造吗?这些诗都特别真挚、强烈。这个强烈是她内心的激情,她就是一个戏剧化的诗人。”
对他人的痛苦保持静默是一种最恰当的尊重
这种诗歌观念,乍看之下,与中国当代诗坛主流的日常性书写存在一定距离,但事实上凌越并不是反对日常性书写,或者个人化写作。
在他看来,诗歌里面有很多的因素,某一种因素强调得过分了,都是错误的。
“关键是你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强调这个因素。现在华而不实被很多写作者所抛弃,但是很容易又流于鸡零狗碎、鸡毛蒜皮。没有抽象的东西,也是个问题,现在我觉得需要抽象。最好的诗歌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它把各种因素全部综合在一起,有坚实的意象,有抽象的思考。”
同样的,他对当下很多中国诗人越写越政治化也表示了保留意见。这种保留意见集中体现在《题一帧照片》这首诗里。
2019年,在新加坡旅行期间,凌越在一家莱卡相机专卖店看到了一个摄影展,他被其中一幅深深吸引:照片中,几个青年坐在哈德逊河畔谈事情,看起来非放松、开心,而远处的背景就是世贸大厦被撞之后冒气的滚滚浓烟。照片摄于2001年9月11日。
这张照片让凌越想到勃鲁盖尔的名画《伊卡洛斯的坠落》,“天使伊卡洛斯从天上掉进大海,旁边的农民照常收割庄稼,一切如旧。灾难在孤立地发生。”在凌越看来,勃鲁盖尔这幅画没有批判什么,不是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式的批判,只是在描绘我们人类的事实而已。
凌越在《题一帧照片》里试图传达类似的意思。他用白描的手法再现了照片里的场景,在最后一节他写道:“当飞机撞向塔楼时,/五位青年也曾站起,手搭凉棚/朝曼哈顿方向张望。现在他们安静下来,继续刚才有趣的话题。”
“我们人类对于他人的痛苦很难真正进入。那种苦难的诗,让人看得不舒服,你就那么大同情心?现在中国这样的诗很多,经常写得让人很不喜欢。你这也同情,那也同情,对不起,你没有资格同情,你没有能力同情,你进入不了,就是这样的,我们个体的孤独、苦难,非常的孤立,而其他人的生活仍然在继续,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事实。”在凌越看来,与其在诗中、在朋友圈中营造一种对远方苦难的关心,还不如真正地关心一下身边的父母妻儿。
“对于他人的痛苦,我们保持一种静默,语言上的静默,可能是一种最恰当的尊重。”凌越说。

凌越最新诗集《飘浮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