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苏轼为什么都曾被人狠批?

从孔子删诗、编订《诗经》开始,汉语诗学便在理性与诗性、审美与功利、政治与艺术之间找到了独特的连接与平衡,并由此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审美章程,引导乃至支配了汉语诗歌的诗兴、诗意与趣味。
《天人共生与道文兼济——汉语诗学样本》中,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泽认为任何路径的选择都意味着一种限定,意味着对特定秩序与系统的认同,包括他的局限性,审美的“偏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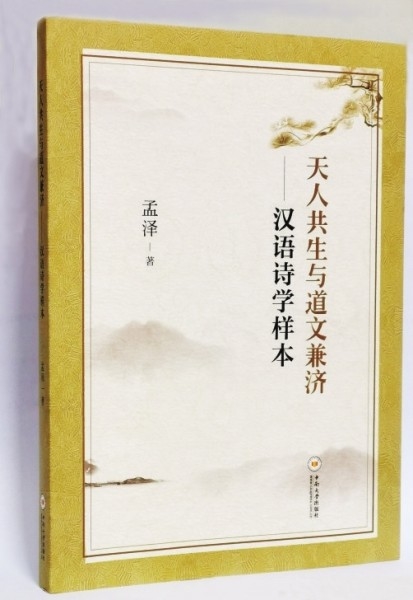
或许,就因为这,汉语诗歌发展到105年前,诞生了一个叫“新诗”的变种,只是,稍嫌遗憾的是,一旦遇上极端的情境,这个变种就面目全非。

孟泽。组图/记者李林冬
王船山曾批评杜甫“追求私欲,非君子之情”
唐大历五年,也即公元770年,58岁的杜甫在长沙遭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兵乱——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崔瓘,带领一班骄兵肆虐长沙,演出了一场“兵变”恶剧。
“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发中夜,高烟焦上苍。至今分粟帛,杀气吹沅湘。”杜甫诗《入衡州》中记录了这场兵乱。
杜甫在好友苏涣的帮助下,上船离开了杀气笼罩的长沙的。他沿湘江北上,准备投奔在郴州当官的某个亲戚。
杜甫的晚年,多是在躲避各种兵乱、到处投亲靠友中度过。他的这些经历,多被他写入诗中。这一次,他在衡阳停留的时候,也不例外地写了些相关的诗,除《入衡州》外,流传较广的还有《逃难》一诗:“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
这首非常写实的诗,写尽了杜甫的凄凉。好在杜甫毕竟有诗名,漂泊路上总会遇到雪中送炭的人。这次,在去郴州路上,给他送温暖的,是耒阳县令聂某。为表示感谢,杜甫写了首标题很长的诗《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
目前所知,这是杜甫最后一首答谢诗。写完这首诗的他并没有按之前的计划去郴州投靠亲戚,而是让船夫掉棹往北,再次经过衡阳并继续往北,最终在这一年的冬天病逝于潭州到岳州的船上。
杜甫离开衡阳35年后,衡阳迎来了从郴州去江陵赴任的诗人韩愈。彼时,韩愈的好友邹儒立恰好担任衡州刺史,韩愈便在衡阳逗留了半个月左右。这半个月,韩愈诗兴大发,写了20多首诗。其中,包括对衡阳影响深远的《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
正是因为这首诗,让一个叫李宽的甘肃人步韩愈后尘,去了石鼓山上的合江亭,并被湘江、蒸水、耒水三江环绕、烟波浩渺的美景所吸引,留下来结庐读书,创立了著名的石鼓书院。
时间再过去800多年,衡阳府城南回雁峰一个叫王夫之的少年入读石鼓书院。后来这个少年成长为“真能懂得文学”的哲学家王船山,说他“真能懂得文学”的,是《中国诗史》的作者陆侃如、冯沅君。在这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伉俪眼中,中国古代懂得文学的哲学家只有三位,另两位是孔子和朱熹。
如果杜甫晚年在衡阳的那段经历及他类似的经历没有写入诗,抑或他的诗写得没那么好,那么,他及他的诗就不会在900多年后被“真能懂得文学”的王船山拎出来批评了。
王船山不仅批评了杜甫,还批评了韩愈,且并没有因为这二位曾是衡阳的过客而有丝毫的留情:“若夫货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设于醉饱之情,腼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甫失其心,亦无足道耳。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
诗圣、诗史杜甫的诗,在王船山看来只是为追求私欲,非君子之情;且又矫饰为文,有悖诗道,对后世有着很坏的影响,以至于“诗遂永亡于天下”。
闻一多说苏轼的天才是笑话、是罪孽
和王船山对杜甫的狠批类似的,还有闻一多对苏轼的批评。
1933年,闻一多慷慨解囊,资助臧克家出版诗集《烙印》。在《烙印》的序言中,闻一多认为臧克家是个和孟郊类似的诗人。闻一多由孟郊谈到了批评过孟郊的苏轼。
苏轼流传下来的文字中,评到孟郊的有四处。闻一多在《烙印》序言中主要引用的,出自苏轼的《读孟郊诗二首》(其一)。
“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蚏,竟日持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
苏轼对孟郊这样的批评,闻一多先说“并不怪他”,接着说“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才是。”接着,闻一多对苏轼火力全开:“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象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鳌’也好,是‘蜇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至于苏轼的丰姿,苏轼的天才,如果有人不明白那都是笑话,是罪孽,早晚他自然明白了。早晚诗也会‘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1933年,闻一多还再版了他自己的诗集《死水》。《死水》是闻一多1925年7月归国后两年的诗作,共二十八首,初版于1928年。这本诗集中的诗,被认为是诗人面对丑恶现实所发出的深沉的抗争。
《死水》的装帧是闻一多亲自设计的。封面和封底全部使用无光黑纸,在封面左上方和封底右上方各设计长方形金框,框内上方各横印“死水”二字,下方印“闻一多”三字。整个封面使用金黄与浓黑两色,表达出庄重典雅和深沉宁静的风格。书中设计的环衬,图案是三队高举旌旗、手持长矛盾牌的武士们,他们跨着战马冒着飞矢前进。此时的闻一多,是诗人,是学者,也是斗士。
“现代艺术家精神深处的古典血脉与传统基因”
“闻一多曾经非常欣赏唯美的东西,但是抗战时期,他觉得苏轼写出的那些美的作品是非常可恶的,就像炮火连天的时候,一个美女穿着旗袍在街上显摆,是可耻的。”孟泽和记者聊到他的新书《天人共生与道文兼济——汉语诗学样本》时,解释闻一多批评苏轼时的语境。
在《天人共生与道文兼济——汉语诗学样本》中,孟泽对闻一多批评苏轼以及王船山批评杜甫等人做了更全面且更贴近的解释:“在激烈的时代语境中,当闻一多不再以独立的个人身份和自由的审美意识,而是以某种有着越来越明确的政治归属的集体身份与公共意识看待文学艺术时,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性诉求,便轻易地成了文艺的价值与最高目标所在。这也正是王船山、曾国藩在‘道’‘文’之间的取舍的秘密,他们同样以高出个人身份的整体身份看待艺术,以至最终取消艺术的个人性、私人性作为‘道’‘文’兼济的方向”。
闻一多曾说他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对此,孟泽认为其“新诗之中”的身份,是艺术家、学者;闻一多“新诗之外”的身份,不仅是他有资格作为新诗选家,而且他也有资格参与历史、参与现实的改造。最终,闻一多用生命写就了一首悲壮的“行为主义”之诗。
孟泽认为从闻一多身上,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中国现代诗学的单纯与复杂、贫困与丰饶,以及可以发现“现代艺术家精神深处的古典血脉与传统基因”:“当诗的旨趣与诗人的使命上升到民族国家人类的解放时,诗人和理论家所指望的就不再是新诗的建构,而是自我的建构、民族国家的建构,不再是诗的境界,而是生命的境界、道德政治的境界。这是新诗、新文学、新艺术的最深的动力和动机。这或许不只是新诗的个性,也是整个汉语诗歌的个性,整个汉语世界文学艺术的个性。”
对话
文化巨人常常是与自身传统文化面貌迥异的人
潇湘晨报:为什么中国诗歌会特别具有“人间性”和“社会性”?“戴着镣铐跳舞”是怎样成为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诗人的一种自觉的?
孟泽:中国诗歌具有特别的“人间性”和“社会性”,这是学贯中西的现代学者许思园先生说的。这种特点自然跟中国的文化传统、宗教传统有关,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的文化,世俗化的进程开启得很早,程度也很深。在“天”与“人”、“道”与“文”的关系上,事实上是以“人”“文”为本的,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天道”是基于“人道”的,“天文”依归于“人文”。这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但由此奠定了汉语诗歌的美学方向,也导致汉语世界的文学艺术与政治、道德、教化有特别深的关联,特别多的“事故”。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中国,也表现得特别分明。“带着镣铐跳舞”,这是关于诗歌写作的一个隐喻式的说法,任何诗歌都是如此,没有限制,也就无所谓自由,审美的自由同样是在特定的限制中获得释放的。汉语诗歌有自己特别的“镣铐”,汉字汉语有自己特别的形声意韵,有自己特别的节奏和蕴涵,汉语诗歌因此也就有它特别的风格和气质。
潇湘晨报:孔子删诗,还留下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风”;王船山否定杜甫,说“杜甫之滥百于香奁”;闻一多说苏轼的天才“是笑话,是罪孽”。这样的“进化”,是偶然还是必然?
孟泽:孔子是真正懂得艺术的,“诗三百”,第一首就是《关雎》,证明孔子对于人类情感世界的理解是通达和透彻的,孔子之成为“万世师表”,并不是历史的误会。他关于人的成长和建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真正颠扑不破的伟大发明和总结。船山否定杜甫,基于他特别的经世立场和文化抱负,基于他在天倾地坼的晚明剧变中对于“圣贤豪杰”的期许和指望,并不是他不懂艺术,船山有非常高明非常精彩的美学思想,很多方面甚至是唯一的。闻一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于唯美主义,对于苏轼的审美风度的舍弃和批判,同样有特定的含义,不是出于无知粗暴,这涉及时代潮流,也涉及现代知识者的自我设计,一言难尽。
潇湘晨报:您在《天人共生与道文兼济——汉语诗学样本》前言中说“新诗”之初,“欧化”“中文写的外国诗”等不同说法的背后,是汉语诗歌从此有了一种自身传统之外无法回避的参照、动力和源泉。第一首白话新诗诞生到现在,已经有105年。就您的观察,汉语诗歌这105年来在其无法回避的参照、动力和源泉的影响下,有没有发生改变其根本的变化?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孟泽:“新诗”的发生,跟传统诗词曲的转变,不是一回事,是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标志之一,没有“西学东渐”,就不会有“新诗”。“新诗”在精神特征与美学特征上与传统诗词,大异其趣。但既然是用汉语写作,则必然摆脱不了汉语表达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新诗”的未来端赖于创造。
潇湘晨报:您在书中说,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当时为新文艺及其生长发育提供了最宽容的视界,提供了最合乎文艺本质的定义与诠释。周作人为什么能这样,这和周作人的阅历及知识背景有关?
孟泽:这与周作人的知识结构和教养有关,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类学者,自己对于文艺和宗教的理解,是基于对“花草虫鱼”的理解,对于生命的体贴,尽管他自己也知道,他毕竟是中国文化养育的,骨子里仍然是“道德家”。
潇湘晨报:1998年,诗人韩东发起过“断裂”行为,希望能做到和非文学的干扰因素保持距离。这个声音,最初好像很响亮,但现在很难有人记起。这是不是证明了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发生“断裂”的土壤?就像周作人尽管对于文艺的非道德性与个人性有着足够的宽容,但他骨子里、文章里仍然是“道学家”的模样。
孟泽:是的。一种文化有一种文化的“宿命”,任何创造都无法摆脱这种“宿命”。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我们偷懒、放任自己的理由,那种传承光大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思想家、艺术家,一定会是某种意义上的自身文化传统的“敌人”,好像是诗人博尔赫斯说过,那种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巨人,常常是与自身传统文化面貌迥异的人。这不是语言游戏。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