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阿多诺:存在主义向内心世界的退缩,是一种虚弱的反抗


题图: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阿多诺一生著述甚丰,涉猎广泛,主要著作有:《否定的辩证法》《启蒙辩证法》《美学理论》《最低限度的道德》《新音乐哲学》《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文学笔记》等。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永康由德语直译的阿多诺著作《本真性的行话——论德意志意识形态》。
《本真性的行话》是阿多诺批判20世纪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存在主义思潮的著作。本书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布伯、雅斯贝斯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阿多诺分析了存在主义者圈子内的一种极端“内向性”的用语,表明其所指直接就是“虚无”,而这又导致了一种极端主观化的内在经验,丧失了所有的客观性和创造性的主体活动。阿多诺认为,这种向内心世界的退缩,尽管也可以被视为对物化的外在世界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是虚弱的,最终只是对外界的虚假的隔绝,从而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接受。阿多诺主张德国古典时代的理性精神,主张创造性主体与客体的辩证互动。本书最初的意图是作为《否定的辩证法》中的一章,对应着“与本体论的关系”,但因体量超出了计划而独立成书。本书可被视为《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入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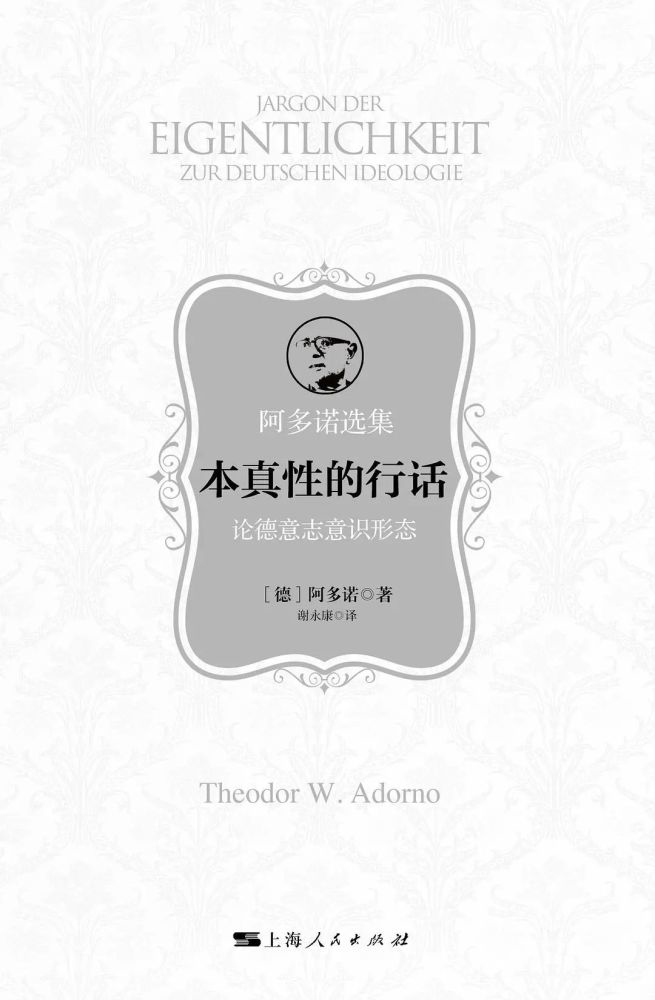
《本真性的行话》试读
文 | 阿多诺
20世纪20年代初,一群从事哲学、社会学以及神学研究的人曾计划筹办一次会议。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改变过信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重新获得宗教,而非宗教本身。他们所有人都对当时仍然主导着各个大学的唯心主义心怀不满。哲学促使他们出于自由和自主而选择了“实证神学”——正如克尔凯郭尔已经如此命名的那样。但是与其说他们对特定的教义,即启示的真理内涵感兴趣,不如说是对“意向”(Gesinnung)感兴趣。当时有一个被这个圈子吸引的朋友并未获得邀请,这还让他小有不快。人们给他的暗示是,他还不够本真(eigentlich)。因为他在面对克尔凯郭尔式的飞跃(Sprung)时犹豫不决;他怀疑,通过自主的思维唤起的宗教会因此而低思维一等,并否认自身是绝对者,但宗教按照其本身的概念来说却是想要成为绝对者的。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反智的知识分子,通过排斥一个不承认他们之间互证的那种东西的人,他们便确证了一个更高级的共识。他们在精神上捍卫的任何东西,都被登记为他们的伦理风尚(Ethos),好像一个人追随一种更高境界的学说,便提高了其内在的精神层次似的;好像在《新约》里面没有记录下反对法利赛人(Pharisaer)的内容似的。——40年之后,仍然有一个退休的主教在一场新教神学学院的学术会议中愤然离场,因为一个受邀的发言人质疑圣乐在今天的可能性。他肯定被告诫过,或者他自己也觉得,要与那种不愿签字认同的人分道扬镳,不与之为伍:好像批判性的思想没有任何客观基础,而只是表明主观错误似的。他这一类人将“自立为正当”[用博尔夏特(Borchardt)的话说]的偏好与对其自身的反思进行反思的害怕结合为一,好像他们都不完全相信自己似的。他们一如既往地怀疑,他们称之为具体物的东西,有重新错失给可疑的抽象的危险,而这种抽象是不能从诸概念中剔除的。他们以为,具体性要通过牺牲而获得承诺,尤其是通过理智的牺牲而获得承诺。异教徒们隆重地将这个圈子称为一群“本真之人”。当时,《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还远未出版。在这本著作中,海德格尔直接以生存论存在论的方式将本真性(Eigentlichkeit)作为一个专业哲学术语引入进来,这样他就断然地将那些本真之人很少在理论上竭力追求的东西浇铸到哲学之中;他由此而赢得了一批追随者,他们都含混地满足于那种本真性。通过他,教派的各种苛求变得可有可无。他的著作为他赢得了声望,因为它敏感地描述出了1933年之前知识阶层的隐秘渴望的走向, 并将这个走向诚实而负责地呈现于眼前。直到今天,在海德格尔以及操着他的语言的追随者那里,神学语调仍在回响,尽管这种回响在逐渐减弱。因为那个年代的神学嗜好已经渗透到了语言之中,远远超出了当年自诩为精英的那些人的范围。但是同时,本真之物的语言所贡献的,毋宁说是对本真性的崇拜(Kultus),而非基督教的崇拜,即使有时候由于暂时缺乏另一种可支配的权威性之故,他们这种崇拜看起来也类似基督教的崇拜。先于对特殊内容的考虑,这种语言对思想进行塑形,让这种思想自身去适应征服的目标,即使在它想要对此目标表达反抗的地方也是如此。绝对者的权威性由被绝对化了的权威性推翻了。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是它所是的那个阴谋(虽然它的确是),它也是在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发展趋势中发源起来的。语言为它提供了避难所;在其中,正在蔓延的灾难表现得好似拯救。
在德国,一种本真性的行话被谈论更甚于被书写;它是社会化精英分子的标志,是精致高贵和宾至如归的合一,是一种作为高级语言的亚语言。它从哲学和神学(不单纯是新教学院)开始延伸,经教育学,经业余大学和青年团体,直到经济和行政部门的代表们那种高雅的谈吐方式。这种行话充斥着人类深层情绪的伪装,然而却将自身标准化得好似它公开否认的外部世界一样;其原因部分在于它的大规模成功,部分也在于它通过那纯净的特性就自动地设定它的信息,并借此将自己与那本来赋予了它灵魂的经验阻隔开。本真性的行话操弄着为数不多的词汇,发出闭门羹似的信号。在此,本真性本身并不是最紧要的;紧要的毋宁说乃在于它照亮了行话得以茂盛发育的天空,以及秘密滋养着这行话的意向。首先,“生存状态的”“在判定中”“委命”(Auftrag)、“召唤”“照面”“真正的言说”“陈述”“关切”(Anliegen)和约束等就足以堪称典型;还有为数不少的这类非专业术语可以被添加到这个清单中来。有一些术语——例如《格林词典》(Grimmschen Worterbuch)介绍过的“关切”,本雅明(Benjamin)还无辜地使用过——自从掉进那个紧张区域(Spannungsfeld)之后(这个词也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才染上了这种色彩。我们不是要编制一份畅销高贵名词的“禁用词汇目录”(Index verborum prohibitorum),而是要探究它们在这种行话中的语言功能。当然并不是这种行话的所有词汇都是高贵的名词;有时候它也会拣起平凡的词汇,抬举得高高的,按照法西斯主义的习惯将它们镀上青铜色,这个习惯聪明地将公民表决和精英主义混合在一起。那些卓尔不凡的新浪漫主义诗人,如格奥尔格(George)和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根本不用这种行话来写散文;反而是他们的某些代理人如冈多尔夫(Gundolf)才会这么干。这些词汇只是通过它们所否认的星丛(Konstellation),通过每一个单个人唯一性的举动才成为这种行话的高贵名词。单个词汇失去的魔力,犹如通过某种措施以国家调控的方式被购置回来。单个词汇的超验性,是一种第二位的、由工厂生产供应的东西:失却了的原初性的怪胎。经验性语言的诸构成要素(Bestandstucke)的持久性被操控着,好像这些构成要素就是真正的和由启示而得的语言的构成要素似的;神圣词汇在经验上的亲切性伪装成了说者和听者都能感觉到的切身之近。穹顶被机械地喷涂,原子式的词汇未经改变就被用来做装饰。通过这种行话所谓的“架构”(Gefuge),它们获得了相对于这个架构的优先性。这种行话从客观上说就是一个体系,它将结构混乱,以及语言崩塌为自在的词汇作为组织原则。它们中的某些词汇或许在其他的“星丛”中可以不用顾及这个行话而被应用;确切地说,“陈述”,在知识理论中用来表示主谓判断的意义,“本真的”,也作为形容词,(当然是谨慎地)用在要区分本质性与偶然性的地方,“非本真的”,表示某种断裂,即与其所表述的东西不相一致的表述;“电台播送的音乐相对于传统的、以现场演出的范畴构想的音乐来说,就被涂上仿佛(Alsob)的底色,涂上非本真的底色。”“非本真的”在此是批判性的,是对一种包含假象之物的规定了的否定。但这种行话却从任何一种如此透明的背景中将本真性或者其对立面抽取出来——肯定没有哪个公司在接受一个订单委托的时候会当面阐释一下“委托”(Auftrag)这个词。但是这类可能性仍然是狭隘和抽象的。谁若对这种可能性过度夸张,那么他就走向了赤裸裸的唯名论语言理论,认为词语就是可交换的游戏筹码,全无历史的印迹。然而历史却渗入任何词语之中,并从原初意义的复兴那里抽走每一个词语,而这种行话正是要追踪这种意义的。什么是行话、什么不是行话,这取决于词语是否以这种语调书写,在其中这个词语处于超出其本身含义的位置;取决于单个词语的意义充实是否以命题、判断和所思考的内容为代价。据此这种行话的特征还是非常形式性的:它关心的是,它想要的东西单凭其被报告的方式就会被广泛地追捧和接受,而全然不顾及这些话语的内容。它驾驭着语言中前概念的、模仿性的要素,以服务于它所期望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效果关联(Wirkungszusammenhange)。例如“陈述”就是要使人相信,言说者的生存同时沟通着事物,并将这种生存的尊严赋予事物;他让我们完整地看到,若离开言说者的这种溢出,言说就已然是非本真的,表达对事物的纯粹顾及就已然是一种原罪。这种形式性的东西有利于蛊惑人心的目的。精通这种行话的人,不需要去说他在思考什么,甚至他从未真正思考过什么:这种行话剥夺了他去思考点什么的可能并使思想贬值了。本真的事情据说是:整个人在言说,这才应该是核心的。在此出现的是,被这种行话自身风格化处理为“自行发生”(Sich ereignen)的东西。交往戛然而止,并为这样一种真理作宣传,这种真理由于不假思索的集体赞同而必定是可疑的。这种行话的气氛带着某种古罗马占卜官的严肃,借助于任何圣物都可以随意宣誓。
行话的词汇脱离上下文,也脱离概念性的内容,它们听起来仿佛是说出了一种比其所指更为高尚的东西,似乎应该用灵晕(Aura)这个术语来表示。本雅明在同一时刻引入这个术语,并非偶然,此时他借这个术语所想到的东西(按照他本人的理论)对经验而言乃是消亡了的。本真性的行话的关键词乃是灵晕衰落的产物,是没有神圣内涵的神圣性,是被冻结的流溢(Emanationen)。灵晕伴随着一种非约束性,这种非约束性让它在祛魅了的世界中变得可任意支配,或者用准军事性的现代德语来说,就是让它随时待命。对这种行话所呈现的物化的长期指责,也被物化了。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针对糟糕的艺术提出的对效应的定义,即没有原因的效果,是适用于这种行话的。在神圣的精神被耗尽的地方,人们就用机械的舌头说话。但是,暗示的和非现成的秘密是公开的。不掌握这个秘密的人,只需言说,说得好像他掌握着秘密,而其他人都不掌握似的。表现主义的陈词滥调,“每个人都是被选中的”——这是被纳粹党徒杀害的保尔·科菲尔德(Paul Kornfeld)的一部戏剧中的台词,按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y)的错误引用,很适合于一个被社会发展威胁和贬低的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满足。小资产阶级无论在现实层面上还是在精神层面上都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从这个事实出发它便导出它的恩赐,来自原初性的恩赐。尼采活得不够长久,没能面见这本真性的行话而恶心:这可是20世纪杰出的德国怨恨—现象(Ressentiment Phanomen)。尼采说的“这闻起来不好”,只有考虑到以下这种罕见的康宁生活的沐浴礼,才具有意义:
真正说来,礼拜日从礼拜六晚上(Sonnabend Abend)就已经开始了。当手工艺人清扫他的作坊,当家庭妇女将整个房子都收拾得一尘不染,甚至将房前的街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将一周积累下来的垃圾清理完毕,当最后给孩子们洗完澡,大人们彻彻底底地冲洗掉这一周的尘土,新衣服也已准备得整整齐齐——当所有这一切都以一种田园诗般的细致和从容办理停当,一种安息的深深祝福的氛围便聚拢到人们身边。
特别推荐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起推出的“阿多诺选集”系列丛书,精选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阿多诺的多部著作,囊括其《道德哲学的问题》《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最低限度的道德》《黑格尔三论》《认识论元批判》等论著,邀请国际知名学者霍耐特撰写选集总序,国内外知名学者马丁·杰、谢地坤、吴晓明、张一兵、王南湜等担任学术顾问,专门成立了一个由谢永康教授为主编的学术团队,负责翻译、甄选文本,计划推出一套高质量、高水准、规模宏大的阿多诺学术选集。
◆ 选集亮点
※邀请国内外一流学者担任顾问并作序推荐。
※由十余名学者组成的庞大学术团队专项负责翻译、甄选文本工作,保证了译本的质量。
※选集规模宏大,甄选了阿多诺20余本著作和遗著的翻译出版,可谓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阿多诺文集。
※本选集忠实于阿多诺的德文原文,以边码形式标出原文页码,方便读者进行中德对照。
※书后附有术语索引和人名索引,以中德双语列出词条,方便读者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