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的匿名人生


(十九世纪巴黎上流社会 CFP/供图)
《天鹅之舞》是我们理解《追忆似水年华》和普鲁斯特的一把钥匙。虽然这字典一样的两本书里,普鲁斯特仅仅出现在序言、第一章、还有全书的最后两章中,但它却充分向读者展示出了普鲁斯特成为普鲁斯特的那个舞台——促使一个伟大艺术家觉醒的世界。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普鲁斯特就是一个天才的伟大作家,这是普鲁斯特成名以来传记作家和研究者给后来人的最大误导。如果回到普鲁斯特自己的那个世界,就会发现普鲁斯特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至少在他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没人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普鲁斯特生于1871年,1922年逝世,一共活了51年。《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出版于1913年,那时候他已经42岁了,距离生命结束也只剩下九年。即便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普鲁斯特依然只在一小群艺术家和作家中间得到了承认。大众媒体和主流评论家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在争取评论界来关注自己的作品的同时,普鲁斯特不得不承认他比很多新人还要“不知名”!
跟一个42岁的文学新人相比,普鲁斯特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形象。那就是“山茶花时代”的普鲁斯特在巴黎上流社会赢得的名声。在哮喘病还没有动辄把他捆在床上几个月或几年的岁月里,普鲁斯特穿着精致的礼服,扣眼插着夸张的山茶花在巴黎上流社会里纵横驰骋。“全巴黎最会吹捧人的人”是山茶花时代的普鲁斯特赢得的响亮名号。普鲁斯特对社交的爱好、还有他对贵族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拜,为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友谊,比如本书中一个无所不在的人物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伯爵(《追忆似水年华》里夏吕斯男爵的原型)作为“全巴黎最需要人吹捧的人”,就和普鲁斯特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上流社会的人们因为普鲁斯特既能当面奉承,又会在巴黎的报纸上用“全体巴黎人”这个响亮的笔名匿名吹捧自己而欢喜他。但匿名撰写社交新闻这个爱好,带给普鲁斯特的却并不仅仅是成功。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普鲁斯特是一个会在报纸上匿名爆料的人。比如《天鹅之舞》中的一位女主角,尽管和普鲁斯特保持了多年的友谊,却还是对别人抱怨“普鲁斯特这个人”、躲在角落里“鬼鬼祟祟”、“不知在刺探些什么”!
而且普鲁斯特在“山茶花时代”所取得的社交成功,还进一步损害了他的文学事业。对当时的大部分评论家和文人来说,普鲁斯特就是一个世纪之交在上流社会吹吹拍拍、打听八卦、然后信谣传谣的人、一个在报纸上堆砌肉麻词汇的“文学长舌妇”。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纪德在收到《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的手稿的时态度如此冷漠。
所有这些已经被历史涤荡的事实叠加在一起就能看到另一个普鲁斯特。一个富裕的上层犹太市民的普鲁斯特、有钱、有品位、但病态的崇拜贵族的普鲁斯特、一个作为社交明星的普鲁斯特,甚至于一个想要成为社交明星而不得的普鲁斯特。
这样的一个普鲁斯特是怎么成为生命尽头那个伟大的艺术家普鲁斯特的?山茶花时代的普鲁斯特是怎么变成《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的?答案就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自我觉醒,这也正是普鲁斯特自己所概括的《追忆似水年华》的主题。而《天鹅之舞》则展示了普鲁斯特这个作家所觉醒的那个世界,那是普鲁斯特想要征服却没能成功的那个世界,而其中刚好有另一个普鲁斯特,而且是更成功的普鲁斯特,那就是夏尔-哈斯,《斯万家那边》里夏尔-斯万先生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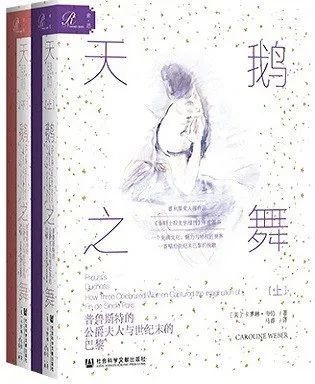
《天鹅之舞: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巴黎》
作者: [美]卡罗琳·韦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 马睿
出版年: 2021-4
从某种意义上说夏尔-哈斯就是普鲁斯特的梦想,如果“山茶花时代”的普鲁斯特能够得偿所望,无论他自己是否承认,他客观上都会变成另一个夏尔-哈斯。因为在每一个普鲁斯特倒下去的地方,夏尔-哈斯都捷足先登。或者说在每一个夏尔-哈斯高歌猛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领域,普鲁斯特都尝到了失败的痛苦。
夏尔-哈斯是第一个被接纳进入骑师俱乐部的犹太人,也是少有的能让整个上流社会至少当面对他笑脸相迎的犹太人,他和所有普鲁斯特不得其门而入的大贵族和贵夫人们都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本书的第二位女主角格雷弗耶伯爵夫人对夏尔-哈斯推崇备至,既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封闭沙龙,又请他陪自己参观一年一度的沙龙展。相比之下普鲁斯特尽管也多年出入伯爵府,却从没有机会参加“封闭沙龙”,只能参加公开的招待会。
为什么普鲁斯特没能成为另一个夏尔-哈斯?如果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看《天鹅之舞》,就会发现答案均匀地分布在全书的每一个部分里。在普鲁斯特所生活的时代,法国贵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权力。依照来源和政治立场法国贵族可以分为三类:拥护波旁王朝的“正统派”、本书的女主角塞维涅伯爵夫人就属于这一派;拥护奥尔良王朝的“奥尔良派”,格雷弗耶伯爵夫人属于这一派;还有拥护1870年才垮台的拿破仑三世的“波拿巴派”。
对正统派来说,从1830年开始就已经失去了权力,到世纪末他们已经丧失权力接近一个世纪了。奥尔良派稍好一筹,到1848年才被赶下台,但到1900年也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了。这半个世纪又是生活方式快速现代化,奢侈品、舒适性商品层出不穷的半个世纪,但所有这些也都价格不菲。普鲁斯特可以给自己的朋友买劳斯莱斯轿车和飞机,但他不得其门而入的很多贵族却没有这么阔绰。
鲁维洛瓦在他的《礼貌史》里说普鲁斯特关于上流社会的描写在各方面都非常准确,唯独在钱的问题上很不真实,他笔下的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花起钱来“都更像美国钢铁大王而不是法国贵族!”这个评论准确指出了普鲁斯特和他心目中的上流社会的一个重大分歧:普鲁斯特是阔绰的,不会算计金钱。但他眼中自带光环的贵族们,如果这样生活可能早就破产了。
例如书中的塞维涅伯爵夫人,虽然靠“亨利五世的宠姬”的名号,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但事实上无论是她还是她丈夫,其实根本不具备过奢华生活所需要的财产。塞维涅夫人是一个因为没有陪嫁几乎要进修道院的穷姑娘;伯爵是一个没有多少财产,只能绝大部分时间在“亨利五世”的“流亡宫廷”里躲清静的穷贵族。嫁给大富豪的格雷弗耶夫人,之所以选择那样一个“榆木脑袋”的丈夫,也是因为她的父母虽然出身王侯,却没有钱可以给她作陪嫁。而愿意娶她的那位伯爵,其实受封贵族才不到一个世纪,为了给自己的家族镀金才接受了这桩婚姻。
这种爵位和财产通过婚姻的结合,被当时的人们叫做“给家纹镀金”。本书开场的那场盛大舞会的女主人——萨冈王妃是位充满门第之见的贵妇人,但她的父亲其实是一个黑心的军队供应商,靠让法国士兵在普法战争里穿纸做的靴子才发了大财,为了让女儿戴上王妃冠,花了一大笔嫁妆帮助时尚明星的萨冈亲王重振了家业。
这样的婚事如果发生在依然保持着君主制的其他欧洲国家,会被看作是“贵庶通婚”,而“贵庶通婚”是一个贵族在传统观念里能够犯下的最大的几桩罪恶之一。但失去权力的法国贵族,为了钱、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已经顾不得门第、血统的“高贵”了。他们很清楚,无论自己的祖先是否可以追溯到圣路易的十字军东征,只要破了产等待他们的就是跟别人一样沦落街头。
那么当贵族已经失去了政治和财富上的优越地位,为了维持生计甚至抛弃了身上唯一值得珍视的“门第”和“血统”,让子孙后代身上流淌着“第三等级的血”,他们还能靠什么继续趾高气扬、继续盛气凌人呢?这是1830年以来的正统派、1848年以来的奥尔良派、1870年以来的波拿巴派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他们当中少数财富尚存的幸运者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但财产窘迫的塞维涅伯爵夫人就不行,甚至连格雷弗耶伯爵的妻子,伯爵夫人伊丽莎白也不行,因为她只是丈夫娶回家、用来证明家族高贵门第的活凭证。
这种处境尴尬的贵族女性却要维持一个优越的地位,保持自己的崇高形象,必须不断寻找理由说服自己,给自己寻找一个在财产、权力之外的新自我认同的基础。她们的选择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东西——艺术。艺术首先没有具体的功能,对万事追求实用的布尔乔亚来说艺术本身就违背“市民伦理”。对艺术的推崇就意味着对“实用主义”的反抗,能把人引向追求荣耀和优雅的贵族趣味。同时艺术还不需要大笔的钱,至少不像飞机和新式汽车那么费钱。欣赏艺术还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修养。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就让艺术天然的产生了一种“发思古之幽情”的效果。艺术把每一个热爱和欣赏它的人带向过去,那个贵族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黄金时代”。当国王客死异乡,艺术给最后的贵族提供了一个新的王国。
到世纪末,艺术成了贵族阶级的普遍共识,一个在财富、权力之外塑造自身优越地位的理由。不仅仅是本书中的两个贵族女性选择了艺术。其实在她们身边围绕着的一系列贵族男性也选择了艺术,比如格雷弗耶伯爵的“罗贝尔舅舅”,前文提到的孟德斯鸠伯爵,就以“须臾之物的国王”自居,把波德莱尔以来法国唯美主义运动变成了自己的运动。他的趣味、收藏、诗歌甚至是他的豪宅都是唯美主义趣味的化身,于斯曼因此把他写成了自己的小说《逆流》的主角。
贵族物质基础的虚无化导致贵族的艺术化,而贵族的艺术化反过来又让贵族展现出他们最吸引人的一面。一群举止优雅、被第三共和国隔绝在一切能够发财致富的“庸俗事务”之外只能全身心的投入到“艺术的幻想”当中的贵族,本身就成了一群艺术家。
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普鲁斯特如此热爱这些贵族,成了他们露骨的吹捧者。对普鲁斯特来说艺术是生命中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就找到了他和夏尔-哈斯最大的不同。对普鲁斯特来说,贵族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他们热爱艺术,而对夏尔-哈斯来说贵族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他们是贵族。夏尔-哈斯用自己的艺术修养服务贵族、讨好贵族。他总能巧妙的隐藏自己的观点,把自己的结论伪装成各位“老爷”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格雷弗耶夫人说她最喜欢跟夏尔-哈斯一起逛沙龙展,因为“他总能帮我理清思路!”的原因。
对夏尔-哈斯来说社交界的成功是第一位的,作为一个犹太平民,他需要上流社会的承认来帮助自己获得社会地位。但对普鲁斯特来说艺术是第一位的,如果上流社会不爱艺术,他们就毫无价值。甚至于如果这些贵族,在艺术趣味上、在鉴赏力上、在聪明才智方面不如自己,他们都会在普鲁斯特眼中黯然失色。
普鲁斯特不会隐藏他自己,虽然他是“巴黎最会吹捧人的人”,但如果孟德斯鸠伯爵在艺术上表现出愚蠢的一面,或者肤浅的一面,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加以讽刺。伯爵和普鲁斯特多次绝交,但也多次和好。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夏尔-哈斯身上,因为夏尔-哈斯不会暴露自己比贵族更有艺术品位这个事实。因为一旦暴露了这一点,那么无论是夏尔-哈斯还是普鲁斯特,客观上就成了贵族最厌恶的一类人。他们在半个多世纪里已经相继失去了权力、地位和财富,艺术品味是他们最后的堡垒、是赖以证明自身崇高地位的最后依据。但这时却突然跳出一个平民、一个犹太人,既不缺钱又比他们更有品位。这个人简直是一个宣告贵族阶级注定灰飞烟灭的可怕幽灵,而这样一个人居然还登堂入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谁能接受一个这样的朋友?除非是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比如孟德斯鸠伯爵这样的人。而绝大部分人只能要么试图赶走这个人、要么装作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夏尔-哈斯成了夏尔-哈斯,而普鲁斯特成了普鲁斯特的原因。因为虽然普鲁斯特也打入了上流社会,但他和这个群体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其实是貌合神离的关系。当哮喘病把普鲁斯特逐渐从社交生活里拉出来、绑在床上时,他有了社交界绝大部分人都不具备的充裕时间去反思他的所见所闻。依靠哮喘这个理由,普鲁斯特可以不去拜客、不去回拜、也不用按照礼仪的规定定期去投名片,去歌剧院亮相。他可以在一盏绿灯的照耀下慢慢反思、回味他的人生。这是他可以从艺术的角度从新审视、重新构建他的世界的原因。普鲁斯特不是社交界的“自己人”,所以他不是第二个夏尔-哈斯,也没有成为一个单纯的在日记本上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的龚古尔兄弟式的日记作家。
在这个漫长的彼此伤害的社交生活中,在更漫长的对兼具欢乐和痛苦的社交生活的反思当中,一个艺术家马塞尔逐渐从“贵人迷”普鲁斯特的灵魂当中觉醒。这是一个始于“艺术化的贵族”、终于“一个艺术家的自我觉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刚好就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主题。
普鲁斯特是世纪末的巴黎一个高高在上却处在社会边缘的小群体里孕育出来的一个最伟大的作家。《追忆似水年华》是作家整个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开出的一朵优雅的花。《天鹅之舞》看起来讲的是一群已经化作尘土的人、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不过是这朵伟大的“蔚蓝色花”旁边的点缀。但如果看不到这些点缀、这些泥土,就无法真正理解《追忆似水年华》,因为这朵花的色彩、芳香、普鲁斯特的整个灵魂,其实都来自《天鹅之舞》所展现的那个已经被人遗忘了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