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书评|卢一萍《大震》:一个死囚犯的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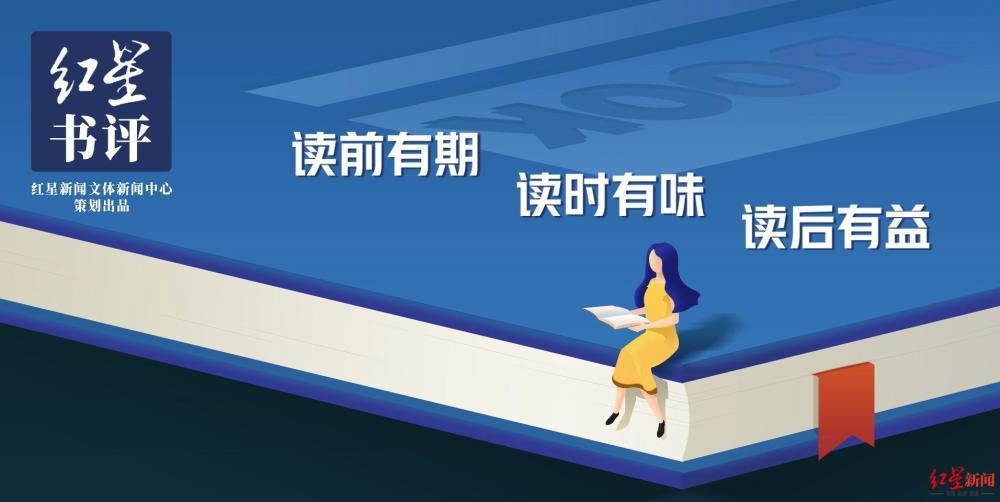
一部以“特殊性”为前提的现实主义佳作
——读卢一萍小说《大震》
◎陈培浩
汶川大地震,是新世纪中国标志性的重大灾难事件。文学叙事如何面对这场重大灾难,是一个仍在延续的提问。
卢一萍的《大震》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倾力打造的“百花中篇小说丛书”中的一部,写了一个死囚犯在汶川大地震中“逃往与回归”,从而完成“人性的救赎”的故事。作者将地震现场所产生的特殊情境推至极致,让人物在特殊而短暂的极致情境中释放人性复杂而丰富的纠葛和冲突,从而完成了小说的人性实验和伦理追问功能。
《大震》主要写了三个人物:原本要在5月12日被执行死刑的陈尔璧、管教民警谭乐为、即将刑满释放的惯偷杨耀东,三人都在这场突然降临的大震中幸存了下来。谭乐为为了防止陈尔璧逃跑,把他和杨耀东拷在了一起,而杨耀东也因此成了陈尔璧的人质,陈尔璧挟持他逃跑,谭乐为则要尽力追捕。三人的命运由此纠结在了一起。陈尔璧杀人前是有名的外科医生,这个逃跑的机会是他死里逃生的唯一途径,他一度甚至摆脱了杨耀东和谭乐为。但作为医生的他,面对灾难,面对那些受伤的人,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使他不断要去救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乃至灵魂得到了救赎。
《大震》是一部以“特殊性”为前提的作品,但这种“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戏剧性”。汶川大地震这样达到8.0级的地震已够罕见,它所催生的种种生离死别、舍生忘死、绝望与坚韧的故事本身已经具有足够催人泪下、扣人心弦的戏剧性。但这些故事内在所携带的精神叙事未必是作家所想提取的,因此,卢一萍在事件的特殊性(地震)之上,再加了一层环境的特殊性(监狱)。这两重特殊性的叠加就给小说带来了特别饱满的叙事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叙事的背后寄托着作者怎样的思考?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微妙的关系。一个真实的故事或事件,一旦用虚构的方式来讲述,反而难以让读者相信。这就是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卢一萍在《大震》创作谈中如是说。的确,《大震》为我们提供了谈论虚构与叙事的可能性的契机。小说天然享有虚构的权力,虚构使叙事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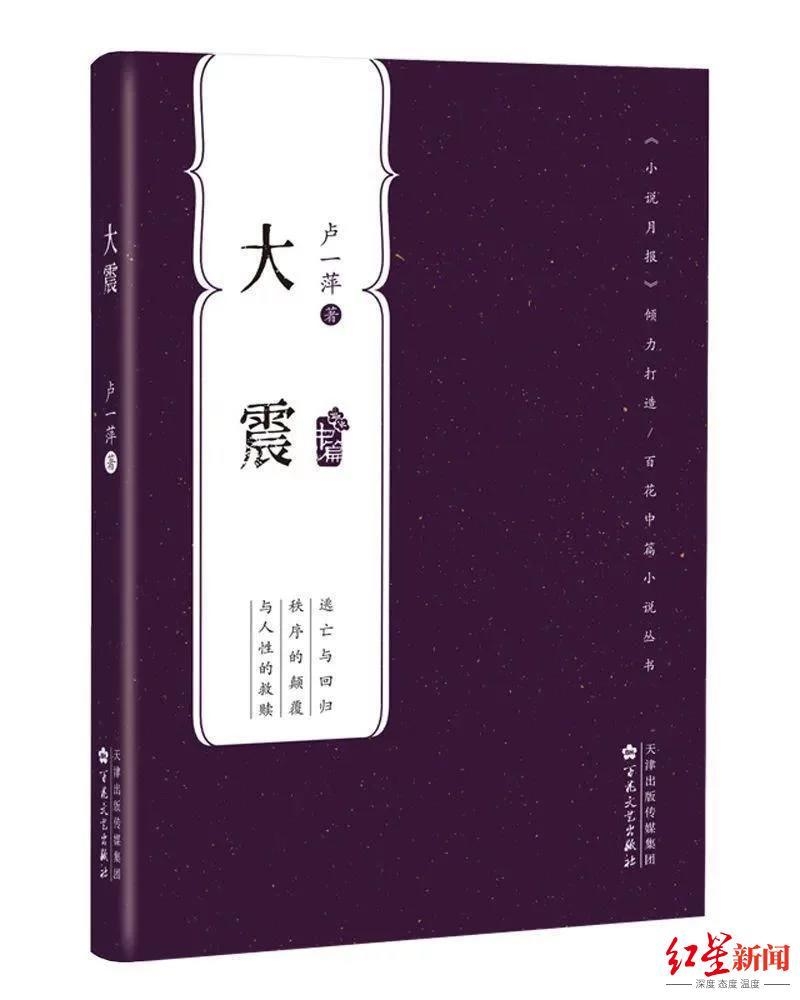
现实主义由于追求镜子式的观照效果,其想象力运作常常较为潜在而隐秘。《大震》启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想象力,一种要求既出人意表,又合乎情理的虚构。对于《大震》来说,其虚构最大的前提来自于情景的特殊化。汶川大地震已然创造了极大的特殊情景,小说进一步聚焦于特殊事件中的特殊空间——监狱,这种特殊性的设置无疑极大地保证了小说的戏剧性张力。
长期以来,人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受到“镜子说”的巨大影响,并因此产生了一些误解。镜子与现实是一种纯客观的成像关系,镜子式写作是对表象现实的完全再现,而现实主义与现实的关系则不然,且不说通过文学书写的中介转换之后纯客观是否可能,对表象现实的完全再现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追求。《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现实主义巨著其实到处充满不动声色的想象力。比如安娜和弗伦斯基在火车站的首次邂逅就将想象力隐于严丝合缝和伏笔千里之中。托尔斯泰绝不仅仅是铺陈情节,更在揭示心理、塑造人物、暗示命运。可见,现实主义的想象力表现于如何在镜子式再现效果中把尽可能多的艺术信息融合进去。
显然,《大震》也启用着这样一种克制的现实主义想象力,那些不动声色的细节和情境包含着卢一萍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观察和匠心独运的艺术运思及剪裁。小说第一节从谭乐为与女友金悦娴的一次相会写起。写其两情相悦时,叙事人跳出来发了这样一段议论:“要长久地爱一个人,迷恋对方身上的某种东西很重要——比如微笑中的明眸善睐,双唇相触的瞬间,眼波的一次闪烁。如果你所爱的人是一个星体,打动你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如同尘埃般微小的部分。”一般来说,在进入现代主义之后,叙事人的议论通常会被视为一种叙事的呱噪,但是《大震》中这段叙事人声音却绝非可有可无。它所携带的那种更内在更幽微的爱情观不仅说明作者本人对爱情内在景观的独到观察,更暗示着谭乐为是一个具有内在感受力的人,与他那张不无僵化的原则脸拉开距离、创作张力。一个内心如此柔软,又跟女友正处于热恋之中的狱警,在大震之后,他要克服内心怎样的痛苦和挣扎,才能继续坚守那张原则脸,继续在已成废墟的岗位上坚持下去?所谓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就是在不动声色的铺垫中,寄藏着丰富的阐释空间。
《大震》的叙事技艺娴熟,叙事的种种铺垫、冲突、起伏等常规的叙事手段卢一萍都不在话下,小说在梦境、潜意识的暗示等方面也有不俗表现。这些事实上都在考验着作家对于细节现实、情理现实的想象力。一般人只知道地震了,监狱坍塌了,原来稳固的秩序乱套了,但如何在此特殊情境中使不同身份者差异化的心理纤维毕现,并进一步将其提炼为叙事的冲突和动力,就考验着作家的情理想象力了。在这些方面,《大震》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对小说技艺稍有领悟者不需赘言。
不妨这样说,现代主义想象力更像一位刻意给人制造惊讶体验的魔术师,它超现实或荒诞的叙述语法使它的“想象性”如此一目了然。可是,现实主义并非没有想象力,现实主义的想象力运作更像是转魔方,作者看似寻常之手使散落在不同侧面的经验板块循一定轨迹运动,六面集齐之时,便是作品诗性显现的时刻。转魔方并不是变魔术,它并无魔幻性。生活的日常面目是一个被打乱的魔方,现实主义倾向于以并不违反现实情理逻辑的方式创造完整性现身的瞬间。显然,《大震》正是深刻洞察了现实主义想象力“魔方性”的作品。
(评论作者陈培浩,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现任职于福建师范大学)
编辑|段雪莹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