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丁浪与《北京晚报》

近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的创始人之一,著名记者、编辑丁浪同志逝世。
自1956年在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丁浪同志被分配到《北京日报》任副刊编辑。1958年3月,《北京晚报》创刊,丁浪同志调该报编辑“五色土”副刊,曾组织谢觉哉、徐特立、陈毅、朱德、王震、邓拓、廖沫沙、夏衍、袁鹰、袁文殊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家、艺术家写文章,为他们开辟专栏。
浪花归海,文字长存。《北京晚报》五色土特辑丁浪同志旧文,以表深切缅怀,回顾丁浪同志笔下风采。
电影“青春之歌”是这样改编的
——访杨沫同志

“青春之歌”改编电影的消息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关心。从座谈会上,从来信中,许多读者对整个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处理、情节的安排和如何弥补原小说的不足等等,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不少是相同的,也有不少是相反的,读者非常想知道作者到底是怎么改编这部小说?为此,我访问了小说作者和电影编剧杨沫同志。
杨沫同志首先谈到改编的主题思想。她说电影仍将以林道静的成长过程贯穿全剧。通过林道静在党的培养下走向革命的道路,阐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走向广阔光明的大道。同时小说中出现的那些老共产党员的形象,在电影中也企图使他们更加鲜明,以便展示党在白区艰苦的地下斗争和他们忘我的高贵品质。
杨沫同志说北影厂已确定将这部电影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从林道静跳海自杀开始,到林道静出狱入党结束。下部主要是想从多方面反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面貌,弥补小说中的不足之处。
接着我们谈到一些读者所关心的问题。杨沫同志说,经过编导多方面的考虑,剧本最后是这样确定的:
一、卢嘉川与江华合不合并的问题。决定还是不合并。主要觉得卢嘉川的死,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许多革命者倒下去了,许多新人又站起来,前仆后继,永不停息。在当时,事实上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和林道静从始至终保持联系。再说卢嘉川这样的烈士何止千万,他的牺牲对林道静的作用很大,影响也很深。他的死并不会减弱战斗的乐观的气氛,相反的会更深刻的震撼主人公(也是观众)的感情深处,促使她坚决为光辉的未来而战斗。
二、林道静的思想发展,应当更合理、更清楚、更使人信服。时代气氛不足之处也将在电影中设法给予弥补。
三、其他人物的合并问题——小说中人物太多了,放在电影上就不好办。为了突出林红这个人物,就把徐辉的一些事迹加在她身上。罗大方没有了。江华也不像小说那样,在卢嘉川死后才出场,而是用各种办法,使他的形象一开始就比较突出。
谈到这里我插了一句:“除了人物更集中之外,电影还有那些地方与小说不同了呢?”杨沫同志说:主要不同的地方有这几点:
一、定县的斗争改为农民的麦收斗争,江华来领导这个斗争,林道静也参加了。从这里她看到农村革命斗争的力量,也看到了自身的弱点并受到锻炼。
二、加强了林道静第二次被捕后和敌人的斗争过程。原小说写得比较简单,但电影要以这个斗争做全剧的高潮,因此从各个方面写了敌人的狠毒奸诈和林道静经受的多方面考验。同时在这场戏中还要把林红写成狱中斗争的领导者,把她的从容就义写得充分一些。
三、正面出现了卢嘉川被敌人集体枪毙的悲壮场面。
四、北大南下示威一场,正面写林道静看见了北平车站学生卧轨的场面。其他改动的地方还是不少的,但无法一一说清了。
杨沫同志说,这次改编她一共写了三遍稿(二稿在2月7日出版的“电影创作”上发表)。二稿写完后经过北京电影制片厂全体职工的讨论,北影和北京晚报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以及中国青年、文艺报展开对“青春之歌”的讨论后,她吸取了来自各方面的宝贵的意见,又再修改了一次。当改写三稿的时候,也碰到了一些不易解决的困难,譬如她对监狱里的斗争、麦收斗争、和南下卧轨等的生活积累不足,于是她亲自去拜访了几位当时领导或参加了这些斗争的老同志,得到这些同志的帮助,困难很快地就解决了。因此她说,这次改编本由于走了群众路线,得到了多方面同志的关心与帮助,也得到了几位导演同志和其他创作人员的协力合作。因之,小说中的优点保存下来了,缺点也得到了不少纠正。最后,她一再谈到,要感谢广大的读者对这次“青春之歌”的改编给与的关心和帮助。
(1960年3月15日《北京晚报》)
访徐老

正当东风浩荡、形势无限好的时候,党的生日又来临了。在这庄严的时刻,自然地使人想起了那些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的革命前辈。是他们以艰苦的斗争给我们带来了最美好的春天。为此,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在“七一”前夕,访问了革命老人徐特立同志。
徐老的住房非常简朴,就是书多。他老人家布衣布履,精神焕发,是那么平易近人。听说徐老今天整整看了一个下午的书,我不觉失口说:“徐老,您年纪这么大了,还是少看点儿吧!”徐老爽朗地笑了,那在艰难的革命岁月里所刻下的每一道皱纹,好像都挂满了笑意。他说:“我不老,现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天不学,等于二十年不学,你说行吗?”
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快乐地说着“我不老”,这三个字一下子深深地打进我的心里。徐老是不老,因为他老人家有一颗永远年青的心。我不禁想起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一九二七年,那正是革命低潮的时候,许多同志牺牲了,不少动摇分子逃跑了,甚至投降了。就在这个时候,徐老却挺身而出,坚定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千万革命前辈一起投入战斗。我说:“徐老,您入党的时候,环境多么艰难啊!”
“不!一个人要是只知道艰难,他是不会去做的,要看到艰难后面就是胜利。环境越艰难,就越会出聪明人,因为他要改变环境,不懂就学,就闯。”接着,徐老谈起井岗山前后的斗争情况。
那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没有大炮、也没有兵工厂,只有红缨枪和少数的步枪。所以,我们就学会了打游击战,敌进我退,以小胜大。用红缨枪缴敌人的步枪,用步枪缴敌人的机枪,又用机枪缴敌人的大炮,后来连飞机也被我们缴来了。敌人不仅给我们送来枪弹,还送来兵。他们围剿一次,我们就扩大一次。长征也是这样,前人走不通的路我们要走通,前人没到过的雪山草地,我们也要闯过去……。
徐老炯炯的目光中,仿佛使人看到当年他老人家在长征的路上精神抖擞、昂首前进的情景。他说起过去我们如何白手起家、如何建立根据地、扩大队伍、发展组织,许多人如何从一字不识变成了文化人,变成了将军。他说:就这样,我们发展、壮大,推翻了三座大山,把一个谁都看不起的民族变成谁都看得起的民族。为什么革命发展能够这么迅速呢?因为我们有了先进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因此,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能战无不胜、从胜利走向胜利。
于是,徐老谈起了革命者需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那是一把宝贵的钥匙,有了它就能使我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迅猛地闯开通往人类最幸福的世界的大门。
徐老就是一位好学不倦的老人。透过客厅的窗户,可以看见他的书房是满架满架的书籍,“毛泽东选集”放在最显目的地方。他老人家为了改造世界,博览群书,精通古今,四十三岁学法文,五十二岁学俄文,数十年如一日,从未中断学习。
停留片刻后他又说:“现在我们的国家那么强大,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了呢?还不是。”
“将来,我们一定是什么都会有的。”我插了一句。
“那不能坐着等啊!就得要好好地学、好好地干、好好地闯,让它快点有。”徐老的声音是那么坚定,眼光里充满了信心和对年青一代的热望。可敬的老人啊!他八十多年的经历是我们一部最宝贵的无字的教科书。他就是为了让人类幸福的生活快点到来,让丑恶的东西快点消灭而坚决地干,坚决地闯的。他老人家总是说:“今天觉得昨天做得不够。”他总是以不断革命的行动,谋取子孙万代的幸福,并以此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好好地学、好好地干、好好地闯,让有的更好,让没有的快点儿有,还有什么比它更使人感到幸福的呢?徐老的教诲,将永远鼓舞我们朝着共产主义前进。
(1960年7月1日《北京晚报》)
新春走访“老解决”

走进赵子岳同志家里,觉得他房间里的摆设跟主人一样朴素。记者听见许多年青的电影工作者都称他为赵老师,这一亲切的称呼里好像包含着什么,便问起他从哪时起搞艺术创作活动来的。他笑了笑,带着他平时那种特有的缓慢语气说:“搞艺术我从根儿就喜欢,搞算术就不行。”记者不禁被这一风趣的回答惹得笑了起来,难怪《锦上添花》的导演陈方千介绍,说赵老师是个喜剧人物。小时候,赵子岳同志学的是美术,抗战中间,他丢下画笔在太行山区演了八年抗战话剧。1950年,北影拍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他临时被抓去扮演一个农民。打那时起就和电影结上缘了。十几年来他演了不少正反面角色:《新儿女英雄传》中的黑老蔡、《暴风骤雨》中赶大车的老孙头、《青春之歌》的地主、《红旗谱》的狗腿子李德才。现在又在《停战以后》扮演伪县长班长儒、《锦上添花》中的站长老解决。
记者听说《停战以后》和《锦上添花》是同时拍的,便问他是怎样掌握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的。
他谦虚地说:“作为一个演员,同时演两个不同的人物应该可以掌握的,但我还没有掌握好。”又说:“演员要创造一个人物,自己要在生活中书本上长期的积累各类型的形象。这些形象你不用时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嗯,你要用时,就能慢慢地像炼丹似的把他炼出来了。”
“那你是怎样提炼出来的呢?”
“别急,现在就谈实际的。”他说起话来总是不慌不忙,慢悠悠的。“我举一个外表的例子来说吧,不知你注意了没有,班县长的头上有一撮假头发,梳得光溜溜的。”
“为什么呢?”
“我小的时候,见过一些班县长这样的人物,庸俗、无聊、很会吹拍、生怕落在别人后面、爱赶时髦,又时髦得不怎么样,洋不洋、土不土,酸不溜湫的。我想在班县长身上突出这些特征,这撮假头发梳得油光蹭亮,就是为了这个需要。”
谈到老解决,他把帽子脱下,幽默地说:“老解决也是个秃头!”在他演过的角色中,老解决和他的本色最相近。据导演介绍,赵子岳同志为人纯朴、勤恳,所以在设计人物的时候,导演早就把他和老解决扯在一块儿了。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演主角,也是第一次演喜剧角色,负担要重一些,但是,由于他熟悉老解决这样的人物,演起来就易于表现出人物的品质,而不必在外型上作任何的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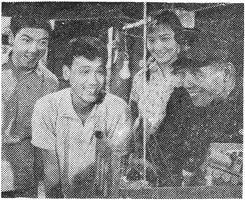
老解决(右)在看“小发明”的玩艺。
记者问他最喜欢老解决那几场戏时,他说:“要说最喜欢,要算‘三追’那场戏了。这场戏是在十三陵拍的。平常我的性子慢,别人笑我是‘慢半拍’,而老解决在这场戏里是很急的,慢可不行。所以,我得多下功夫,于是每天我带着干粮在河边练习,一个人追来追去,对着石头背台词,像发疯似的做戏……”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难怪“三追”那场戏他演得很干脆,拍得很顺当,导演相当满意。
我们谈得兴致正浓的时候,《锦上添花》中的“秦广播”(陈志坚饰)进来了,他来告诉“老站长”,北京站的铁路工人要与他们见面。他看见记者,还用“秦广播”那样的口吻说:“你来采访,那我告诉你个头条消息。”
“什么消息?”
“赵老师会变脸,这次是和谢添同志同场表演。”
(1963年2月1日《北京晚报》)
《野火春风斗古城》拍摄前后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已经拍摄完成,下月初就要在本市影院放映,这里想告诉观众一些有关影片的拍摄情况。
以谁为主角
据影片的导演严寄洲介绍,《野火春风斗古城》要拍电影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他们每天收到许多来信。这对导演和演员来说,又是高兴,又觉得是个压力。观众对影片抱的希望越大,压力就越大,怕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所以影片拍成后,还不断地进行修改。
把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搬上银幕,应该如何取舍呢?导演与小说作者李英儒反复地研究,最后才确定采用这条线贯串全剧——杨晓冬进城,策划关敬陶起义,目的是为了破坏敌人的抢粮计划,保护麦收。
小说以杨晓冬为主,影片则是以银环为主,着重写银环由脆弱到坚强的成长过程。围绕着银环成长,相应地改动了一些情节。譬如在小说里,杨晓冬被捕后,银环的情绪显得过于消极。在影片里作了不同的处理,着重写她积极地想办法营救杨晓冬。晓冬越狱的时候,在万分危急之中,她故意吸引敌人追赶自己,想以自己的牺牲掩护杨晓冬脱险。
虽然影片有紧张的情节,但导演极力避免那种过火的渲染,不想以情节取胜,而是试图努力去刻划人,竭力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冲突。由此便决定了影片的风格样式:是一部带点惊险倾向的正剧。
“问问演员自己”
金环、银环的戏很重,又是由一个演员来扮演的,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就转到王晓棠的表演上面。记者征求导演对演员表演的意见时,他没有正面回答,笑了笑说:“目前听到的意见不太一致,有人说金环演得好,有人说银环演得好。你可以去问问演员自己的意见。”我们便来到了另一个摄影棚里访问王晓棠。
王晓棠给人的印象热情、开朗。说话、动作都干脆利落。看来她演金环好像更接近一些,演银环这种腼腆、文静的少女,会有一些距离。按她的话说:“我几乎用了全部力量来塑造银环这个人物。”是啊,她在银环身上花费了很多的劳动。拍摄一开始,同志们就发现王晓棠变了,开会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再听到她尖着嗓门和别人争论了,而常常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听别人发言。待人接物也不一样了,说话不像以前放连珠炮似的,连走路的姿态也变得斯文起来。有时,你到她家坐坐,她一反过去的习惯,无论倒茶、送你出门,动作都是轻悄悄的,像个护士的样子。在整个拍摄期间,她都有意识地生活在角色之中。每天一早起来对着定音器定音,以便使金环、银环的声音有所不同。夜深了,她还在翻阅有关河北革命烈士的史料,准备第二天的戏。她找过一些护士、学生,帮助她一起共同来设想银环的形象。根据导演的要求,凡是重场戏事先都像话剧那样进行排练,广泛地听取意见后再进棚拍摄。

《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照
原来有个秘密
她所以这样认真,原来有个秘密,她说:几年来,虽然也演过一些角色,但不够满意,觉得表演的痕迹比较浓,人物挖掘得不够深。这次很想通过扮演金环、银环这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人物,使自己的表演水平能够提高一步。在拍摄期间,她曾到保定访问了一些烈属,她被烈士的英勇斗争的事迹深深地打动着,她觉得如果不真实、不朴素地去表演,也对不起烈士。
这时候,导演在旁边插了这么一段话:“有几场戏晓棠费劲比较大。如韩燕来责备银环那场戏就拍了三次。头两次她过于激动,哭得太厉害了,反而破坏了艺术效果。过了一个多月,我又决定把布景重新搭起来,再拍一次。隔了那么长时间再拍,对演员来说,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她还是克服了。”

拍摄银环得知杨母被捕的场景。左二是王晓棠扮演的银环,坐着的是导演严寄洲。
演员的希望
在谈到金环、银环的表演,王晓棠一再地说到自己不足之处。她认为剧本突出了金环火辣辣的性格,强调了她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一面,这是对的,自己也着重去表现这一点,但觉得金环对自己人那种谈笑风生、热情开朗的一面表现得太少了,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多提供一些戏,金环的形象可能会更加丰满一些。而银环呢,开头那几场戏,为了表现出她文静、温柔的一面,倒给这个框框套住了,其实,戏还可以放得开一些。她说将来影片公映时,她很想听听观众的意见。
1963-12-04《北京晚报》
小兵在成长
——影片《小兵张嘎》拍摄散记

一天下午,我走进北影的摄影棚,想看看拍摄小嘎子参军的场面。一进门,只见导演崔嵬正在打羽毛球。对手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满身嘎劲儿,面对着身材高大的“老兵”,毫不示弱,瞪大了眼睛,简直像个小老虎。不用别人介绍,一看孩子的这股猛劲,就能猜到他是安吉斯,银幕上的张嘎。
一股子嘎劲儿
在摄影棚里,同志们不时地赞扬安吉斯,有的说他不娇气,有的说他能演戏。
有一回,拍嘎子与胖墩摔跤的场面。第一次没有拍好,等想再拍时,崔嵬发现他身上的汗水干了。其实,要往演员身上洒几点水就成,拍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崔嵬不愿意孩子走捷径,他对安吉斯说:“你到外面跑一圈,等出汗再拍。”安吉斯二话没说,马上执行命令,一气跑了几百米,还怕汗不够,又坐在水银灯下烤晒。不一会,汗珠直往外冒,他高兴的大喊:“崔伯伯,汗来了。”崔嵬说:“我就喜欢这股子嘎劲儿,有毅力,不怕苦,这样的孩子才有出息。”解放以来,没有过一部影片像这部片子,小孩的戏是这么重的,几乎每个镜头都少不了他,如果演员没有点吃苦耐劳的劲头,还真不能完成任务哩。

崔嵬教嘎子(中)、胖墩(右)表演摔跤
慈爱而严格的妈妈
安吉斯的妈妈乌兰同志是老干部,自从安吉斯被选上当演员以后,她对儿子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拍摄期间,经常写信给安吉斯,叫他千万不能骄傲。有几次从内蒙来京,特地抽空找摄制组的同志问长问短,她最关心的不是儿子的胖瘦,而是儿子有哪些缺点,既慈爱又严格,对孩子有很深的影响。这次乌兰同志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来北影看样片。母亲看见儿子演得那么好,怎么能不高兴呢。但是,当同志们夸赞她的儿子时,她说:“我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了。他有多大的天才,有多大的能耐,我全都了解。现在他能演成这个样,看得出来,是导演下了很多功夫的。”
是呀,导演确实是花了不少功夫来培养这个电影战线上的小兵的。他常常给安吉斯讲部队小鬼的斗争故事,启发他去塑造小兵张嘎的形象。此外,又在生活上和安吉斯他们打成一片,打球、下棋,说说笑笑。说起下棋可真有点意思,崔嵬挺认真,要是安吉斯连唬带蒙地把他的“老将”吃掉了,他还真的“生气”哩。相处熟了,崔嵬慢慢摸到了安吉斯的脾气,他最大的特点是对事认真,不马虎。启发他演某一段戏,他非得想透了才去表演,从不照葫芦画瓢,也没有过不耐烦的情绪。安吉斯没有演过戏。开始时,几乎每个镜头都得崔嵬把着手教,有时为了拍一个镜头就得教三四个钟头之久。崔嵬说:“他肯学,又认真,所以进步很快,现在拍戏不怎么费劲了,在旁边一点就灵。”
新的一代很聪明,而且会变得更加能干,因为他们有上一辈人细心的指引和培养,也许是妈妈,也许是初次相识的导演……。

《小兵张嘎》海报
当个“纯粹”的解放军
说来也巧,银幕上的嘎子喜欢枪,安吉斯也真的很爱枪。不管跟前是谁,他看见枪就不免流露出真情:“这支枪要是给我多好,有它,上大兴安岭打猎也不怕了。”他喜欢打猎,有一次,哥哥带着他上山,迷了路,哥俩就在森林里烤野兔子过了一夜。
你以为他长大后想当猎人或者当演员?“不!”他用坚定的口吻回答:“我要当解放军。”
不知谁在旁边插了一句:“当解放军,也可以当个业余演员嘛!”
“不!我要当一个‘纯粹’的解放军。”他说的那么严肃,简直有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味道。
从他那稚气的话语里,不难发现,在这个幼小的心灵里,已经立下一个志愿——要像小兵张嘎那样去生活,去战斗。
影片里的小兵在成长,生活里的小兵也在成长着……
(1963年12月17日《北京晚报》)
唱支山歌给党听

前天晚上,才旦卓玛在民族宫剧场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她的歌声高亢圆亮,而又这样朴素动人,就像孩子对母亲诉说内心的话语一样。很多人异口同声问道:她怎么会唱得这么好的呢?为此,我到后台访问了这位二十六岁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
她正在化妆室卸装,脸上还挂着刚才演唱时的笑意。我把观众的反映告诉她:“你唱得真好,是从心里唱出来的,一听到你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马上让人想起你在旧社会受过的苦难。”
“开始唱这支歌的时候,一唱到这一句,我就要哭,怎么也唱不下去。”她的笑意消失了,那黑红黑红的脸上,仍然留下当年被寒风烈日吹打出的裂纹,这些裂纹里面藏着多少她童年时代的悲伤啊!
才旦家祖祖辈辈都是农奴,她很小就跟父母像牛马一样给农奴主干活。她父亲藏戏唱得很好,白天干活累了,晚上就爱哼哼几句,慢慢才旦也学会唱几句了,放羊的时候,一上山顶,就放开喉咙唱。在那黑暗的年月里,穷人那有唱歌的权利?农奴主一听见才旦唱歌,举起皮鞭就往她身上抽。才旦说:“西藏农奴主的皮鞭真厉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年纪大了,也被他们的鞭子打得血淋淋的,我看了直哆嗦,比抽在自己的身上还难受。我还亲眼看见一些农奴活活被打死。所以,每唱这一句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当年的情景。感情一下子就进去了。”才旦又说:“我还远远没有把西藏人民对党的心意表达出来。西藏人民对党的感情那是多少支歌也唱不完、唱不尽的。”接着,她提起她的母亲——一个受尽苦难的老农奴,党帮助她翻了身,结束了农奴的命运。当才旦第一次将工资寄给她的时候,她流着泪到处对人家说:“这是毛主席给我的,是共产党给我的。”她临死前还嘱咐才旦:今后我们子子孙孙再也不会当奴隶了,你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毛主席比父母还亲。才旦说:“母亲说得对啊!党比父母还要亲。是党,把我们从苦海中救出来,把我这个农奴的女儿送进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是党,培养我入了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懂得要用歌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党,给了我一切。”
停了一会,才旦深情地说:“我有好多话要对党说,我真想唱支山歌给党听。”说着说着,她情不自禁地轻声唱了起来,眼睛闪亮,流露出无限幸福的神采。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
现在,她一有演出的机会就唱这支歌,想多听听观众的意见,因为她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唱给毛主席听。
她说起了1957年的一件事。那时,她随西藏青年参观团来北京参观,毛主席接见了他们。那天,阳光灿烂,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毛主席走过来了,慈祥地跟大家握手。才旦一句话也说不出,就知道笑,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滚,怎么也擦不干,结果没有看清楚毛主席的脸。那天晚上,她激动得一夜没合眼。她说:“第二天一早,服务员热情地送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照片,这时我才看清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么健康,我简直快乐极了。”说到这里,她爽朗地笑了,笑得像孩子那么天真,那么开朗。
从那时起,她常常这么想,如果能够唱首歌给毛主席听,那该多好。可是几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很合适的歌曲,现在她觉得这支歌最能表达西藏人民的心意了。她说:“我一定要努力唱好它,争取将来能够唱给毛主席听。”
她还谈了很多,谈到她的老师和同学们对她的帮助,谈到事业、理想,她说:“我还年轻,还有许多事情不懂,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可是,我一想到我们有这么好的领袖,有这么好的党,有这么好的同志,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能干得好。”
(2007年12月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