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彦:我们都有责任为喜剧的沦陷买单


秦腔中的丑角(右)。(IC photo/图)
2020年疫情期间,作家陈彦困在家里,重新拾起自己搁置了8年多的小说《小丑》。也许是受到环境变动的激发,陈彦很快将这部小说写完。几十万字的书稿经历了从西安到北京的空间变换,2021年3月正式以《喜剧》为名付梓出版。
2019年10月,陈彦凭借长篇小说《主角》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成为继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后第四位获得该奖项的陕西籍作家。
陈彦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活跃于戏剧、歌曲、小说、影视剧等多个领域,从事创作三十多年来,他陆续发表了十余部大型戏剧剧本、影视剧本,还写成了四部长篇小说。陈彦并不是“专职作家”,从1980年代参加工作以来,他就一直过着朝九晚五的机关单位坐班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一直处在一种业余写作的状态,大部分作品都是利用休息的时间完成的。
出版社宣传这本书是陈彦“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但围绕着舞台工作了几十年的陈彦却觉得自己和舞台的故事远远没有终结。“下一本小说会暂别舞台,但不代表我不会继续书写舞台的故事,我始终认为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那里还有许多富矿。”
1980年代,受到当时文学热潮的影响,陈彦17岁就开始写作,22岁那年就连写四个剧本,受到省城领导的关注。1988年,陈彦被调入西安,成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业编剧,一做就是七年。几十年来,陈彦与戏剧的关系密不可分,2004年,陈彦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在他的努力和组织之下,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将建院70年来创作的优秀剧目及理论成果加以梳理、抢救。“我在文艺团体工作这几十年,学习、研究、实践这门艺术,汲取了很多十分宝贵的营养,甚至形成了一种民间视角的看待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式。”陈彦回忆。
与前作《装台》《主角》类似,《喜剧》的故事也围绕着陈彦熟悉的秦腔舞台艺术展开,讲述了西安城里两代丑角父子三人的人生传奇,集中展现了1990年代到新千年第一个十年之间的社会变迁,由此带出牵扯其中的各色人等。陈彦以自己对戏剧的理解代入人物命运,让自己笔下的戏曲演员呈现出比舞台上更复杂的性格与选择。
丑角是中国戏曲的一种程式化的角色行当,一般扮演插科打诨、比较滑稽的角色,虽然排在“生旦净末丑”的最后,却是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起到了调剂氛围、调动观众情绪的作用。
长期在文艺团体工作的经历让陈彦感受到传统剧目在当代的尴尬,他从上一代丑角贺少天对传统“丑角之道”的坚守写起,展现出戏曲演员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状态,从而揭示出大时代变迁带给个体的冲击和改变。
贺家长子贺加贝是全书的主角,他继承家学,练就了一身本事,在市场经济时代敢闯敢干,通过自己的能力创办了私人剧院,本可以大有作为,却在各种欲望中迷失了自我,将传统剧目改造得面目全非,最后妻离子散。弟弟贺火炬则在各种因缘际会中理解秦腔喜剧艺术,领悟了传统戏剧当代化的“正道”,人生也由此寻找到了真正的意义。
作为演员,贺加贝总想迎合那些索求“王炸”笑点的观众,丧失了自己的艺术底线。现实生活里,他又为了单相思放弃了作为人的尊严和家庭责任。陈彦认为,时代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往往交织在一起,他感兴趣的正是“在(悲剧和喜剧的)急速转换中,生活与生命的常态”。
写作中,陈彦加入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思考,他在后记里写道:“当一个时代拼命向喜剧演员索要‘包袱’‘笑点’时,很可能把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逼疯逼傻。可当他们真的‘疯掉’‘傻掉’时,唾弃最快、决裂最彻底的,仍会是捧他的观众。一个娱乐化或者叫泛娱乐化时代的造成,不是一群喜剧演员的责任,而是集体的精神失范和失控。我们都有责任为喜剧的沦陷买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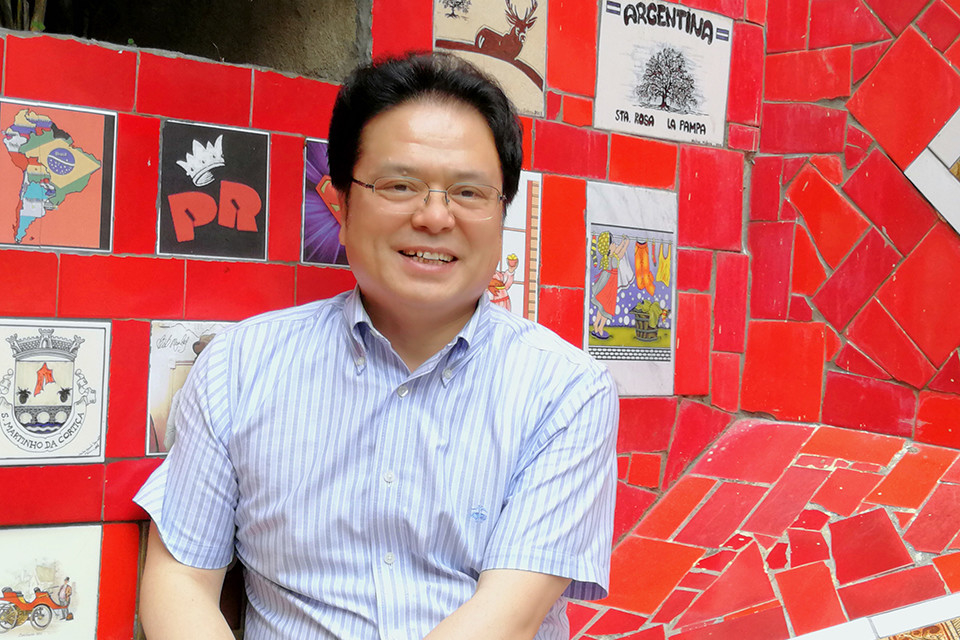
陈彦。(受访者供图/图)
“戏曲人有一种生命的尴尬”
南方周末:《喜剧》讲述的是戏曲行当里的“丑角”,他们往往负责制造喜剧气氛,很受观众喜爱,但是另一方面,大家还是更关注那些漂亮的主角,你写作这部小说的最初意图是什么?
陈彦:我之前的工作让我有机会和各种角儿打交道,也认识一些让我对丑角这个行当感兴趣的人。喜剧是观众特别喜欢的一种戏剧样式,我老觉得喜剧演员也是一群比较独特的人,他们往往智商情商都极高。但我想,他们的生活也不尽然是喜剧,这里面有很多倒错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心写一下“小丑”。但是写了一大半,我就有点找不到方向了,因为一味地写他们的荒诞与落差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就停笔了,直到2020年疫情暴发,我突然觉得这个小说的各种意义浮现了,所以我就又把它拿出来,一鼓作气写完了。
南方周末:你最后完成的这部《喜剧》与最初的构思差别大吗?我看你在访谈里曾提到这部小说对你来说难度要高于《装台》和《主角》,为什么这么说?
陈彦:差别挺大的,我的小说走向是不断地在发生变化的。有时候作家会为了一个精彩的结尾去写作,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就牵着作者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喜剧》的难度主要是故事的架构本身,还有叙事风格。《喜剧》写的是喜剧还有喜剧人物,但是如何把握自己的叙事风格呢,应该还是要带着喜剧色彩,甚至是荒诞色彩才比较对。所以我后来又加了一个叙事“人物”——一条柯基犬,它可以看到很多人类看不到的东西,用它的视角来推进故事。这个角色自身也充满了戏剧性和喜剧感。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是从一个秦腔剧团的变迁开始写的,讲了两代丑角的人生选择。当下的年轻人还有坚守传统戏曲的吗?
陈彦:目前对秦腔人才的培养主要是三种:院校培训、院团招生、师徒传承。第一种肯定是主导。的确,现在的生源里农村的孩子会多一些,他们会觉得学戏可以多一个就业机会。
我写的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很多剧团的人都在自谋出路,所以就多了不同的人生选择。走穴的、改行的都不少,但也有不少人坚守艺术。这都是个人选择吧,戏曲毕竟是相对小众了,不能要求所有的从业者都怀抱理想。我的确也发现戏曲人有一种生命的尴尬,他们付出非常大,但收成不一定多。他们一部分人和现代生活是有一些隔膜的,但他们仍在坚持。
“无论哪一种人生,都有深刻的意义”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通常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跨度,对个人与时代的书写,你感兴趣的是哪方面?
陈彦:我喜欢表现人物的命运,这里面当然有精彩的人物,也有不那么精彩的。我想通过人的命运去表现社会变迁。这里面既有随着社会发展一起在往上流动的精彩人生,也有一些一成不变的普通人,甚至还有一夜之间就被改写了命运的人,但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人生,都具有认识价值和深刻的意义。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表现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一些矛盾,包括城市和乡村,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彼此凝视、对立又融合的关系。后来的《装台》《主角》到目前的《喜剧》虽然比较聚焦在舞台生活的范畴,但我依然想通过这些演艺行当的小人物去折射时代。尤其是演员,他们接触的人其实非常杂,从权贵到知识分子再到最普通的老百姓,我想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
南方周末:比起你最初写作的1980年代,在当代严肃文学的影响力相对式微,你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吗?你的《装台》在拍成电视剧之后收获了更多的关注,你会担心影视化改编折损你的表达吗?
陈彦:我觉得当代文学没有1980年代的影响力很正常,但是不能说因为没有那时候那么热闹了,我们就放弃表达和文学的责任。我自己也做过电视剧的编剧,我觉得不同的媒介的确会有不同的艺术要求,也会做一定的改编,但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之后,内核不会发生质的改变。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里有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当所有人都裹挟在一个巨大的欲望浪潮里,很多人都迷失了。你觉得关注现实和批判现实是一个作家必须的使命吗?
陈彦:每一个作家的人生体验不同,创作的出发点也会不同,但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关注现实,作家还是要有自己的时代使命。小说里有批评或者反思性的思考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小说家应该追求的是人类至善至美的境界,自然就会对当下有所不满。当然也有很多历史小说,但我觉得历史小说也要有当代意识。我们之所以要写一个历史题材,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可以与当下对接的部分。甚至写科幻小说也是对当代人的关怀,表达了现在的人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想象。对我来说,小说还是要建立在对现实的感悟上。一个作家,他生活积累的丰富度,理解和把握生活的深广度,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他所创造的作品的眼界和格局,甚至包括艺术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说都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依然大有可为。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余雅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