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一个译者的隐匿与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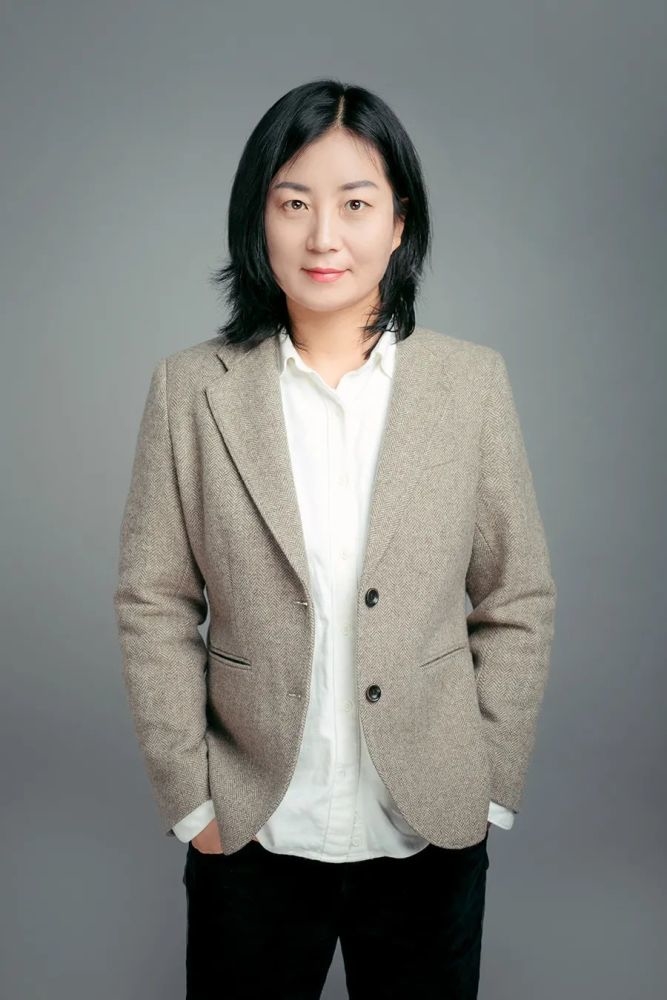
节制有时候是真切的激情,隐身有时候是更好的在场。
文/实习记者 卢琳绵 发自重庆
“真实的生活和小说不一样,过去的生活没有凸现出来,而是陷于黑暗”——陈英记得“那不勒斯四部曲”最后一句——2018年春天,尽管看过原文小说许多遍,但真的译到那了,失踪的莉拉依旧没有回来陪莱农度过晚年,“想哭,又觉得突如其来,难以置信”,一千六百多页,一项“劳苦的差役”,结束了。
“那不勒斯四部曲”是意大利隐身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作品,讲述了两个女孩间复杂缠绕的关系及命运。四年来,陈英一头扎进上世纪60年代的那不勒斯,在那些破败的城区生活、流连,与书中的人呼吸、争吵、恋爱,扑面而来都是意大利南部炎热的风。
这阵风,2011年,从那不勒斯刮起,恰合了全球女性主义崛起的潮流,引发多个国家的阅读热潮。小说不单指向女性友谊,作者费兰特将人物融进时代流变,各种历史事件穿插其中,“女性问题其实也是普世性问题,是女性小说,也是一部意大利历史小说。”英国文学杂志《Granta》形容:“如果你还没读过费兰特,就好比你在1856年还没读过《包法利夫人》。”
六年后,中文版译者陈英翻译的四部曲首部《我的天才女友》面世,好评如潮。“读它的时候,我没有秘密”,“这不是一本书,这是一把刀。它不仅划开了那不勒斯,也划开了我。”2018年冬,HBO上线第一部改编的系列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开播不久便入选《时代》周刊年度十大剧集,豆瓣评分9.3。

▲ 陈英获单向街文学奖最佳翻译
书火了,剧的第三部让许多观众翘首以盼——随着书的火爆,译者陈英也被卷入时代的潮汐中,就像书房里养的绿萝,延展开来,不知在哪个句子的缝隙就勾到了读者的心。“参与时代的过程我都觉得挺惊异的。因为你在做自己的事情的同时,参与了这个时代。”作为一本世界级畅销小说的译者,陈英兼着译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既遵循译者的传统,在翻译中保持隐身与节制,忠实原著;又从译作出发,现身社会实践,介入时代。
译者的现身
近十年,陈英常住在重庆歌乐山脚,过着依山而居的日子。以此地为起点,花上10分钟,能去到热闹的磁器口古镇;沿着山路爬半小时,能到静谧的歌乐山顶——陈英自称半“山居”,“向前走进入闹市,向后走隐入山林”。
后一种常见,节制、隐藏、透明、不在场,都是惯常与译者绑定的词。创作上,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出于对原作的尊重,译文需要规避“僭越”;生活上,翻译中那些近乎体力劳作的部分,以及规定的交稿日期,更要求了一种对日常的高度把控。陈英二者都把握得很好,从不拖稿,作息规律,译作更是广受好评。
采访当天,她带着我登歌乐山——“看一遍是坐飞机在上空游览,或者坐缆车穿过一个文本。翻译跟爬山一样,是步行,拾级而上。”眼前的陈英穿着宽松的运动服,爱笑,爱说“是吧”,这是长年当教师留下来的习惯,一句话停留在此处,音调往往变得最高和明亮,眼神也是坚定的。
登山出一场畅快的汗后,陈英仍保持着强悍的体力。她一年译三本书,工作量大,需要的体力也大,难怪同行朋友说,陈老师的能量,“深不可测!”
在书房里安静地翻译,是人们想象中译者的姿态——“现身,好像就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传统。”这自然与神秘的费兰特有关。“埃莱娜·费兰特”只是一个笔名,没有人能够确定作家真实的姓名、性别和身份。当作者隐身时,除了成为“最好的读者”,把握住作者的语言和传递语言中的文学性,译者能做的还有什么?
在陈英看来,翻译是一门手艺,一个人在书房里,默默地扎一个好看的小板凳。她不擅长做一些看似热闹的事,也不主动。但翻过的书如同一颗石子投进时代的湖泊,这下如影随形了,生活一下子蹦出意料之外的广阔,每一面都挠着她,将她往外拽。连回老家,亲戚问起她,都是“你们家那个翻书的姑娘”。

▲ 那不勒斯四部曲
陈英意识到,“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个转向,让她从语言转向实践,这是她刚从事翻译时完全没想到的。原著作者埃莱娜·费兰特从以往对一个女性的刻画,转到两个女性长达60年缠绕复杂的友谊史篇。陈英则从后现代小说转型到现实主义作品。早期翻译巴里科时,《愤怒的城堡》《一个人消失在世上》都极具实验性。“纯精神性的,诗意的、抽象的、梦境般的”,文字带着一种失重的眩晕,飘在云端。现实主义作品则“能让译者进一步地跟现实问题对接”。
女性参照
2013年,初读“那不勒斯四部曲”,陈英被两个女孩之间持久的较劲迷住。“书中这种特殊的吸引力持续了一辈子,充满思想、力量、激情,女性出于智慧而被绑定的描写非常吸引我。”亲密、控制、背叛、嫉妒与占有,能量巨大,“她们不总是相互帮助,她们也相互洗劫,相互盗取能量和智慧”,“莉拉和莱农的关系充满人世的烟火,是对生命的肯定”,“这不是可以简单用友谊概括的感情,女性可以成为另一个女性的缪斯。”
她觉得,“之前很多对女性关系的想象和刻画是很扁平单一的。费兰特挖得很深,只有这种复杂关系才是真正的关系。真正的朋友是非常罕见的,现实中大部分都是相互来往的人。我们自己因为精神特别孱弱,也承受不起很多这种坚定的关系。”
“那不勒斯四部曲”吸引了一大拨读者,陈英继而经常受邀参加讲座,主题多围绕译作、费兰特、意大利女性写作。实践参加得越多,她就愈发觉得,成长中的参照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不来自现实,也可以来自文学。“那不勒斯四部曲”能成为这样的参照,“长到一定的阶段,其实很需要一个成熟的女性作为你的参照,有很多事情可以交流”,包括真实的女性关系,“大众媒体、电视剧很多情节都在诋毁,在女性友谊没有打造成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塑料姐妹情’这样的表述,‘闺蜜’也混杂着很多暧昧的东西。女性之间的友谊还处于一种缺乏参照的阶段。”

读者们经常和她分享阅读《我的天才女友》《碎片》《鞋带》时的感受。她笑着自嘲,译的书都是婚姻劝退手册,“我觉得(我翻译的作品)可能会提高离婚率,降低结婚率。尽管可能比较遗憾,但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性。”来自女性处境的真实反馈,一点点扎着她,想要以学者的身份进入社会实践,“其实除了是译者之外,我还是个学者啊。”这不是自诩,听陈英的讲座,常有读者说,仿佛回到大学,上了一堂高质量的课,干货满满。
一间自己的房间
翻译“那不勒斯四部曲”时,陈英最得心应手的是第四部《失踪的孩子》。主角从少女时期的生涩与盲目、成年时期的漂泊与从野心中抽离,进入她口中的“真实的老年”,进入对人生有掌控的阶段。“这时尼诺在她心里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是一个愚蠢油腻的形象。莱农在反思,在清算自己的一辈子,也开始对抗年老的问题了。也可能跟我的年龄有关,我好奇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还有不追求男人后她的生活变成什么样,思索一种智性的生活”,“人若解下浮华的东西,爱情、声誉、事业,还剩下什么?”
陈英自认第四部契合目前的心境,语感也好找,年老的讲述者的声音平静沧桑。投射到自身,人到中年,克制的激情,真切强悍,最贴近生活本质,“清醒与节制,使一切井井有条、熠熠生辉”,能攫住内在的真相。
这份平静来之不易,她觉得要捍卫住——“达到一种自洽的状态,并且去捍卫。”身为女性,摆脱监控与受限于人,完全地去掌控自己的生活,于莱农,于她,都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 3月7日,陈英在北大博雅讲坛
1999年,陈英本科毕业。待过一段时间的旅行社,又去了大公司做技术翻译,三年后重归校园,考上了北外的研究生。家境不好,她成熟得早,常过着读书与打工的双重生活,自己负担学费和生活费。
在欧洲留学,为了省钱常住在昏暗的小宿舍。办居留时,挤在流民一样的人群里,警官态度粗暴,每办一次手续都元气大伤。后来又有人写公开信,指名道姓讽刺她,“一个女人,三十几岁了,还在海外读博士”。总结这段时间,陈英说,“到一定年纪才能摆脱。青春期又苦又长,那种受制于人的感觉特别差,没有自我空间,好多想做的事做不到。”
现在,在这间屋子里,陈英把《世说新语》、《聊斋志异》放在床头,每天读点古文,精神舒爽,保持中文语感;也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佛罗伦萨史》、阿里奥斯托《疯狂的罗兰》,一头扎进浩瀚的古典文学中。但她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碎片阅读太多,真正的沉浸太少。小时候上学,她是坐不住的那个,走神,阅读时思绪也是飘散的,报刊倒是看了不少,《小说月刊》《名作欣赏》《文汇报》《花城》。她印象深刻的是歌德的诗,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先锋文学作品,这些成为她文学的养分。每当翻译时,冷板凳一坐,进入状态,成为故事的讲述者,就又过起年少时写作的瘾来。
一个译者的激情与静和
“住在歌乐山这里,却是栖居在文字里头,有时候是冷清的北方,有时候是中世纪乱糟糟、情欲肆虐的修道院。”译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时,陈英感觉,整个夏天的体验都是恋爱,一段在那不勒斯有热度的恋情。
朋友莉迪亚就是那不勒斯人,身上有着小说般炽烈混乱的激情。走在街上,陈英能感觉到女性的气质是一种盛开的状态,一种很强的冲击力从年轻女孩子身上散开。莉迪亚解释这种强悍的生命力:那不勒斯在维苏威火山口上,这可是“欧洲最危险的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把一切都埋了,他们就有一种决绝的姿态。
2009年夏天,莉迪亚带她去那不勒斯。朋友的“Mutter”(德语的“母亲”,莉迪亚称)就是火山的女儿,伤心时大哭,愤怒时会跳,可以讲几个小时不重复的话,蹦出许多真理。Mutter开车彪悍,回莉迪亚家的路上,巷子窄,车子卡得只剩下一个左后视镜,挤一挤也过去了。

▲ 陈英讲座合影
陈英在翻译时往往想起莉迪亚与她的母亲,费兰特写出了一个城市的气息,“那不勒斯人和他们的城市紧紧贴合,有一种真正的激情在整个城市回荡”,“一个对情感刺激很强烈的城市,在那比较容易生气,比较容易恋爱,它的美很美,丑就很丑”,“我仿佛感受到了那不勒斯的风,感受到了主人公成长的破败街区,感受到那些灰尘、热度,还有大海。”
但笔落在纸上,落在翻译实践,尽是节制。面对激情带来的节奏感的更替,才更要保持平静。翻译第四部的时候,她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每天骑个破单车,寻到白云山下没蚊子的图书馆,平心静气地在馆里坐上一整天。“翻译是每天的固定节目,不是今天兴致来了,灵感来了,写个一万字然后休息三天,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作,很规律。它跟一个手工一样,它有工序,先把稿子写出来,然后不停地改,不了解的地方还得精修”,“节制也有一种激情在里面,对你做的事情怀有一种真切的激情。”
工作之余的时间大都静和。她自比是蜥蜴托生的,冷血动物。“工作完了,春分之后,最好的度日方式就是找个有太阳的地方天天躺着。”确实也这么干过,十年前博士毕业后,陈英得了半年的闲空,通日去运河公园和龙潭湖公园晒太阳,拿本书,防备溜圈的大爷来问她“为何老枯坐着”。年票也只需三块钱,她就整日坐在亭子里喝茶,心里特美。书不怎么看,就跟柳条一起感受暮春地下浮上来的燥热。
3月初,重庆精典书店,作为主讲嘉宾,陈英参加了《历史的暴力与女性主义写作》国际妇女节讲座。现场互动环节中,对话从“那不勒斯四部曲”进展到对现实中女性处境的积极追溯。背后的屏幕上是她刚刚对妇女节的祝福语——“更强悍,更开心!”以及那张广为人知的“We Can Do It!”海报。
当天,她在PPT上,黑底白字,列了丁玲的四条教诲,不仅在给现场的女性朋友,更是贯穿在她作为译者的日常生活中: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有节制地生活。第二,使自己愉快,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游惰只会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第三,用脑子,最好养成一种习惯,才不会后悔,才不会上当。第四,下吃苦的决心,生为现代有觉悟的女人,就要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