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堂·师说】北大教授严家炎:“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


严家炎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视频剪辑 徐语杨
古典文论《文心雕龙》这样阐述“文”:“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文学,充满形、声、情之美,需要从业者具有想象力和真诚的心。严家炎认为,“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在自选文集开篇,严家炎表明自己毕生奉行的信条时如是说。不管是研究《创业史》还是为金庸武侠辩护,都体现出严家炎对文学的痴心热爱。
1933年出生于上海的严家炎,从小喜欢文学,高二时在上海的《淞声报》上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还学着写过一两万字的武侠小说。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副博士研究生,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之路。入校不到两年,由于缺乏教师,领导找严家炎谈话,让他给北大的留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就这样,严家炎提前走上了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堪称奠基者的学者中,严家炎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1961年,年仅28岁的北大中文系教师严家炎,被抽调到周扬主持的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由此开始他一生的学术方向。1978年严家炎便开始与王瑶合作招收硕士生,再加上八十年代初出版论文集《知春集——中国现代文学散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严家炎被业界公认为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领军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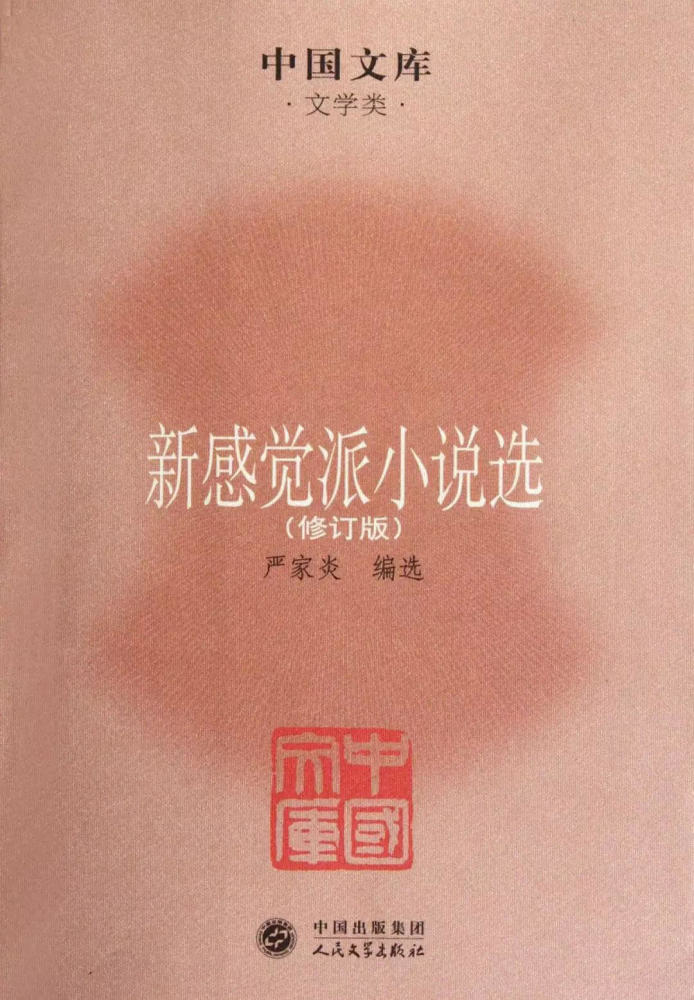
严家炎研究作品
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派”
1982和1983年,严家炎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专题课,听讲者包括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进修教师。每次开讲,近十台录音机同时启动,讲课内容传播甚广,部分观点被他人的文学史、小说史著作所吸纳。严家炎将他这次专题课的讲稿整理、补充、修订成书。这就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此书1989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2009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增订版;2014年10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再版。2008年获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百项精品成果奖”,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严家炎先生的代表作,认为其“最能体现严家炎作为文学史家的功力及见识”。
“新感觉派”小说是20世纪我国引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主要作家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等人。“新感觉派”主张以视觉、听觉,来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即以感性认识论作为出发点,主张追求新的感觉和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强调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和主观感受。莫言的一些小说就具有“新感觉派”特征,比如他的《透明的红萝卜》以构思的奇特、感觉化、体验化的叙事方法和空灵的意境震动了文坛。
这个小说流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属于异数,长期被排斥在主流区域之外,严家炎却是“心有戚戚焉”。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严家炎对“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派”进行了重新发掘,被认为填补了小说史研究的空白。尤其是“新感觉派”被埋没了几十年,一朝被严家炎发掘出来,引得中国最早的“新感觉派”作家代表施蛰存先生笑称自己乃“出土文物”。
严家炎对这个流派的成员、代表作品、创作风格等问题的系统阐述,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新感觉派”的文学地位为研究者默认,“新感觉派”研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严家炎看来,文学具有审美的根本特点,如果脱离了审美标准,很容易走上庸俗社会学的道路。他总是首先从艺术角度对作品加以考量:看看它能否真称得上语言的艺术,看看它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动自己。思想只能渗透于艺术之中,不能游离在艺术之外。脱离了艺术的思想,是干枯无生命的思想,根本打动不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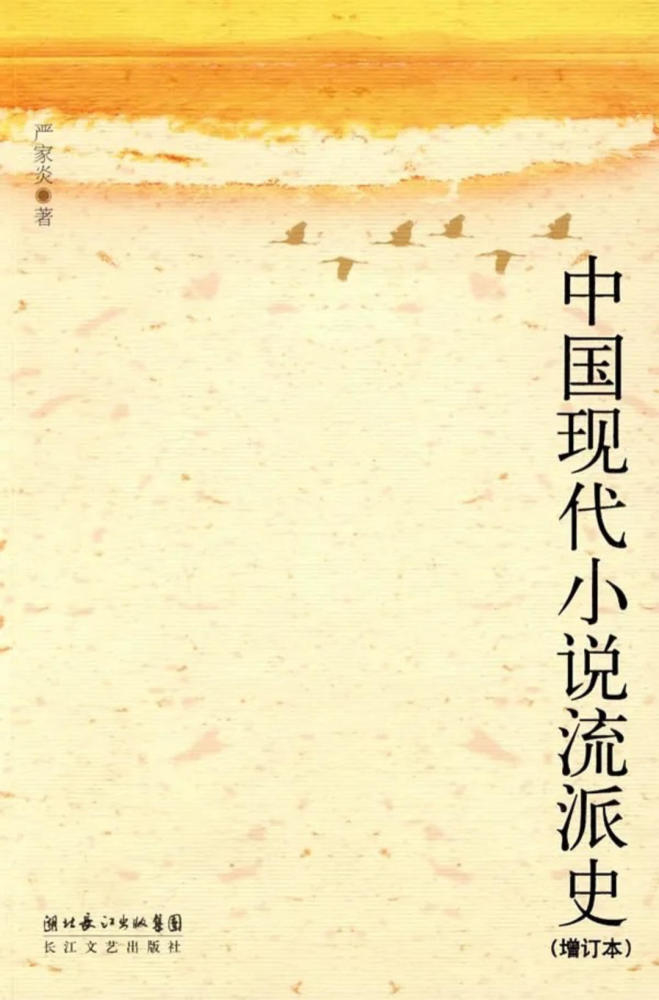
为《铸剑》而“战”
在严家炎的学术生涯中,与人笔战非常热闹,还有一次,起因是他将鲁迅的小说《铸剑》归为武侠小说。
《铸剑》是鲁迅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历史故事新编,既有“干将莫邪”的故事情节,又以古讽今。在严家炎看来,文中“黑色人”那种与专制暴君势不两立以及行侠不图报的原侠精神,几乎就是鲁迅精神气质的外化。于是,在严家炎看来,《铸剑》也是武侠小说。因为,一切叙写“仗武行侠”故事的小说,都可以称为武侠小说。
将鲁迅的小说归位武侠小说,有的人或许不能接受,认为这是贬低了鲁迅的作品。严家炎却有自己的坚持,认为题材本身很难分出高低贵贱,也限制不了作品思想或艺术上的实际成就,“将《铸剑》视为现代武侠小说,绝不会辱没鲁迅。《铸剑》写的是黑色人那种与专制暴君势不两立以及行侠不图报的原侠精神,它可以说,也是鲁迅自己精神气质的外化。这位黑色人的外貌长相简直就是鲁迅的自画像。而且他有一个姓名,叫做“宴之敖者”,“宴之敖者”就是鲁迅曾用过的笔名。由此可见《铸剑》和作者鲁迅间的那种密切关系。”
在不少论著中,严家炎都强调,应该放弃对“武侠”或者“通俗文学”等概念的偏见。从历史上说, 无论雅文学或者通俗文学, 都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中国的《水浒传》 、《红楼梦》, 当初也曾被封建士大夫看作是鄙俗的书, 只是到现代才上升为文学史上的杰出经典的。 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大仲马, 在十九世纪也都被认为是通俗小说作家。“了解了这种状况, 我们也就没有理由看不起通俗文学了。 同时, 通俗绝不等同于庸俗。 严肃文学中, 其实也有大量思想和艺术上比较平庸的作品。 我们应全面看, 各取所长, 互相促进, 因势利导, 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棍子打死, 为地造成一方独尊的局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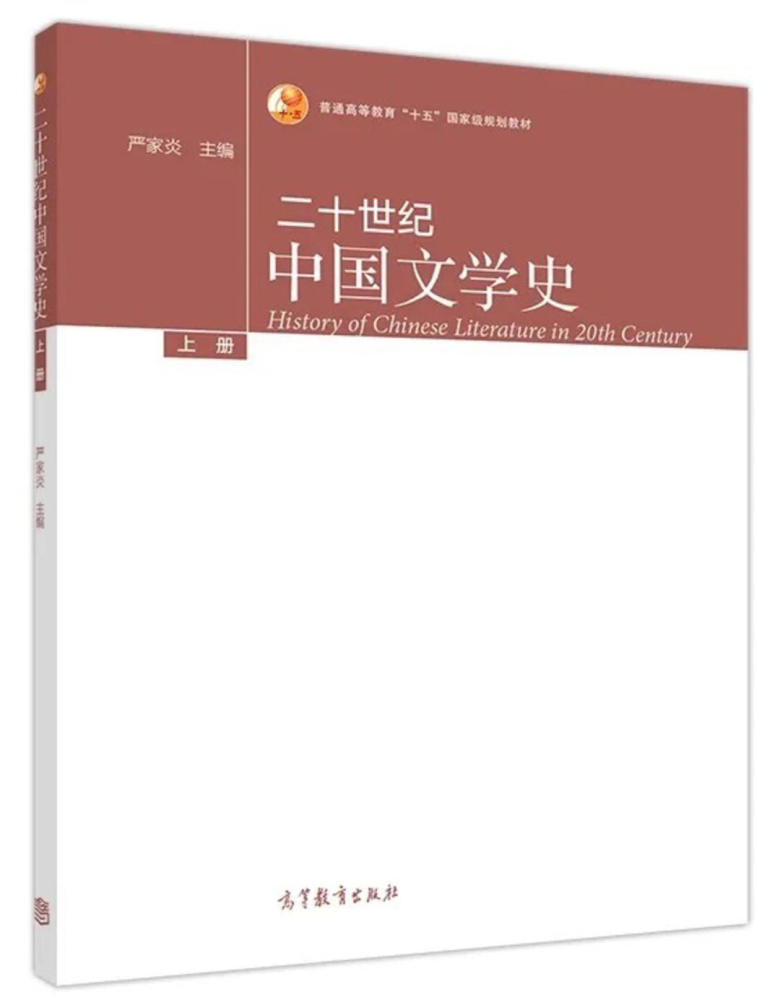
严家炎主编教材
用文学研究为作家“翻案”
发掘萧军身上的侠气
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严家炎不光澄清了不少文学问题,还切实通过实事求是的文学研究,为被遮蔽的作家“翻案”。
1979年,严家炎到萧军位于北京后海的家里访问,想借他的《文学报》阅读。萧生热情接待了他。连续四五个小时的阅读,使他大吃一惊,如梦初醒,意识到,曾经一些人对萧军的批判完全是个冤案。于是,在198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严家炎发表《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为萧军“翻案”,并且对这位“关东硬汉”感到由衷的钦佩。批判萧军的人后来也改正了自己的观点,认同了严家炎的看法。
“曾经有一些东北作家,带头批萧军,这个现象是不应该有的。甚至有人真的把萧军当成坏人了。我就千方百计找实证材料,把当时真实的状况翻开给大家看。大家就都清楚了,误解也就解除了。”说到此,严家炎语气里带着欣慰,“虽然萧军身上有弱点,但他身上也有侠义的精神。他的作品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严家炎曾撰写多篇关于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的论文。为了写好这些论文,他曾在一位明清史专家的指点下,先后阅读了百余万字的近二十种史籍,做了大量笔记,连崇祯逐年撤换的五十名内阁大学士的有关情况,都一一作了查阅考核。
为何对被遮蔽的作家,被误解的作家或者是价值被低估的作家格外关心?严家炎的回答很简单:“不能让他们受冤枉了。做研究,写论文,有时候可以很实在地帮助到人。”
在严家炎看来,做好文学批评,有几大要素。首先要了解自己批评的对象,阅读要批评的书。如果没有读过,老老实实免开尊口为好。这大概是每位严肃的批评者都能接受的道理。奇怪的是,就有人连对方的一本书都没有读过,就可以勇气十足地批评。其次,批评的力量取决于态度的实事求是和说理的严密透辟,并不取决于摆出唬人的声势。批评者的真正使命是要排出正确的方程式,而不是硬塞给读者一些哗众取宠的结论。第三,批评必须尊重原意,忠于原文,不能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另扎一个稻草人为靶子。”
严家炎特别提到,批评要针对事情本身,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这才是真正的君子风度,是文艺批评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真理越辩越明。对不同的意见,我的态度是开放的。别人要是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很愿意开诚布公地去争论。各自把自己的意见摊开来。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而是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绝大部分情况下,双方的观点最终是能达到一致的。如果争着争着,论战双方的现实关系受到影响,甚至出现记仇的现象。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据严家炎的夫人卢晓蓉女士透露,严先生把这辈子所有的积蓄都买成了书,家里哪都是书。严先生从年初到年尾从没有休息,时间都花在读书写书上,可谓名符其实的“书虫”。
2014年8月23日上午,“严家炎先生藏书及文物捐赠仪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严家炎先生将自己的近万册珍贵藏书和名人字画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的文物还有汪曾祺赠给他的画,马识途赠给他的书法等。
严教授提到自己的心愿:“希望这些书刊进入文学馆后,“能发挥它们的最大价值,能有机会让更多的人能看、能读、能借、能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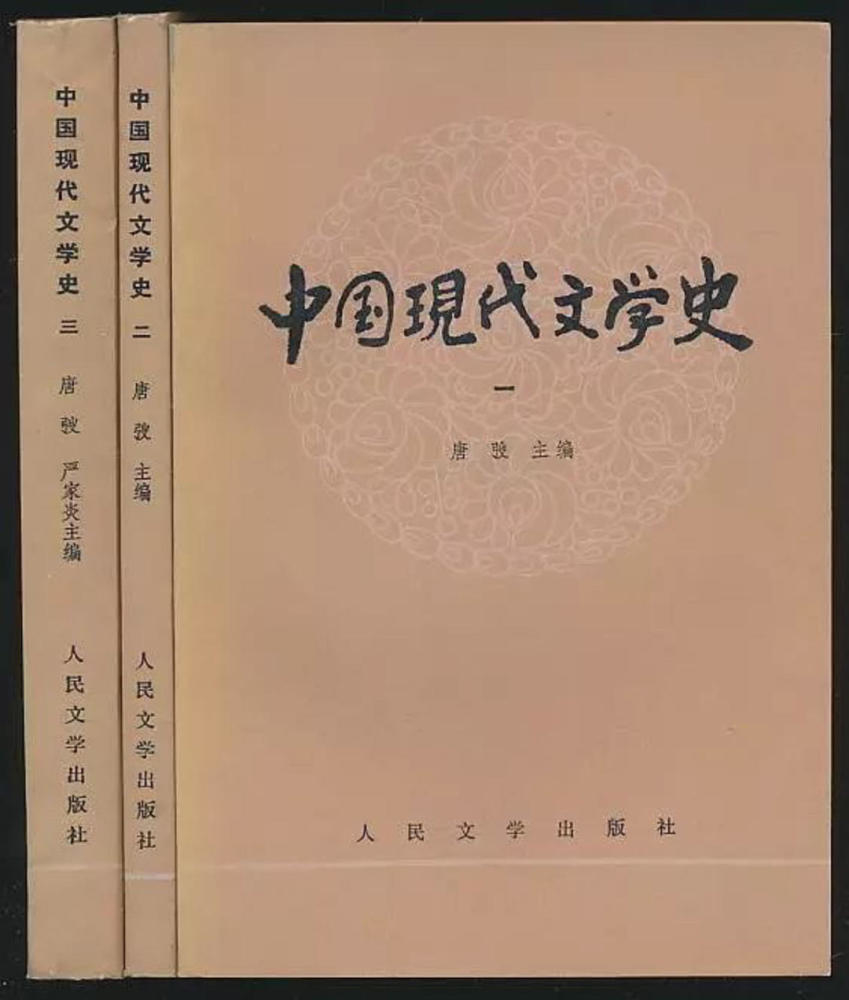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捐赠仪式上表示,自己作为北大中文系84届的学生,曾经在严先生的《现代文学史》课程上受到了许多教益。这批赠书对于文学史研究意义重大,因此,也代表现代文学馆、文学史研究者以及后辈青年学子对严先生表示敬意。
在被捐赠的书刊资料中,还包括一个很特别的“木质斜面写字台板”。它的来历跟金庸先生有关。
与金庸先生成为君子之交后,严家炎多次与金庸先生见面,地点或是在他家中,或是在嘉华国际中心25层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或是直接在太古广场的夏宫餐馆。“在我记忆中,嘉华国际中心25层办公室曾去过多次,连他陈列在那里的书籍也都相当熟悉。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金庸先生办公桌上有一付非常特别的木质斜面写字台板。我曾向他请教,这付写字台板有何用处?金庸先生相当得意地让我猜测。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写字台板装有可调节斜度的齿轮,能让写字者保持脊椎骨挺直,不致书写时弓腰曲背。我坐到椅子上用斜面台板试写了一下,果然身姿感到轻松、舒服多了。于是,金庸先生就提议要把这付写字台板送给我。我当然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金庸先生确实更需要。但金庸先生说,他已经七十多岁,使用率不高,而且他如果真还要用,让人再做一付也很容易。这样,我就变得没有理由不接收了,只能向他表示诚挚感谢并接受他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和情意。”
当年金庸先生白天写社论,晚上写小说,难免感觉疲累。于是他就设计这个架在书桌上的有斜坡的小书板,使得自己不至于在写作时不知不觉趴下来。由此可见,金庸先生之勤奋。
严教授夫人卢晓蓉透露,有一年北京下非常大的暴雨,恰好她和严教授在加拿大,水就灌进了地下室,给一个专门装书信的纸箱子和一部分书造成很大的损坏。被损害的书信和图书,包括金庸的来信和一套金庸送来的最新修订版的金庸武侠全集。“严教授对此非常惋惜、痛心。”
如今88岁时严家炎,虽然住在养老院,但他跟业内同道的文学研究者,比如钱理群等人都保持着联系,“他是我的学生,也是朋友,还有其他一些比我更年长的业内前辈。”
封面新闻记者来自成都,严家炎还提到自己与现居四川的马识途“很知心”。几年前马识途先生,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展出的时候,他还专门去参会和观看,“马老是不简单的人。我们在北京见过几次面,聊了很多文学上、书法上的看法,聊得很痛快。”
时光不可逆,人的年岁会自然增长。但热爱文学、热爱生命、热爱真理的心,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