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2分《波斯语课》:有人哭了很久,有人却嗑到了糖?


不久前热映的《波斯语课》,是一部符合大屠杀叙事的影片——二战、纳粹、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逃生——各要素皆备。
故事的主线也相当清晰明了:二战期间,犹太人吉尔斯(Gilles)为避免遭到屠杀,假扮波斯人。被关押在集中营期间,吉尔斯为保持犹太人身份不被发现,自称雷扎,并用同胞的姓名作为词根,创造了一门“波斯语”,去教授纳粹军官科赫。最终,吉尔斯成功在集中营内存活。

可以说,《波斯语课》承继了《夜与雾》《浩劫》《辛德勒的名单》等大屠杀电影的脉络。
电影学者李洋在《大屠杀的目光伦理》一文中,将大屠杀电影的框架总结为“还原-归罪-反思-对反思的反思”。这种框架不仅成为了类型电影的一种叙事结构,也成为了大屠杀电影的“道德安全阀”:即揭示历史凶手并指认其罪行,为观众反思大屠杀提供情感空间的同时,关照现实。

电影《夜与雾》
不过,与大部分同种类型片中主角之间的全然对立不同,电影里的二位主角,纳粹军官科赫与犹太人吉尔斯之间的交往构成了全片的主要情节,也让电影有了某种“反叙事结构”的色彩。

科赫从最开始不相信吉尔斯是波斯人,动辄殴打辱骂;到一次转折后,开始逐渐信任吉尔斯,确保吉尔斯待在自己身边,乃至身边的军官同僚都对科赫戏称“你的那位波斯人”。甚而,还有人举报吉尔斯是科赫的男宠。战争即将结束时,在科赫的介入下,吉尔斯成功离开了集中营。

自然,在对影片的评价中,除了与主要叙事框架相符合的反思性评价,还有很多人表示“磕到了”,并表示这个片子作为“腐女大礼包”,“懂得都懂”,是一个“霸道德国军官爱上犹太伪傻白甜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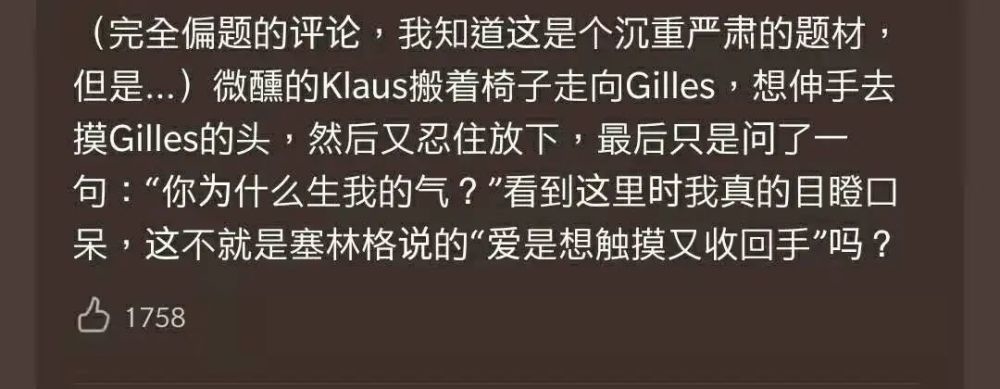

《波斯语课》的网友评论
不少网友都认为,科赫对教授自己波斯语的Gilles怀有某种微妙的情感,并对其取向进行分析,以证明这一论断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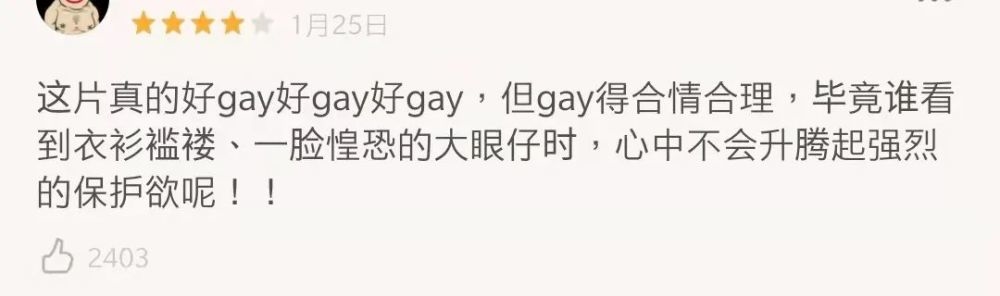
的确,学习波斯语的纳粹军官科赫是整部电影最复杂的角色。
在与吉尔斯用“波斯语”交流时,他提及自己出身贫寒,因为在街上看到纳粹潇洒富足的生活,心生憧憬而加入德军,负责后勤工作。而他最大的梦想,是学习波斯语,然后在战争结束后到德黑兰与自己的兄弟团聚,开一家德国餐厅。
暴怒与温情在科赫的身上共存。

正在学习“波斯语”的科赫。
在对待下属时不留情面的训斥,与听到吉尔斯用同一个单词翻译“面包”和“树”,心生怀疑,把对方摔在地上不断殴打的片段中,科赫身上也明显显露出富有法西斯特色的精神症候。

在这一凭借假波斯语搭建的二人空间中,科赫流露出温情的一面,而科赫与吉尔斯的权力关系也开始发生某种转换。吉尔斯成为老师,同时也是欺骗者;纳粹军官科赫则是学生,同时也是受骗的人。

这一处剧情触动了很多人,有人评论“这种超绝娇羞和憧憬的神情”,令人难得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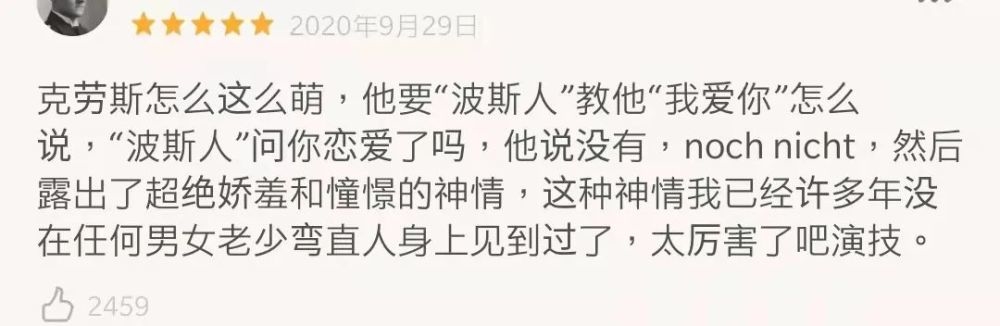
网友对此处剧情的评论。
影片最后,科赫准备登机前往德黑兰,大喊着只有他们二人能听懂的“波斯语”,被扣押起来的时候,这种权力反转达到了顶峰。

许多观众看到这一幕时,会产生难过甚至同情的情绪
当然,出现了许多评论对“嗑CP”评论进行驳斥,认为不应当消解电影题材的严肃性,或试图举例说明,片中二人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非感情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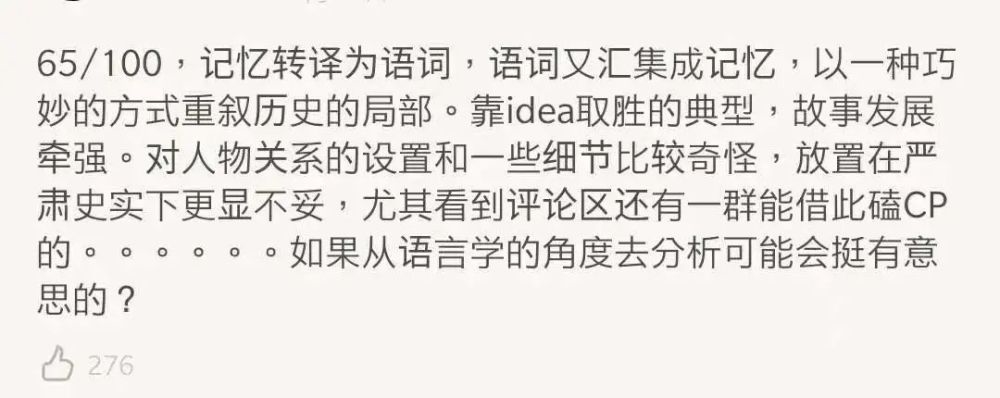
另一部分网友对“磕CP”评论的反驳。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如此沉重的题材下,“磕到糖”是令人羞于承认的?
原因在于,对大屠杀的反思和对战争的反思总是纠葛在一起,但二者其实并不能相互等同。
就战争而言,敌对双方“谁更正义”往往更有讨论的余地,就像我们在看许多电影的时候,往往会更喜欢那些有魅力的反派。


经典的反派角色,比如DC电影里的小丑。
当然,还有和珅。
但对于大屠杀而言,面对这种灭绝人伦的罪行,我们没有选择的立场和任何为其辩护的余地。承认甚至欣赏屠杀者群体中个别的人所出现的“人性”,无疑令人感到难堪。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一种罪恶。
此外,《波斯语课》超出传统叙事框架的部分还在于,除了表现犹太人假扮波斯人与纳粹苦斗之外,还用很大篇幅展现了集中营里德国人自己的工作生活。
与那种“牵着狂吠恶犬,穿着军服,踢着冰冷发亮的皮靴”,作为邪恶符号出现的纳粹军官不同,《波斯语课》展现了更多集中营里工作的党卫军的普通人一面。

对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军的真实影像记录。
影片开头,刚执行完屠杀的士兵把“波斯人”押送到科赫的办公室,得到了两个肉罐头作为奖赏。出了办公室,士兵把肉罐头塞到门口的另一个士兵怀里:“给你。你不要,我就把罐头给我在汉堡的家人了。”
暗恋同事的女军官听说对方喜欢卷发,会为了舞会认真把头发夹卷;情侣被举报者拆散,一方被派上前线,却不敢违抗命令时,眼中的不甘也展现得恰到好处。

关于上下级间的矛盾、对工作分配不公的抱怨、传人闲话、参加集体活动等等,整幅图景的描摹甚至有些像今天的办公室政治。

其实,展现军官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也是对纳粹群体更为冷峻的展现:他们将身边人当作人,而对犹太人进行非人化,从而将犹太人从道德的义务范围内驱逐出去,也就使德国大众无需对屠杀行为进行道德层面的考虑。
影片中,杀人者在执行屠杀时神志清楚,谈笑风生,也出于这一心理。

“用同胞的名字创造一门语言”本身取材自真实事件。这一事件本身已经具有太多可讨论的意涵:
故事开始,2840位集中营囚犯的名字从原有的意义中剥离,成为建造一门陌生语言的砖石;当战争结束,故事走到尾声,人名从凭空构建的语言上脱落,其意义又重新回归到民族与历史。
电影本身已经可以根据这个事例,去讲述一个符合大屠杀电影叙事框架的故事,完成一个符合道德评判与民族情感的简单闭环。

为什么还要描绘这么多“横生枝节”的情节,引起其他的讨论?
又应当如何看待大屠杀电影“还原-归罪-反思-对反思的反思”的基本叙事框架中,超出框架的部分呢?
历史叙事与历史事实
尽管电影中这些超出框架的部分,可能是基于电影工业需要更为丰满的情节与更多向度的议题去增强故事的可看性;但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假设《波斯语课》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个被完整记录下来的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个历史叙事,一种历史解释,也就是“一件由历史学家所讲述的,具有起因、经过、结果的事情”;那么,这部片中无数的细节则是呈现出来的史料。
什么是“历史叙事”呢?所谓叙事,就是将按照时间顺序组织材料,同时将内容放在一种单一又连贯的情节上,也就是“讲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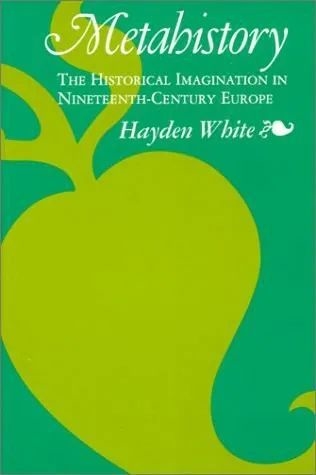
海登·怀特的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是关于历史叙事的重要论著。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无法重演,没办法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我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种种“痕迹”(文字记载、考古发现、历史遗迹等等)来接近过去。
将这些描述过去的“痕迹”按照起因、经过与结果进行排列,并赋予意义的过程,就是“叙事”的过程。


这些都是历史的“痕迹”,都可以被称为广义上的文本。
无论历史学者如何努力,其叙事都会渗透主观色彩,而不是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于历史研究成果不加修饰的展现。因为在历史学家选取材料建立故事,构成属于自己的历史解释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材料遭到弃用,或是被放置在了故事边缘的位置。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领域内,发生了“叙事的转向”。
“叙事的转向”关注文本背后的作者,也就是作者为了证明自身观点,多大程度上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或有意或无意地支配了事实。

回到《波斯语课》,让我们继续假设这是一个严肃的,被人记录下来的历史故事。无论是吉尔斯与科赫二人的关系,还是纳粹军官的日常生活,这些情节被有意无意地放在了叙事的大框架之外。
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真正发生了什么,也无法将其完全复原,种种讨论也只能从不同细节中趋近真相。
诚然,就这类史实而言,无论材料有多少,都无法掩盖极权主义的罪责。但如果把目光放宽到道德批判性不那么强烈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两则其他的例子
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曾对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尘暴为主题所作的两本不同论著进行比较,发现在论题、史料高度重合的情况下,两本书诞生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一则讲述了人类勇敢地战胜自然灾害的喜剧,一则讲述了由于资本发展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协调的悲剧。

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
清华大学的彭刚教授在《叙事的转向》一书中,还列举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文本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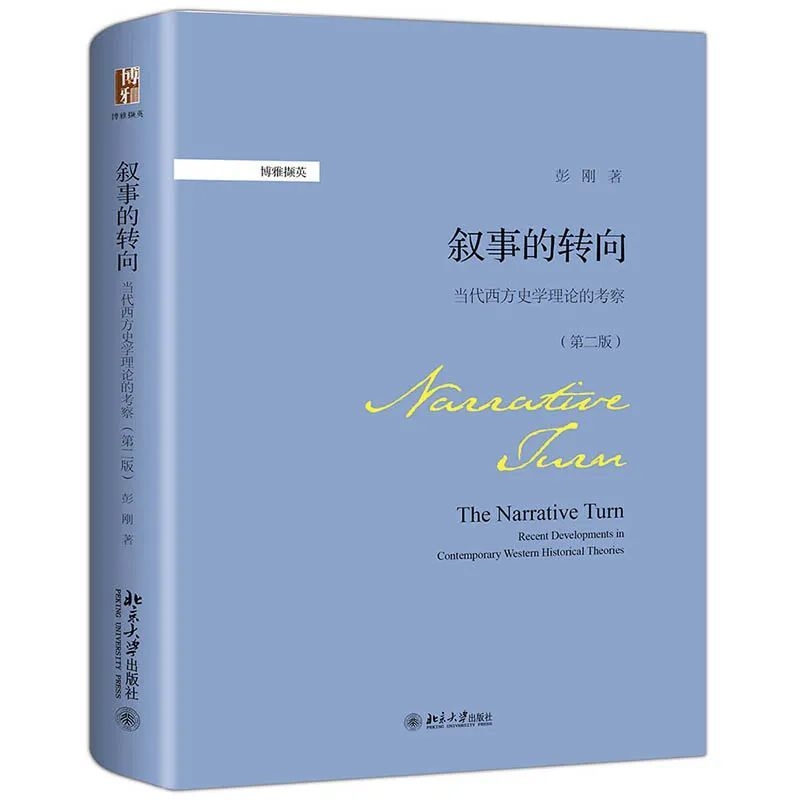
结合20世纪史学理论发展史,重新思考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历史学的客观性等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彭刚的《叙事的转向》
这个例子是一则讲述纳粹首席对英广播员乔伊斯的叙事。
乔伊斯生于纽约,在英国长期居住,曾伪称自己是英国公民。后来,他成为纳粹分子,入籍德国,战时担任对英广播员。因此,他在战后被以叛国罪处以死刑。

广播员威廉·乔伊斯。
彭刚教授将叙事中的每个陈述分开并编号,随后重组为两个故事。两个故事中各自缺少了一些原有的信息,因此,尽管每一个陈述都是真陈述,但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叙事,它们给读者的观感完全不同:一个叫人觉得乔伊斯罪有应得,一个则让人对他心生怜悯。
单个的陈述我们可以确定其为真或者假,因为它所指的是过去真实存在的某个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它与它所指的对象是否吻合,从而对其真假做出判断;但对于整个事件而言,我们却无法如此判断,因为故事本身带有的倾向性,使得材料相加产生了1+1>2的效果。

电影《罗生门》
这些例子不禁会让人想起《罗生门》。
原本只是一个关于武士妻子被强暴的事件,但在事后的审讯过程中,武士、强盗、妻子、樵夫各自展示了不同面向的事实,真假则需要依靠读者自行判断。
历史同样如此。
过去并非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如同未来一样丰富多彩。过去是开放的,也是流动的,我们都站在历史的罗生门前。
我们的确无法把适用于单个陈述的“真”“假”的判断,简单地运用于叙事整体之上,认定其中的某一个叙事比别的叙事更真或者更假。但叙事具有“提议”的特性,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过去某个方面的视角。要在结构之外,看到更多其他的枝节。
当一系列相关的陈述构成一个可理解、有意义的历史图景,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
的确,历史学家的工作开始于文本,最后的产品也止于文本。彭刚教授对此打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我们“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
但是无论如何,过去的真实性都不会因为历史学的文本性而变得不可理解,从而丧失其效用和意义。
借用彭刚教授的一段话:尽管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能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在出现无可辩驳的史料对于自身历史构图造成质疑或颠覆的情况时,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必须勇于放弃自己的预设,这是史学研究实践中最常见不过的情形。
今日活动
你去看了《波斯语课》了吗?你觉得“历史”与“历史记录”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吗?我们能从文本中触摸到真实的历史吗?
欢迎在留言区与大家一起分享讨论。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记忆与历史。小北将选出两位留言精彩的读者,送出我们今日的主题图书《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