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青年的文学初心
 2021-04-12
2021-04-12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04月12日 08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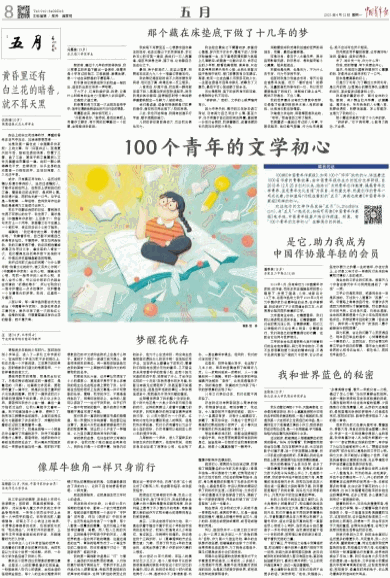
编者的话
100期《中国青年作家报》,如同100个“怦怦”跳动的心,讲述着近1000名作者的青春故事。由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这份文学新报,自2018年12月25日创刊以来,始终以“点燃青年创作激情,提高青年文学素养,坚定青年文化自信”为宗旨,与热爱文学、热爱创作的青年一同成长着。你知道吗?你现在看到的“五月”,其实也有着《中国青年作家报》同样的初心。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那里,有“100个青年的文学初心”在静候你的共振。


漫画:程璨
---------------
那个藏在床垫底下做了十几年的梦
冯嘉美(19岁) 武汉晴川学院学生
搬家前,睡过十几年的床即将拆除,我从那厚实的床垫下翻出一沓信纸。细看来是小学写过的拙文,文笔粗糙,剧情生硬,像一个站在田野里的干瘪稻草人。
我本想将它同其他积灰的物品一起扔出,但在扔出前它传来一声咳嗽。
不大不小,仅有我能听到。我想:它是什么时候有的生命力?压埋许久依旧活跃。
应是那次语文课。
我单薄的练习本第一次出现在老师手中,她字句清晰地朗读出我天马行空的想象。
周遭都在笑,其中却无贬义。
“你做得很好。”老师说,身后的黑板上写着作文要求:将不同的故事融成一个故事。全班唯独我做到。
我铅笔下写贾宝玉一心想要求回林黛玉的性命,他去五指山下求灵猴施恩,求它铁石心肠可落一滴泪,换他们一双人再重逢。但那灵猴是泼猴,骗了他,让他替自己压在山之下。
最后,猴子假活成人,在梁山落草,而贾宝玉还在九九八十一难里幻想黛玉归。
我依稀记得那段时间不少同学要我写后续,他们当了真,有得还举一反三起来。
人言来往,吵闹不绝,我在某一瞬间感觉笔下的人果真如写的那般活起来。后来我寻找其中原因,回想起那时每个单纯眼神里都映射出一处鲜为人知的神迹。
他们是读者,读者的相信即是对故事的信仰,信仰则滋养出笔下人物的灵魂。
从此,我也开始相信,我拥有创造平行宇宙、赋予魂魄的能力。
儿时的梦总爱做得很大,反正我无畏也无为。
我去挖出黄粱之下藏着的梦,梦里他心惶惶,梦外我不亦乐乎。看笔下的人好争好抢输掉一生,本不值得同情却要为其赔上几滴眼泪。或塑造一位鲜衣怒马,贪恋红尘的少年郎,眼看他高楼起,宴宾客,只在极其寻常的某天丢失心脏,此后永世都沉陷于微雨中哀叹,等门前青苔有马车碾过。再者,就来一位在古镇小河旁卖花的少女,一生都在委屈与自卑中挣扎,被辜负了又辜负,最后不甘心地闭眼了却余生。
无论是哪种,笔下的世界有无数可能,总是种种玄机不可问。
“砰砰砰。”那时,文学的心跳声强而有力。
因为中考失利,高中的三年除去语文考试,没有再为自己写过什么情。直至大学,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去挥霍。拿到第一份签约合同时,我穿着睡衣,迎着走廊的长风同妈妈讲那分激动。
泪眼朦胧间我觉得我创造的世界即将诞生,完善,最后金碧辉煌。
可是没有,像石子入水竟无声,黑夜吞鸦影竟无踪。我反思过,是我越来越小心翼翼,越来越迎合。
我曾经是无畏,也是无为。不为什么去书写,只为书写而书写。
但那时我是为利益去书写,每天沦陷在信息洪流里,成为“道听途说”的莽夫。流量即是我所争夺的一切,所以我甘愿牺牲笔下的他们,消耗他们身上生气,哪怕不符常态,不应人情。
我的世界最终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它像是才修建好就被洪水卷入海底的建筑,比烟消云散还惨痛些。
欢愉是文学给的,后者痛苦是我给的。
“咳咳。”那沓信纸又咳了起来。
我再重读一遍自己写过的人与事,不禁笑起来,他们稚气莽撞,行为也来得莫名,挑不出好可也厌不起来。
我问同在写手圈的前辈,这写得好吗?她说,普通俗,但我记得住。
末了,她补充一句,你为什么写?
我说,那时想着,写下来便会开心。
猛然,先前因为国度坍塌而灰心重重的我,好像浮出水面深深吸了一口气。
那本是最真挚的初心。
仅是为了书写,为了靠近文学而书写。是三月的雨,让落肩头的樱花挣扎出最后的绽放,至此留在过路者的心中。
我将信纸重新收好,面对空白的文档。眼前,有个舞台拉开序幕,欲望蔓延,渴求生长,形形色色的人七嘴八舌,我要他溃败,我要她涅槃,怎么样都好,全是为了我的初心。
那个藏在床垫底下做了十几年的梦。
“砰砰砰。”它不再咳嗽,心脏有力跳动,不会停。
---------------
黄昏里还有白兰花的暗香,就不算天黑
沈诗琦(20岁)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学生
阳台上的白兰花绽得热烈,厚重的香味在空气中流动,如涟漪层层荡漾……
这是我第一篇发在《中国青年作家报》上的文章,叫《日落白兰》。那是夏天的午后,接到发表的消息。我看了又看,品了又品,甚至于把文章重新从文件夹里翻出来重读一遍。当时一颗心跳得躁动不安,脸颊滚烫,似乎全身的血液都像一口刚挖的井,正汩汩沸腾,久久无法平息。
或许,只有真正写作的人,经历过投稿以后漫长等待的人,经历过退稿的人,才能体会到在网上、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文章、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是何种心情。我觉得兴奋,同时也长舒一口气。似乎这是一种勋章,一种证明,告诉我写作这条路还是值得为之继续付出努力。
我忍不住翻出当时的日记,看到自己充满不可思议的句子:我发表了,竟然是在《中国青年作家报》上发表了?!我在句末打上一个问号,紧接着又忍不住画上一个感叹号,将这页日记小心折了起来。
编辑说:“我记得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呢。”我捧着手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笑得有多灿烂。不管同学、朋友如何告诉我,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我依旧期待着能被真正也写过文字,拿过笔的人肯定一次。他们看得见白纸黑字底下流淌的汗水,听得见深夜里键盘敲击的呢喃。
我听过无数次类似的问题:“为什么要写呢?快餐文化的时代,谁又来关心你呢?”《中国青年作家报》会关心吧,编辑会关心吧,和我一起写作的人会关心吧,总有人会关心吧。所以这份报纸仍然诞生在所谓的“纸媒的寒冬”,所以它和我们一起守护着这一点点的情怀,守护着每一个发着微光的梦想。我说,这里有一片星河。
从那以后,每一篇作品我都会优先发送给《中国青年作家报》,渐渐也有很多文章刊发。虽然没有了第一次的脸红心跳,但是我知道,只要黄昏里还有白兰花的暗香,就不算天黑。
---------------
是它,助力我成为中国作协最年轻的会员
潘幸泉(18岁) 石家庄二中高三(5)班
2019年1月,我有幸成为《中国青年作家报》的作者,两年多来在编辑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发表了随笔、小说、诗歌共计1.6万字,这些作品助力我于2020年8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在作者群里,我还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文友,大家常常谈起共同热爱着的文学。
文学是有生命的。它需要营养,我们就以阅读和生活来丰盈;它需要睡眠,我们会时常沉淀心灵;它需要穿戴,我们又以惊艳的行文让它赏心悦目;它需要出行,我们将自己的智慧塞满它的行囊,还教会它如何与世界相处。
文学的生命也在潜移默化地引领着我们的生命走向精彩。因为写作中的你,不得不去思考事物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不得不去探究更加广阔的大千世界,它必然会坚定你要为之执着一生的信仰。你在它身上,必然像父母对你一样寄托对未来的希冀和对精彩人生的追求。
有生命的文学让我们孤独。前些天几个作者在聊天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孤独”一词。
文学必然是孤独的,或者说生命一定是孤独的,不过我个人更喜欢“孤勇”一词。尽管路上常常独自行走,尽管许多灵魂因为同病相怜才惺惺相惜,我也要走出恢宏的气势。仗剑走天涯,风雨出洞庭,生命的孤勇即便是十几岁少年也同样有资格评述。我想到贾平凹的散文集《自在独行》,其中有一句话叫作“孤独的人最不能接受怜悯和同情”。
因为孤勇,会让我们静下心来获得自己,明白自己毕生的追求,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善良的人。正因如此,我们会更加热爱文学给予自己的慰藉,竭尽全力地把对世界的认知传达给他人,感动他人,同时也丰盈自己。
---------------
梦醒花犹存
王洁(31岁,文学博士) 宁波财经学院创意写作教师
想起很多年前的少年时代。那时我刚刚小学毕业,进入了一家私立中学读初一。在当时那个学生为数不多的班级上,我依然是一个不爱说话、又非常内向的男生。那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姜老师,一个慈祥善良的老太太。
姜老师教我的课程,那是完全忘记了。只是依稀记得她教过的一篇课文,是鲁迅的《风筝》。这篇课文讲完后,姜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就是谈谈自己童年时代与玩具的趣事。我写了一篇讲述我们小时候玩玻璃弹子的故事。作文交上去之后,姜老师叫我去办公室一趟,拿出一叠方格纸交给我,让我认真把作文誊写一遍。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便照办了,后来她又把稿件返还回来,上面已经用红笔勾勾画画做了许多修改了,并嘱咐我照着修改过的文章再誊写一遍。
我也照办了。我是全班唯一一个把自己作业誊写了两遍的孩子,我并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意思。姜老师说,她把我的作文寄到当地的报社去了,我兴高采烈地回家把这一殊荣给我爸妈说一遍。那时我不敢想象自己的作文被印在报纸上会是什么样子。直到不久后的一堂语文自习课上,姜老师走到我的身边,将一卷报纸轻轻地放在我的面前——上面赫然印着我作文的标题和我的名字。
我感到无比兴奋,这件事让我满足了小小的虚荣心,甚至连平常并不怎么在意我的班主任也在班会课上赞扬了我,似乎能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件不可想象的壮举。看啊,我写的作文,不再是老师批改了,而是印在报纸上,全市的人都可以读到了——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打开了一扇不可预知的窗户,窗外的奇妙风景模糊不清但充满了希望。
那份报纸一直被我珍藏在书桌的抽屉里,用一张塑料文件袋装着,现在都已经泛黄了。直到今天我还是感谢姜老师为我做的那些事情,她让我从小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真正拥有写作的天赋。
有时候我在想,也许当时作文写得好的孩子,在我们那个班级里还会有其他人。而我也只是一个成绩平庸、性格内敛的孩子,她为什么会选中我,而没有去选择那些成绩拔尖儿的孩子呢?在她批改完作业,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的我们,看着我们刚刚走出美妙无忧的童年、又不曾经历未来艰苦中学的那些小脸,在那个阳光充盈的悠远午后,她想到了什么,才会作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我都没有再见过姜老师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全名。但是当年她做的事让一种东西延续至今,那就是关于写作天赋的错觉。
这种错觉贯穿了我的整个中学阶段,那个时代也正是一大批少年作家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的氛围让人做着不自量力的作家梦。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曾在高考结束后约定,以10年为期成为一个作家。这样的约定也许会遭到现在人的哂笑,但是我所庆幸的是,我们仍然有着可以为此付出心血的目标,仍然有着可以铭刻在心底10年的美好东西。
几周前的一个深夜,很久不曾联系的好朋友突然找我聊天。他告诉我说,他现在自主创业做了自媒体公司,也出版了书,一直在靠写字谋生。他问我,我们的约定兑现了吗?
这些年,我拼命埋头写作,也出版了几本小说。早年的退稿信积了邮箱好几页。从一家期刊到另一家期刊,从一个编辑到另一个编辑。有时一些新任职的年轻编辑开始喊我“老师”,让我觉得惶恐不安。我时常在想,我真的成为作家了吗?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吗?
10年之约早已过去,我们也都不再年轻了。
好在我还没有衰老到那么荒凉的地步。我相信梦还在,哪怕梦醒了,花还在。令人惶恐的并不是梦的破碎,因为一个人一旦真正有梦,没有什么能碾碎它。梦醒了,繁花依旧在,只是这个世界已不再是我们熟知的那个世界了,这个春天已不再是我们所流连的那个春天了。
每当我意志消沉时,我都会回想起那个遥远午后,白发苍苍的姜老师走到我的身边,轻轻地将一份报纸放在我面前的课桌上,就像小心翼翼地播下一颗种子。
---------------
我和世界蓝色的秘密
王彤乐(22岁)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学生
我永远都记得那个下午。天蓝得像海,云朵像白鲸在游动,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份印有我名字的报纸揣在胸前,一路小跑回家去。那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是一篇抒发对大海渴望之情的小作文。那时候的我还没有见过海,是一个长相普通、学习普通、性格内向且毫无存在感的小女孩。
还没到家,就能闻到从楼道里飘出的饭菜的香味。“妈妈,你快看看”,我挥着那张报纸给妈妈看,妈妈在厨房炸土豆,光与她的影子纠缠不清。她一只手在围裙上擦着,另一只手接过我递的报纸,反复确认我的名字就在上面后,眼里便闪出无限惊喜的星星。
那天的晚餐除了土豆与白粥,还多了一碟我最喜欢的糖醋小排,那是记忆里我为数不多地令妈妈那么开心了。也是那个时候,我的梦中开始不断地出现大海,亮莹莹的海浪迎接风扑来,我和妈妈就住在大海边缘一座靠近太阳的草房子里,我写着那些触动了我的故事,妈妈也为此而感到开心,贝壳风铃不时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的少年时代就在这座三面环山、流水奔腾的小城里度过了。和这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我没有见过大海,喜欢抬头看蓝色的天空,我们怀着各自不同的梦想慢慢长大。尽管繁重的课业压力常常让我顾不上看书写作,但这份蓝色天真的秘密一直都在我心底被小心呵护。当我完全令自己置身于一本书中的时候,当我虔诚地敲下每一个字的时候,那种难以言说的奇妙感觉,赋予着我无限的力量。
到了高三,升学的压力总是令我情绪低落。我记得那个春天的某个星期六刚刚下完一场雨,我因为数学题而苦闷异常,在妈妈喊我吃饭的时候很久都没有回应她。直到她轻轻敲我的门,拿来水果并问我:“山上的花开得可漂亮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漫山遍野粉色的花,可我们却讲不出更多的话。“拍张照吧。”她说。我摇摇头。“多漂亮啊你看,春天一年就只有一次哦,错过了怎么办嘛!”妈妈执意要给我拍照。她把一簇粉嫩嫩的花往我耳前摆的时候,几滴残留的雨水划过她白皙的胳膊,夕阳隐隐约约地笼罩着人间,头顶的天还是蓝的,像那些毫无杂质的梦等待人们继续去完成。那样的时刻,脑海中便浮现出了人生的第一首诗。
后来我无数次在春光里写诗,看着蓝天,想象大海,将自己的秘密全都藏入诗句中,并在一本一本的诗集中得到人生的答案。我非常喜欢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一句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写作除了为让妈妈能感到开心点儿,“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或许也可以算是我的文学初心吧。因为文学,我不断地认识着这个世界,不断地筑造着自己理想的乐园,无比幸福地守护并延续着这蓝色美好的秘密。
伤心的时候,我会想象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兔子,长长的耳朵,绒毛柔软,并且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开心的时候,我更愿意在这闹哄哄的世界走一走,去感知更多的幸福,比如女孩子捧花时内心小小的期待,比如小狗摇着尾巴跑来时铃铛发出的清脆声响,这多么可爱,多么值得为此而完成一首美丽的诗。
随着我的长大,妈妈也在慢慢变老。每一次收拾行李箱,每一次看着车窗外的她渐渐变小,每一次降温她发微信提醒我加衣,这样的时刻,这份蓝色的秘密就又一次在我的心底涌动。我想有一天,我会写出关于大海的童话,会带妈妈去看海,会用文学抚慰好那些生活带给我的伤疤。
我很庆幸因为文学,我的生命里可以经历更多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我一次次被点亮,重新拥有力量,而这也是我和世界蓝色的秘密。我知道远方有大海,也知道妈妈和我一样渴望着远行去看海。世界有时候会不尽如人意,我们也会有太多无法完成的遗憾。但一路走来,文学总能令我看到蓝天中那弯弯亮亮的彩虹,这秘密那样纯粹,那样美好,像童年时养的兔子,低头晃动着柔软而洁白的长耳朵。
---------------
像犀牛独角一样只身前行
龙思韵(21岁,侗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华南师范大学学生
我文学创作的萌芽,在我的小学时代渐渐萌发。那时候,班里将郁雨君、伍美珍、沈石溪等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争相传阅,一张张小说页近乎印上全班一大半同学的指纹。纸张被无数人翻得脆响,纸面上不小心被沾上的油渍、汗渍等生得离奇的液体,也渐渐地与纸张“和光同尘”。只有打开书的扉页,上面书本所有者歪歪斜斜的字迹,反倒随着时光历久弥新。
在书中主人公们千奇百怪的世界中,流淌着他们丰富多彩的意识流向。当时我自以为对这个世界一知半解。然而,一本本文学作品启迪了我的心灵。
原来这个世界远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富奇,这些主人公的故事像潘多拉的宝盒,一股脑地将人物内心的语言、全知生活的怪诞倾盆倒出。每个人的生命纹理像深圳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如图章般篆刻在了我的内心,让我不自觉地想连根拔起、一探究竟。
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诞生我文学初心的缘由。
而在我的成长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动画片中,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质,每部动画片都拥有一个类似于“守护者”的形象,例如《西游记》中的孙猴子。这无形地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每个人都像一枝蔓延的藤蔓,在成长路上不断地寻找攀援、倚靠。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实则就是守护和被守护的关系。人情世界就是一座攻而不破的碉堡,这里边绵密的空气、复杂的格局形成了一个再生形态的二维空间,我没有道理不对这个“美丽新世界”感到好奇。
我的第一篇诗歌作品是以“灯”为意象,从遥远的天际到熟悉的课桌,从闪烁的星灯到烛灯再到台灯,我跃然于纸上的作品们也从碳素笔端、电脑荧屏再现到白纸黑字的印刷体,这种飞跃性的质变让我萌发出一种写作冲动,仿佛“未来”这个词化成了幻影和人形,他在朝我招手、命我接受招安。
即使在忙忙碌碌的初升高,我也从没放弃过写作。除了写作之外,我当时课余生活最大的兴趣就是看电视剧和电影,我在网络上搜寻了不少国内外的电影,电影里蒙太奇的创作方式和长镜头的洞察视角让我感觉新颖。
其实,从我决定进行创作为始,我一直在执着于描绘不属于我这个年龄段所独有的生命形式,我承认我是有点儿少年老成、言过其实、无病呻吟的偏执。我记得在我十三四岁时,以《莫拿婚姻的方式经营友谊》为题,反思了我长达6年的友谊经历,还凭此获得了某小作家创作大赛的二等奖。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年轻人的集体记忆少之又少,每个人脑中碎片化的拼图很难准确无误地卡扣在这个时代记忆的轨道中。可以说,我的成长和这个时代的其他同行人一样,是被中外不少影像影音、书籍著作影响并且镌刻的。
回览初心,荏苒时光如白驹过隙,我想起了韩国著名的女作家孔枝泳曾以《像犀牛独角一样只身前行》为题,记录和述说了当代女性对自我、对社会的和解和坚守。当时,身处青春期的我看完了孔枝泳的所有作品,心里备受感动,并且以同样的题目记录了我的成长生涯。从那时开始,文学近乎10年的潺潺流水渐渐穿透了时光、拂晓了每一天崭新的黎明,并由此吹皱了我“文学自留地”上的一池春水。
现在想来,也许我的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串串抛光的、连贯的手串儿,它是一组组破碎的镜片,镜面上的镜片照射出放大、缩小的我,投射出或肥胖或瘦弱、或苍老或稚嫩的灵魂。
所以,回览我并不一以贯之的文学初心,我一以贯之地决定以一只“独角的犀牛”自称。作为第二大陆生动物,犀牛的皮肤虽然很坚硬,但褶缝里的皮肤十分娇嫩,经常有寄生虫在其中,为了赶走这些虫子,犀牛们要常在泥水中打滚抹泥。
而犀牛这层坚硬的皮肤就是我对于文学意象世界的追求。从有到无、从多到少、从完满到不完满,是犀牛在泥地里打滚抹泥的目的,也是其对或美好新世界、或叛逆乌托邦的探索和追求。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