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40年|陈嫣婧:评价一个文本何以成为可能
 2021-04-12
2021-04-12


40年
回眸
对于一张以文学命名的报纸来说,40年的岁月,是时光的丰厚馈赠,更是一往无前的动力所在。40年激流成曲,奔腾而来,它属于每一位文学读者,属于每一位作家,承载时代的记忆,蕴藏关于未来的想象。生机之中,有着大众波澜壮阔的内心,也回响着属于文学的浪潮。我们约请多位作家回望一起走过的温暖旅程,也为自过去延伸向未来的这份友情留下文学的见证。
评价一个文本何以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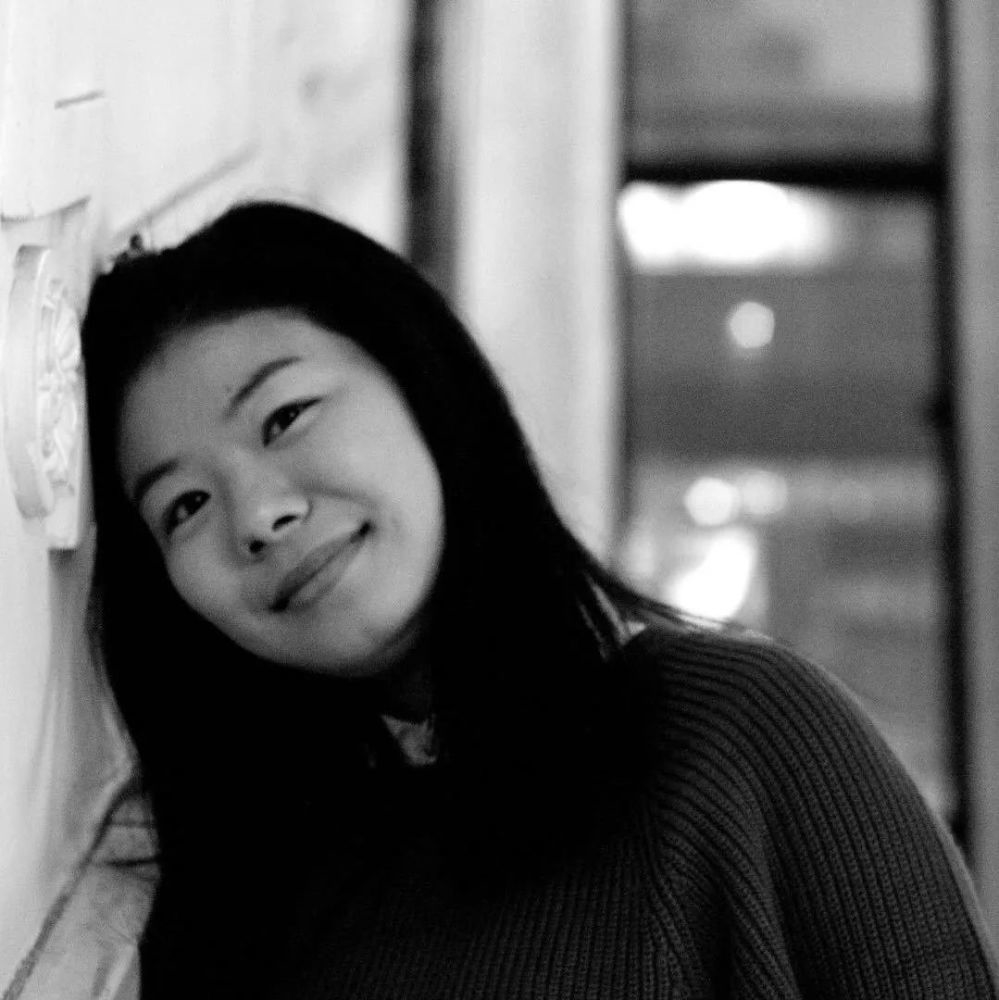
陈嫣婧 / 文
青年评论家
不知不觉间为《文学报》写文本评论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所做的,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对成熟的文学观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判断与分析。然而随着对这些单一文本的接触越来越深入,我发现作家的作品,甚至是作家写作的行为本身,无不指向了“文学是什么”这一非常原初,同时又很本质化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在探讨文学中的风格/德性,以及它的自律性/介入性时,文学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张力便会呈现在评论者的面前。这说明文学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一种表达方式,或一种价值载体,它的独特性和经典性至今依然在被追问。
其实在乔纳森·卡勒所著《文学理论入门》的第二章,作者就向我们抛出了这个问题。然而,卡勒紧接着便说了一句:“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因为“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东西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与那些公认的文学作品的相同之处反倒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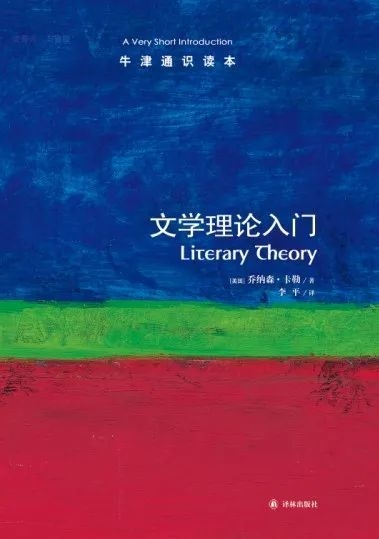
乔纳森·卡勒
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单一的文学作品首先应该是独特的,但风格化却妨害了它的典型性,使它变得难以归类,而若无法归类,那么判断这个作品属不属于“文学”,就完全成了一个多半凭直觉少数凭经验的不靠谱行为。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不靠谱,或者说意识到了文学与建立在现代文明体系之下的其他众多学科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即它本身作为一门学科的不确定性,“文学是什么”才会被当成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但其实,当产生了为它下定义的欲望时,我们自身都已多少带着一套基本的价值判断,只不过并不见得都能为自我所认识。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超出自己价值判断的那一部分就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诸如形式/内容,文本/作者,审美判断/意识形态这些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身就不可能非此即彼,全然对立。也因此,基于这些基本元素所展开的各种争论就变得无可避免同时也非常重要了。
以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为例,有些论者认为文学不能完全逃避伦理道德的责任;而反对方则认为这责任事实上是让文学作品强行背负起 “文以载道”的义务,反而妨害其抵达它本该有的纯洁性。如果纳博科夫还活着,相信他一定也会站在反对一方的。因为对文学纯净度的追求,正是纳氏最根本的文学观。他在给美国几所大学讲授文学课程的讲稿中一再强调文本形成自身规律的重要性。他赞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对叙事时间的精准把握,却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名其妙的感伤主义假得可以。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他强调 “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不然这门艺术就成了无所作为的行当”。从中,虚构与现实世界在纳博科夫那里的关系已经被说明得很清楚了。小说作为一门立足于 “虚构”的“技艺”,必须做到“以假乱真”的极致,也就是说,通过一种绝对的完美的“假”,来达到绝对的完美的“真”。相对来说,现实世界的“真”,不过是一堆 “杂乱无章的材料”罢了。从第一代评论家对《洛丽塔》的反应来看,纳博科夫无疑十分成功地践行了他的文学观,他亲手建构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美学王国,让一切现实的原材料,包括人们对固有道德观的粗暴判断在这个文本里得到了重新洗牌。


纳博科夫
然而问题是,即便《洛丽塔》是纳博科夫文学观的完美体现,这是否等于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就能够使作者完全置身事外,保持中立?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非人格化叙述所可能造成的距离的混淆,道德判断的晦涩,这些都是典型的现代文学的征候。作者有意识地撇清自身与文本的距离,尽可能不参与小说的叙事,而将叙事责任推到小说人物的身上,做到极致,就成了《洛丽塔》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在传统小说中,我们往往会认为作品中的“我”暗示的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但在 《洛丽塔》中,“我”不仅不可能是纳博科夫,更不可能是除了男主人公亨伯特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个小说实际上是亨伯特的“自我供述/辩护”,它相当于一个闭环,只能呈现亨伯特一个人的逻辑和情感。而这也就意味着小说切断了其他任何一条可能通往亨伯特,以及判断评价他的道路。如果说芥川龙之介的经典小说 《竹林中》是将 “不可靠叙事”中的“不可靠”发挥到了极致的话,那么《洛丽塔》则是尽量将 “不可靠叙事”变得“可靠”,让亨伯特变得“可信”。然而,文学史中所有意图将文学从日常价值观中抽离出来,并赋予其独立价值观的努力最终都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纳博科夫并不是第一位。举个更早些的例子,19世纪后期波德莱尔等人开始奉行的“唯美主义”文学,就真的做到“唯美”了吗?所谓“恶之花”,没有“恶”的铺垫,“花”的审美价值从何而来?由此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中间存在一个逻辑前提,即“善/恶” 逻辑。这个逻辑是可以被作者在作品中生产出来的吗?文学作品不但不能生产价值观,甚至还必须与固有的价值秩序构成某种对话关系,哪怕是以背离、反诘的方式构成,而《洛丽塔》的美学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成立。
作为一种对过分强调小说“审美”功能的反拨,指出艺术潜在的道德责任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出于“审美”,我们对人性,特别是人性的幽暗面产生理解,施加同情,这完全可以。但我们反过来追问这种同情的立足点和局限性,同样也可以,特别是从作家本人的角度出发去维护其所持的创作观念,这不但极其必要,甚至可以说是立足作家作品研究的传统方法的。但批评家进行文本解读时,基于自己的立场,使用正确的方法,只要能自圆其说,亦未尝不可。比如在对文本进行叙事学相关的论述中,我们能看到的最好证据,就是对“第一人称自我叙述”的分析。正因为这种叙事方法完美地规避了道德论断,反而使得读者阅读小说时的道德焦虑显得尤为突出。总之,文本自身的开放性带来了评论视野的开放性,但文本自身的完整性同时也对评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即评价逻辑的自洽。当我们通过一篇评论来理解“文学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揭示文学的特征,这些特征不是一些具体的、既定的内容,而是在批评的过程中生成的一种角度或一套方法。
■ 《海上学人》
策划:本报编辑部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1981·文学报40周年·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