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伯庸新作首发《收获》:但问荔枝“如何来”?


马伯庸
拥有780万微博粉丝的“马亲王”马伯庸又出新作了。
这一次,他的小说《长安的荔枝》首发《收获》长篇专号2021年春卷。这是他首次以小长篇亮相传统文学期刊,也是《收获》首次发表马伯庸的作品。此前,马伯庸的散文已得到纯文学界的青睐,2010年,他的《风雨》与贾平凹的《一块土地》一起获得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他的《宛城惊变》、《破案孔雀东南飞 》等又获得朱自清散文奖。

马伯庸首次以小长篇亮相传统文学期刊,《收获》首次发表马伯庸的作品。
而小说新作和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有关,讲的是唐朝“荔枝使”李善德如何把“ 变,两 变,三 味变”的鲜荔枝从岭南运到五千 之外的长安的故事。李善德是算学及第,老实本分,因被同僚算计而被迫接下这烫手的任务,却能通过各种数据的陈列、运算和推演,争分夺秒地无限逼近那个在当时“绝无可能”的任务目标。
和《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一样,《长安的荔枝》又是一篇让人读来酣畅的历史小说。马伯庸拼接起那些历史的碎片,带来一个熟悉又陌生,过去又现实的阅读体验。在虚构和真实之间,马伯庸很喜欢大仲马的一句话:“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用来挂我写小说的大衣。”
小说里那个疲于奔命的李善德也让人想起眼下流行的“社畜”,甚至有读者和马伯庸说,这个故事看到一半便不忍看下去了:“我每天上班就够苦的了,为什么休息时看篇文还要再遭一次同样的罪?”马伯庸就想,小人物的窘境与烦恼,真是不分古今的。
如今他自己虽然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也要每天早上6:20起床,做早饭,送儿子上学,接着去工作室写东西,写到下午5点回家。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要把工作和家庭生活分开,回家后笔记本一关就绝不再打开,灵感再好也不。在《长安的荔枝》后,他迅速投入了新的创作。
近日,马伯庸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表示自己又在吭哧吭哧写一篇大稿子,因为故事背景的专业领域有点艰深,所以写起来比较费劲,但边学边写还是挺开心的。
“具体什么领域,我还要保密。有时我也搞不清楚,我是为了写小说才去了解一个陌生领域,还是为了找个理由去探索陌生领域,才开始写小说。”

【对话】
澎湃新闻:为什么想写《长安的荔枝》?是因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给了灵感吗?
马伯庸:这篇文章的最早缘起,要追溯到我阅读明代徽州文书的经历。当时我在一份材料里看到一个叫周德文的徽州人。永乐七年,朱棣决定迁都北平,把周德文一家强行从徽州搬迁到了大兴,充任厢长,负责催办钱粮 、勾摄公事——其实就是去全国各地采购各种建筑材料,支援新京城的建设。
周德文这份工作很辛苦,他自己说“东走浙, 西走蜀,南走湘、闽,舟车无暇日,积贮无余留,一惟京师空虚、百职四民不得其所是忧,劳费不计。凡五六过门, 妻孥不遑顾。 ”最后他因为太过劳碌,病死在了宛平县德胜关。
这是历史上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但和永乐北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却有着密切联系。如果我们用周德文的视角去审视史书,你会发现,每一件大事背后,都有一群琐碎的小人物在支撑。所以说,千古艰难唯做事,一事功成万头秃。可惜史书对这些小人物关注得实在不够多。
去年我和一个朋友聊杨贵妃,说起荔枝,我猛然想到了周德成。“一骑红尘妃子笑”,大家历来关心的都是“妃子笑”,可很少有人想到“一骑红尘”背后的艰辛。为了完成这个工程,是不是也有许多周德成这样的小人物忙到头秃。我很想从这个角度写一写,于是便有了是篇。
澎湃新闻:我看到故事还写到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李善德看到《三辅 图》 记载的汉武帝往事,说汉武帝为了吃到荔枝也从岭南移植了 批荔枝树种到 安的上林苑,但那批荔枝树在当年秋天就死完了。李善德于是想, 百年前的上林苑或许也有 个倒霉的 官吏摊上了荔枝移植的差遣,并为此殚精竭虑,疲于奔命。
小说写到这里,还有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可惜史书 ,是不会记录这些琐碎 事的。后世读者,只会读到 ‘武帝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 ’短短 句罢了。”这句话放在李善德所在的唐朝是成立的,放在我们今天也是成立的。它也潜藏着你写《长安的荔枝》的原因吧。
马伯庸:是的,为小人物树碑立传,是我的情怀所在;怎么为小人物树碑立传,则是我热衷的创作方法论。大时代、小人物、精准的切入点,这三点我认为是新时代历史小说的重要创作方向。

马伯庸最新小说《长安的荔枝》首发《收获》长篇专号2021年春卷
澎湃新闻:《长安的荔枝》前后花了多长时间?再写唐朝会更得心应手一点吗?有写“长安”系列的计划吗?
马伯庸:事实上,这次创作不在我的计划之内,纯属意外。不过写作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写出什么来。恰恰是这种意外,伴随而来的是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从动笔到写完,前后七万字,完成恰好是十一天。
因为之前写《长安十二时辰》我查阅了大量文史资料,这些东西都留在脑子里,所以这次动笔,写得格外酣畅,心无杂念,既不考虑读者感受,也不考虑出版前景——七万字的长度实际上很难出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率性而为,很是开心。
澎湃新闻:小说主人公李善德要找的那条把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的路线,也是小说作者马伯庸要找到的路线。在小说里,为了确保贵妃能于生辰之日吃到新鲜荔枝,李善德在正式运送荔枝之前有过三次实验,用排除法把从岭南到长安的运送路线从四条变成两条再到最后唯一的一条。从地形地貌到交通流转,这条路写得极尽详细。
古今地理交通有着天壤之别。我好奇的是,今天的你如何找出这条古代的路,并有底气写下“除 是腾云驾雾,否则再没有 这条路更快更稳的了”?
马伯庸:古人的工程和交通技术不够发达,并无移山填海之能,只能依傍山川形势而行。因此只要地质环境未有大的改变,道路走势基本上是可以预测的。譬如秦岭横亘于关中与汉中之间,自古只有子午、骆傥、褒斜、陈仓四条山间谷道和一条祁山大道可资利用,无论诸葛亮出川还是杜甫入川,都必经其一。尤其唐人热衷于旅游行散,留下大量各地风景、地形、水文、驿途、里程等地理记录。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打开电子地图的地形图,按照文献记录逐一比对,便可以得出合理的路线。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唐代运送荔枝的真实路线,只是依循常理推想出来的路线。它符合历史逻辑,未必就是历史真实,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探讨罢了。
澎湃新闻:“荔枝 变,两 变,三 味变。从岭南到 安,远近不下五千 路。”要保证荔枝新鲜地抵达长安,除了提速(找出那条最快的路),还要尽量延长途中荔枝保鲜期。小说里写到了各种荔枝的古早保鲜法,最后“ ‘分枝植瓮之法’‘盐洗隔 之法’, 共能争取到 天时间”。这些办法是你自己想到的,还是有出处可依?
马伯庸:书里提到的荔枝保鲜办法,都是参考自历代农书与笔记。比如“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这句话,即是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所说;“分枝植瓮之法”取自宋徽宗的,另外在宋代蔡襄《荔枝谱》、明代徐勃《荔枝谱》 以及吴应逵《岭南荔枝谱》中,亦有相关记载。有一些办法,我还验证一下其可靠性。比说文献记载有一种保鲜方法,讲水果放入竹筒中密封,可以保鲜。我开始并不理解这么做的意义,请教了农学专家才学到一个科学解释:密封的竹节会降低氧气浓度,提高二氧化碳浓度,从而减轻水果的呼吸强度,确实能起到一定保鲜的作用,古人诚不我欺。
这些保鲜办法其实是历代劳动人民想出来的,发明时间不一。我稍微在文学上夸张了一下,让它们统统集合在了唐代出现。我的挑选标准有两个:一是要符合科学原理;二是以唐代的科技水准能够视线。只有符合着两个条件,读者才会觉得可信,从而理解主角的不易之处。
澎湃新闻:你本身是一个对数字十分敏感的人吗?
马伯庸:我对数字不是很敏感,数学成绩也不好,但我对数字里呈现出的理性之美一直很迷恋。它是客观的、冷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岭南到长安的距离五千里,不会因为杨贵妃的娇嗔而缩短哪怕一寸;驿马的体力极限每天四个时辰,不会因为主角着急而提升一秒。我一直觉得,所谓的现实主义,就是描写人类这种感性动物如何去适应这个理性的世界。
澎湃新闻:“新鲜荔枝在唐代怎么从岭南送去长安”,这个问题本身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但背后涉及历史、地理、农学、算学诸多领域。你笔下这个“送”的过程让人大呼过瘾。为了确保它逻辑严密,让人信服,你会在心里反复推演这一路的过程吗?我发现你的许多作品如《长安的荔枝》《两京十五日》《草原动物园》都写到了运转、路途,你似乎对“一路的过程”特别着迷,为什么呢?
马伯庸:一直以来,历史记载的倾向往往重宏大而轻微观、多上层而少基层,史书里关于帝王将相、权谋政治的记载汗牛充栋,可对于琐碎的技术细节却吝于笔墨。就拿“一骑红尘妃子笑”为例,我们在唐代文献里几乎找不到这次运送的细节,甚至连荔枝究竟产自何处这种最基本的问题——岭南还是四川——都没有明确记载,以致后世众说纷纭。
不独荔枝,很多事情都在历史长中被磨蚀掉了细节,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大轮廓。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我们并不清楚具体的工程细节,除了蒙恬、扶苏之外,一个负责人的名字都没流传下来;汉武帝北征匈奴,我们只见到气吞万里如虎的汉骑精锐,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后勤物流如何调度确保?记载极少,我们只能从残缺不全的边关汉简里去寻找答案。所以我一直想写一点不一样的历史故事,从感情上去关注一下不被记录的小人物;从技术上去表现一下他们的艰辛与苦恼。

《两京十五日》书封。
澎湃新闻:虽然《长安的荔枝》写的是历史故事,但其中很多细节会引起我们超乎历史界限的思考,比如官场里的“马球盛况”、“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 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 ”……我想即使是历史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本人对现实世界的关切与思考。对你而言,《长安的荔枝》的现实意义是什么?你想过写现当代的故事吗?
马伯庸:一般来说,作者总结自己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挺尴尬的。不过有一次我问读者,历史小说里讲的都是发生过的事,角色都是早已死去的人,你一个现代人明明与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究竟为什么会去阅读呢?那个读者自己也不清楚,跟我聊了很久之后,我们同时得出结论:任何一部历史作品,都隐含着它的现代性。现代人与历史作品最重要的连接,就是读者与古人产生共鸣,有着超越时间的感同身受。
我最喜欢的一部历史小说是徐兴业先生的《金瓯缺》。这部小说是以北宋末年作为背景,从海上之盟讲到靖康之耻。徐先生构思这部小说初稿是在抗战期间,他虽然写的是徽宗一朝的腐朽与愚昧,但那种忍看大好河山沦为虏手的痛惜之情,同样也回荡在现实层面。
如果一定要总结出《长安的荔枝》的现实意义,我想应该是“社畜”二字,讲的尽是职场上班族们的苦楚。小人物的窘境与烦恼,不分古今。事实上,曾经有读者跟我说,他看到一半不忍看下去了:“我每天上班就够苦的了,为什么休息时看篇文还要再遭一次同样的罪?”

《长安十二时辰》海报。
澎湃新闻:你最近的几个历史小说似乎都有几个特点:第一,时间紧张。《长安的荔枝》要在11天里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两京十五日》要在15天里从南京赶到北京,《长安十二时辰》则在天宝三年元宵节的12时辰内上演;第二,必有“阴谋”;第三,极尽细节。你介意有人因此评价你“重复”吗?
马伯庸:我的作品里的“阴谋”不能算阴谋,只是主角逐渐见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对细节的渲染也不存在重复这个说法,这是小说创作的技法之一;只有时间压力这个特点,确实是我最近几年的创作兴趣,但如果了解我的创作履历,就会发现我这个人没常性,每隔几年就会换一个口味,不会在同一个风格上停留太久。
澎湃新闻:你也会写《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样的非虚构历史纪实作品。同样的历史类写作,你更喜欢写虚构还是写非虚构?在难度上,哪一种于你更有挑战?
马伯庸:非虚构的难度更高一点,因为你不能杜撰了。当初我在撰写《显微镜下的大明》时,非常痛苦,因为要拼命抑制自己创作的热情。一件事,明明这么发展,会更有戏剧性,寓意会更深刻,为什么它却戛然而止?如果我多加一笔,是不是就更精彩了?我必须时时把小说家的热情按回去,反复告诫自己在写非虚构。
《藤野先生》讲过这么一件事:藤野先生批评鲁迅的解剖学笔记,说你把血管位置挪了一下,虽然比较好看,然而真实情况不是这样。这也是我在写非虚构作品时,不停提醒自己的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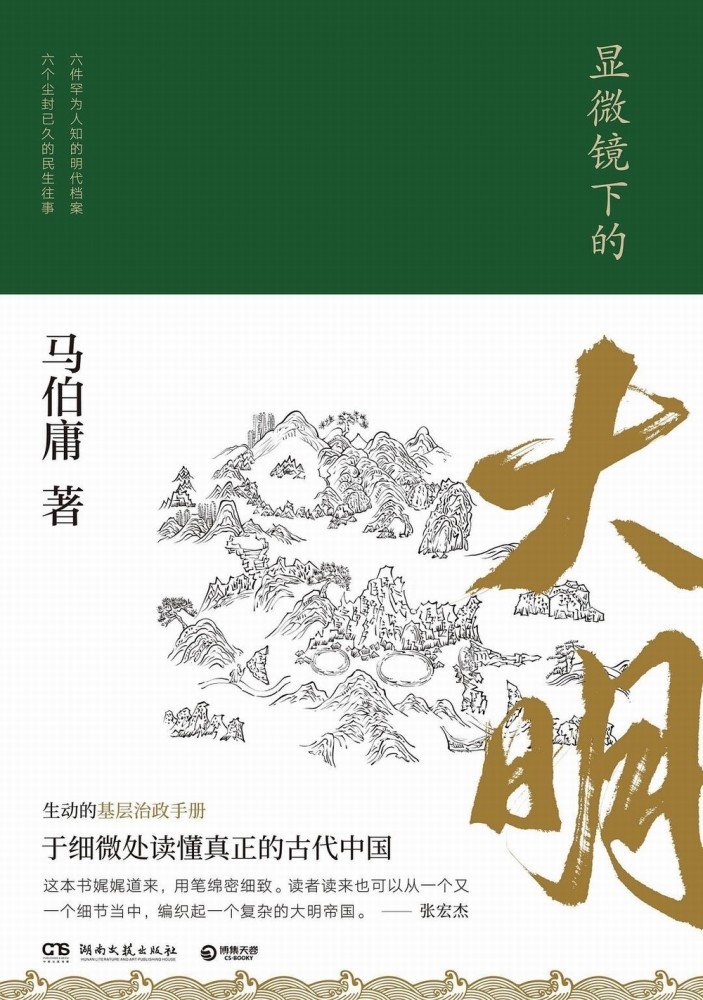
《显微镜下大明》书封。
澎湃新闻:你认为虚构与真实的边界在哪里?
马伯庸:虚构与真实的边界在于逻辑。一个历史事件,往往有三种选项:“逻辑上不可能发生”、“逻辑上可能发生”与“事实已经发生”。我们拿杨贵妃为例,倘若要写一个“马嵬坡之变”的主题,该怎么写?写杨贵妃被神仙接走,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是完全的虚构,这正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可以写杨贵妃确实死在了马嵬坡,完全符合史实,这就是现实主义作品;但还有第三条路:历来有一个传说,讲杨贵妃是假死,其实被遣唐使所救,东渡日本,甚至山口百惠还自称过是杨贵妃后人。它是真实的吗?我们无从证明,大概是杜撰的,但从逻辑上说它是不是可能发生呢?当然可能,哪怕只有1%的可能,也是可能。文学作品的发挥空间,就在这种逻辑的可能性中。
澎湃新闻:这次《长安的荔枝》首发《收获》,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年初《收获》举办过一次跨界论坛(“无界对话:文学辽阔的天空”),请来了悬疑、科幻、网络、影视等各领域的写作者。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怎么看待类型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关系,或者这样的区分本身就是没有必要的?
马伯庸: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网络作家,只是喜欢在网上分享一些作品,所以对我来说在杂志写稿和在网上发表没有区别。我认为文学的分类、定位以及评价,是评论家和文学史研究者们的工作,作家并不需要承担这个工作。我相信大部分作家在动笔之时,脑子里不会浮现出这些条条框框,她或他只是迫不及待地把想用文字来发泄自己的表达欲,发自内心,源于冲动,倘若时时想着自己的作品该是如何分类,便着相了,写不出好东西。
我一直认为,作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状态,当你有了表达欲望,并试图用文字表达出来,那一段时间你就是作家。
澎湃新闻:你喜欢的作家都有谁?
马伯庸:太多了,中国的老舍、汪曾祺、王小波,日本的司马辽太郎、村上春树、隆庆一郎,欧洲的毛姆、茨威格、凡尔纳、布鲁诺·舒尔茨、道格拉斯·亚当斯,美国的马克·吐温、阿西莫夫,南美的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博尔赫斯等等。
澎湃新闻:如果不当作家,也不去外企,你最想做什么?
马伯庸:不当作家的话,我最想去做个人寿保险经纪或房屋中介,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去观察这些人面临生死问题与财产大事时的变化,应该很有趣。当然,我说得太轻松了,更大的可能是,我因为巨大的业绩压力而日日忧虑,以致头秃。这样就回到了我们最初的主题:还是“社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