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青年小说家、青年诗人、青年作家……的信

年轻人梅格攻读数学的决定令华威大学数学教授伊恩·史都华十分高兴,却也为年轻人对职业决策的担忧感到哀伤,但他也非常理解这个问题:“是否必须放弃对美的感受以研读数学。”
这位数学科普作家从彩虹的几何学角度出发,提出了“你所见到的彩虹不同于我所见到的“这一鲜为人知的事实,得出数学上的浪漫结论“彩虹是个人经验”。与梅格的忧虑相反,数学一直提供他一种更有想象力、更能丰富情感体验的方式,感知世界的奇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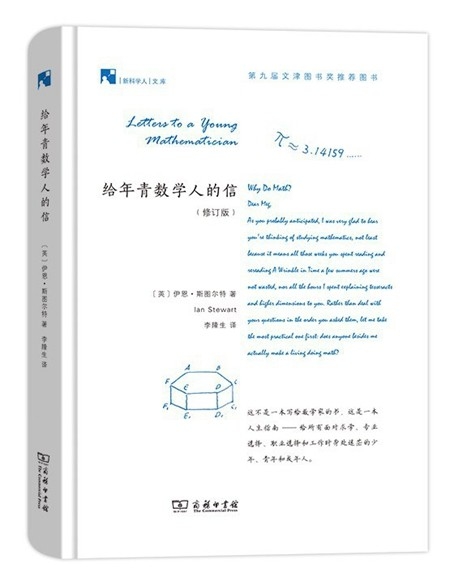
《给年轻数学人的信》
年轻人是乐观的,也是动摇的,需要找到一种前途获得对自己的答复感。经历过寄希望于奇迹的中年人,通过书信间的回应和探讨,把年轻人的困境变得普世起来。
想把文学爱好当前途的年轻人,也在寻求建议。略萨收到的信带他重温了十四五岁时的抱负和苦闷——“我感到我的抱负仿佛一道紧急命令。”
略萨的建议开门见山,以至于我来回翻了几次,确认并非自己漏读了序言或译者代序。信件内容几乎全部聚焦于虚构小说创作,又像一部枝繁叶茂的私人书单,用优秀小说家的作品来描写他们为迷惑读者而使用的魅力手段。将语言、风格、视角、结构、时间维度、现实层面等要素从小说中一一剥离,阐释它们如何作用于一部小说的说服力——小说的主题本身没有好坏,主题的好坏是通过其他要素的活动方式形成的。

《给青年小说家的信》
它们的出现必须是必要的,即便平实,但得真诚。在略萨看来,真诚和虚伪在文学中无关道德,关乎审美。它们的存在必须是有效的,小说才能因此自力更生,从小说家独立走向读者。小说技巧是后话了,何况小说中最高明的技巧是“出色的隐藏”,藏起你所知的,但保留它们的影响,表面上的朴素其实掩盖着“巨大的创造勇气”。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致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写信人提到自己有令人不快的呕吐小兔子的习惯时,现实层面质的变化就像穿帮镜头一样发生了。
虚构的才能起源于对现实的反抗,是“主观的、想象的、非历史的”,也如博尔赫斯再创造的、从足部开始吞食自己的神话动物卡托布勒帕斯,不断自我挖掘,寻找编造的机会。创作一部虚构小说的过程是建立虚构小说主权的过程,也许年轻人就是小说本身。
年轻人也是梵高《春》里的那棵树,比起脸谱化的春日明媚,《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初版译者冯至先生,更赞同他们是个“没有夸耀的春天”,“还在忍受着春寒,四围是一个穷乏的世界,枝干内却流动着生命的汁浆。 ”

《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写下这温和的十封信时,里尔克自己还是个年轻人。但他用预言的口吻告知你似乎不可逆的未来。“你的寂寞将渐渐扩大,成为一所朦胧的住室“,“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在根本处,也正是在那最深奥、最重要的事物上,我们是无名地孤单”。又总是怀着仁慈,留下一条退路。“自有一种幸福,无须脱离这个幸福才能扩大你的世界。”“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来到。夏天终归是会来的。但它只向着忍耐的人们走来。”在里尔克的信里,年轻人的悲伤不会因为他的坦诚而滋长。
“爱”似乎是他解决问题的首选。像“爱一间锁闭了的房屋”一样爱你所遇到的“问题的本身”,把它们当作自有本来生命的事物去相处和承受。爱这世上的体验,“你还不够做一个诗人来呼唤生活的宝藏。对创作者没有贫瘠,也没有无关痛痒的地方。”用爱理解艺术品中无穷的寂寞,不要妄下论断,认识它们的价值。爱世界上的危险,因为那“危险的不安定是更人性的”,因为世界并不敌对我们,“如果它有恐惧,就是我们的恐惧。”里尔克向人类负面的感情表示敬意,但绝对反对默许或错置情感冲动。不要被它们支配,用爱叫它们反水。这种爱无法单枪匹马,需要勇气支撑,或忍耐酝酿,或谦卑填补,理应是美德中最成熟的形式,却是他建议对付这个世界的最直接的武器。
恰如收信人所说的,当他们停止信件往来时,他已被赶入“正是这位诗人用温暖、和蔼而多情的关怀”为他“防护的境地”。 这十封信就是书中提及的临时避难所。
虽然以里尔克“请你走向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给青年作家的信》“我无法教给你什么”的开场背书,很快,科伦·麦凯恩毫不留情地将年轻人逼上冯内古特的悬崖,让他们“在坠落中不断强硬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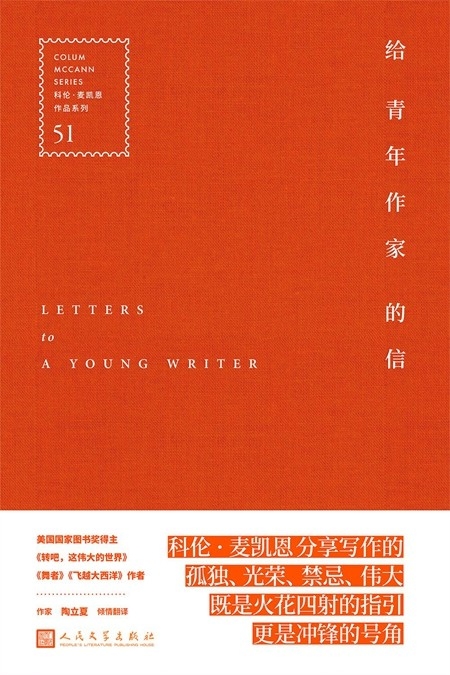
《给青年作家的信》
正因为“所见与所知之间的关联从不确切(约翰·伯格)”,年轻人必须向世界敞开自我,保持敏锐并因此痛苦。痛苦是我们需要的,这里指的是被触动的痛苦,科伦称之为“执念”。“找到能与之抗衡的语句让执念消失”,书写正是为了从对痛苦的感受中实现自由。边界在他的创作观念中也十分重要,因为边界不仅让你知道自己支持什么,也知道自己反对什么。边界也当不断被挑战,“别写你知道的”,他建议年轻人,“将自己逼进最黑暗的角落,发现一些自己知晓却尚未意识到的事”。
那些落笔给年轻人写信的人,一样受益于老师、家人、阅读过的作者,但同时经历过出走、完成了脱离的时刻。在“没有人能帮你”“我无法教给你什么”被过度使用以致失去意义之前,它们是一种承诺,承诺拒绝年轻人的依赖,而要他们从所受的影响中独立出来。科伦·麦凯恩曾把小说《舞者》的初稿寄给约翰·伯格——“这位作家写的每个字我都想占为己有”,约翰·伯格手写回复了六页批注,包括一条删除的建议,辅以科伦看来也十分有力的证据。问题是,这是科伦自己最钟爱的内容,为它倾注了半年时间。科伦无法忍受地背叛了自己的英雄(或许里尔克说的“请走向你的内心”为他提供了最终服从自己的证据)。而小说出版后,他收到了一封“最美的信”,约翰·伯格为自己的建议向他致歉。
科伦很清楚这一点,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但自己的声音是从多个别处获得的。要燃烧,火花即是所得亦是所需,要自己学会握拢,再把火光传递给下一代年轻人。他写下《给青年作家的信》,把年轻人“带往火焰的方向”,在那里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将在何处被灼伤”,当他们意识到时,也已看到火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