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赵松:在小说中“等待”无限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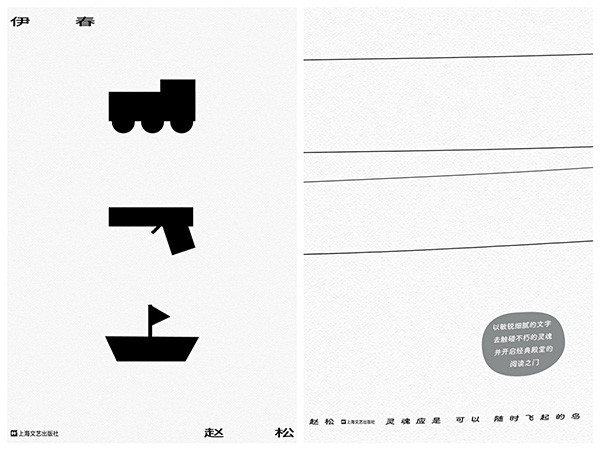
1月9日,小说家赵松与小说家小白、批评家张定浩做客思南读书会,带来一场题为“小说的制谜与寻解”的对谈。
有趣的是,这一期的读书会主题和上一期有了某种奇妙的呼应。上一期来了小说家李浩,李浩带来了他谈小说的《匠人坊》。这一期来了小说家赵松,赵松同样带来了他谈小说的阅读随笔集《灵魂应是可以随时飞起的鸟》,还有自己的新小说集《伊春》。把这几本书放在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家在作者和读者两种身份之间的微妙关系。
赵松说:“我始终觉得,一个写小说的人读小说的角度会和大多数读者不太一样。写小说的人一定有自己独特的读法,这个读法还和自己的写作有某种关系。”
张定浩认为把赵松品读小说的作品和赵松自己的小说“比对着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赵松是一个非常难以评论的作者,他的小说给人以阅读的快感,但这种快感分析起来有点困难。但我们读赵松对其他小说家诸如克洛德·西蒙、玛格丽特·杜拉斯、塞萨尔·艾拉等人的谈论,往往可以从中看到他对自我小说的期许。作家文论在西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文类,但中国当代小说家同时写文论的还不够多。就我所知,赵松可能是当代中国小说家里对于文论写作非常自觉和成熟的一位。”

1月9日,小说家赵松与小说家小白、批评家张定浩做客思南读书会,带来一场题为“小说的制谜与寻解”的对谈。
走进孤独者的世界,“等待”那个时刻
赵松的短篇小说集《伊春》和阅读随笔集《灵魂应是可以随时飞起的鸟》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对于《伊春》,张定浩的评价是“一部很勇敢的作品”:“赵松是东北人,东北是当下现实主义的富矿,但凡谁写出了东北故事,一群批评家都蜂拥而上,但赵松完全不直接写这几十年来的东北。他写的是孤独之人内在的精神状况。”
“但和许多文学青年不同的是,他写孤独的人,但这个孤独者并不自恋,并非只看到自己,相反一直在留心外面的世界。《伊春》这本书写到了各种各样孤独的人,但你会发现这些人依然愿意与他人交往,愿意帮助他人,哪怕这种帮助是徒劳的。这是赵松这本小说最令我感动的地方,他相信再孤绝的个体都依旧葆有与他人交流的可能。”
另一方面,“沉浸式体验”也是张定浩对《伊春》的一大感受。“赵松很注重两个方面,一是细节,一是环境,他的文本需要读者自己参与进去。”在张定浩看来,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基础是信任。首先赵松信任读者——有时间和耐心去进入他的小说;其次读者也信任赵松,愿意前往那片由语言筑成的空间,自行探索。“当代很多试验小说之所以让读者始终读不进去,那根本不是读者的失败和时代的问题,而是作者的失败。有能力的作者是能够在三言两语间就吸引读者投身其中的。”
赵松的小说很少讲述一个完整的人的故事。他总觉得,去讲这些故事还不如去看社会新闻,看网上各种不可思议的段子。“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我想写小说的人能做的恰恰是退回相对个人化的视角里,有距离地去观察、想象,构建一个可以让人慢下来的文本,而不是去急于编织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或者有诡异体验的东西。”
小白的小说观和赵松不同。在小白看来,小说还是叙事,重点是作者能讲出事情。“赵松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退缩的状态,因为有电视、电影、游戏、虚拟现实……这些东西的功能或许比文字还要好,所以他退缩了。但我还是更愿意去讲事情,愿意讲那些不一定讲得出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对小说的基本判断可能还是有点差异的。”
“但我也理解赵松。”小白说,赵松的小说其实是在一种“等待”的状态,一开始赵松自己都是模糊的,如果读者愿意等待,最后会和赵松一起进入一个美妙的时刻。“这种‘等待’其实也是一种叙事,它需要读者与作者一起进入。”
“小白写小说,他眼睛很‘毒’,用了‘等待’这个词,我忽然觉得就是这样。”赵松回应道,“我确实在小说中设置某种延滞的效果,有一种‘等待’在里面。而真说在‘等待’什么,我又没有确切的答案。这可能是我试图强调的孤独者的某种状态或者语境。孤独者的故事跟波澜壮阔的故事总是反向的,孤独者的故事都发生在内心深处,都是些只言片语,一些断断续续的甚至不能用语言轻易道来的东西。这样的人可能会很多,他往往被湮没在人海里,你看着他的脸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是我在小说里很关注的一个点。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认为,他们的世界有某种很微妙的不确定性,能够在充满确定的环境里延展出奇异的不可想象的变化。”

作家赵松的短篇小说集《伊春》和阅读随笔集《灵魂应是可以随时飞起的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不确定”是人生样态,也是小说的落脚点
张定浩发现,赵松似乎特别喜欢机场这个意象,好几篇小说都写到了一个人对机场的迷恋。“机场是体量庞大的、沉重的,里面容纳了各式各样的人的秘密,但在某些时刻又不断会有飞机呼啸而起。在这庞大的有秘密的沉重所在中,始终有轻盈飞翔的可能。机场是一个中转站,不是开端也不是结局,它收留很多的秘密,同时也给出各种各样的可能,这种不确定是人生的样态,也是赵松小说的落脚点。”
“机场在不同的小说里出现过几次。”赵松说,最典型的是一个人出差,下大雨了,一个人被堵在高架上,非常焦虑,一会想飞机会不会晚点,一会想飞机会不会不飞了。最后快到机场的时候,领导那边传来信息说今天不飞了,明早再走,但那个人也到机场了。“这时他突然觉得没什么事,可以在机场逛逛,没有任何指向性行为,那是很好的时刻。”
而“没有任何指向性”,也一直是赵松希望的样子。“我对我的小说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必须保持某种可能性。对我来说,只要发现了可能性,并且在文本里保留了这种可能性,甚至放大了这种可能性并赋予它很微妙的层次,我的小说就达成了我所追逐的某种期待。”
他还说到,现实世界的有限往往来自于生命的有限,这种有限性本身带有悲剧性色彩,文学存在的价值就是试图在这种有限性里寻找某种无限的可能。“我看了一部小说,感受到一个异样的世界,它带来的体验是我日常中没有的,就像包法利夫人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她一直这么活着。我并非说我比别人多了什么,而是我的思维和想象让我打开了一个个通道,让我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出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之所以坚持写阅读随笔,也是他希望自己在有限生活中能保持阅读与学习的习惯。“人从婴儿长大成人,学习一开始是个开放的过程,然后又慢慢走向封闭。当人被定在某个位置上,你是一个工作者,你要养家糊口,你要去生活,你会越来越被‘定型’。当这一切都确定无疑的时候,你的感知力和想象力都在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越是确定无疑的状态,越会让你陷入‘再也没有新感觉’的可能,它比生命消失本身还要令人不安。”
也可以说,赵松自己的人生选择也是打破“确定无疑”的最好印证。上世纪90年代,赵松是中国石化抚顺分公司厂办调研组的一员,主要工作是给领导写报告,手捧“铁饭碗”,日子很安逸。后来他成为他们单位的“奇葩”——第一个辞职的人,就因为“未来是什么样,一眼就看到了。”

赵松
法国“新小说”的影响:一个作家的死亡有两次
赵松还曾是先锋文学群体“黑蓝文学”最早的核心成员之一。从2007年出版的《空隙》、2015年出版的《抚顺故事集》到2017年出版的《积木书》,他的作品风格受到了法国“新小说”很大的影响。
“这个流派里的每个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玛格丽特·杜拉斯,他们完全不一样。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话讲,能让这群‘孤独者’聚集的,恰是他们都反对传统,或者说拒绝从十九世纪初期留传下来的所谓‘现实主义’叙事规范。他们永远在反对模式化,尤其是‘意义’、‘深度’这些已经被大学教授和人文主义不断强调和固定的东西。阿兰·罗伯-格里耶就认为,小说文本就像艺术品,没有内在的东西,所谓的外在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
这些前辈是如此地强调观念和方式的独立性,他们给赵松带来的另一大启发是:如果把每个人的写作都视为一条可能的道路,他永远无法追随任何一个人走上他们的路。“无论是卡夫卡、乔伊斯,还是海明威、福克纳,我写成谁的样子都是要‘死掉’的。在漫长又曲折的学习写作的过程中,这一点清晰对我非常重要。我总想在变化的文本中打开自己的可能性。”
也因此,每次写完一本书,赵松的满足感都非常短暂。他陷入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状态,因为这一本书的方法在下一本用不上了,他不知道下一本书能不能出来,怎么出来。“我经常有这种短暂的虚无感,像走钢丝的人一样,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停在一个点就掉下去了。一个作家的死亡有两次,一次是生命衰竭时,一次是写不出新的东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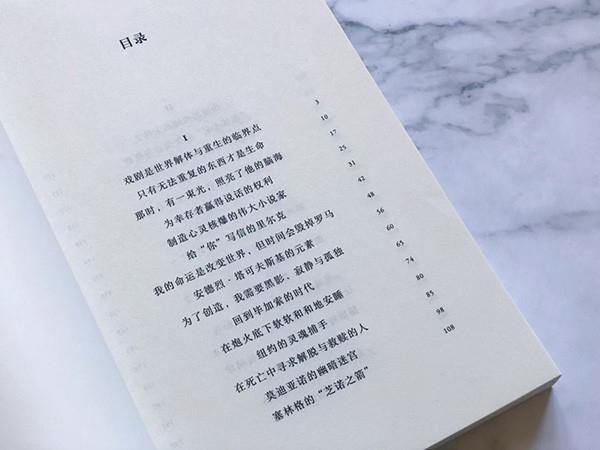
在最新出版的阅读随笔集《灵魂应是可以随时飞起的鸟》中,赵松也对阿兰·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40余位世界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品读。
小白回溯了法国“新小说”的历史,提及当时法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新小说”那派人“抱着团”,在写法和观念上都颠覆了从前的小说传统。“法国‘新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开拓。不仅开拓了小说的写法,更开拓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张定浩更强调这一流派对中国当代写作的影响。“法国‘新小说’强调对作者孤独主体意识和感受能力的挖掘,这个观念在当时现实主义占主流的背景下极具煽动性或破坏性,而同时,又似乎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受到当代很多年轻写作者的追随。我们知道每个文学青年最熟悉的就是自我,这种强调自我感受的写作相对来讲是容易上手的。但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作品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很多年轻写作者选择新小说的方式来写作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理解他人。”
在他看来,法国“新小说”这一流派并非一种新的文坛登龙术和终南捷径。“赵松之所以是我眼中真正得到法国‘新小说’精神的人,就在于他没有被前辈的具体的小说观念或模式所束缚,他要写出的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新。”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