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生”傅高义去世,生前致力于帮助西方了解中国

《朝日新闻》消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本文发表于2019年11月,南方人物周刊就中日关系问题在香港专访了傅高义
“我开始去日本是1958年,呆了两年。以后我每年都有一次访问日本,80年代以后,我每年去看中国。为什么我要写这本新书?是因为中国人觉得,与日本的关系要看历史,但日本人看历史看得不够。为解决两个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多了解历史”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江采欣
全文约5030,细读大约需要12分钟

图 / 本刊记者 方迎忠
傅高义(英文名Ezra Feivel Vogel,1930——2020)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作家,精通中文和日文,著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等作品。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国中古历史,长期从事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历史的研究,在哈佛被称为“中国先生”。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花十年时间写出名作《邓小平时代》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向89岁的傅高义伸手搀扶时,傅高义没有推开她。甘琦感叹:傅先生研究中国、日本这么多年,终于接受了中国的“敬老”文化。往常她做同样的举动,会被别的美国教授推开——“你觉得我很老吗?”
30岁那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傅高义到哈佛大学访友,东亚研究中心的裴泽教授告诉他,哈佛大学最近获得一笔基金,想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可以留在哈佛教书。正是这一机缘,让他开始研究中国。
十年后,傅高义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年)》,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这本书由他在香港翻阅1949年到1968年《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资料,并与大陆朋友深度访谈后完成。1973年,傅高义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1987年,受广东政府邀请,傅高义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广东之行。两年后,他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
傅高义对日本的研究几乎与中国研究同时进行。1958年,傅高义关注到战败后的日本,对日本如何应对战后危机、重建经济繁荣和新的社会秩序产生兴趣。他去日本学了一年日语,做了一年田野调查。回美国后,出版了《日本新中产阶级》,被称为“有关现代日本最前沿美国观察家之一”。
1979年,49岁的傅高义出版了改变他人生的一本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讲述了他眼中日本诸多社会模式的成功范例,对当时发展减缓的美国有借鉴意义。这本书在日本销售七十多万册。此前,他是哈佛大学一位无名学者,这部著作出版后,走在日本街头会有记者过来采访。
至此,傅高义成为当时美国为数不多同时熟谙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能从两国研究中洞察亚洲与全球局势的学者。2019年,他推出新书《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详述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彼此之间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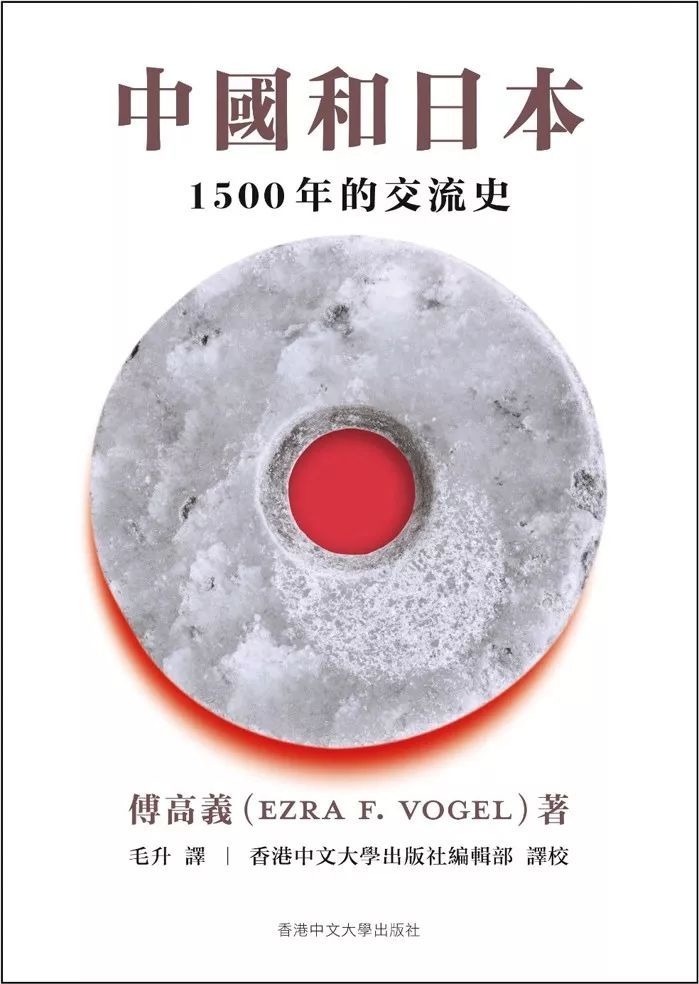
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
1930年,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英文全名Ezra Feivel Vogel。决定以研究中国为终生事业后,他取了中文名“傅高义”——德语里“Vogel”发音像中文的“fugao”,加上他英文名首字母E。E者,义也。“义”在中文里属于很高的道德水准,也恰恰是他心中伦理的至高境界。1973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
从1958年开始,傅高义每年去一次日本。1980年在广州常驻,每年到一次中国。他见证了战后日本的发展与泡沫经济的破灭,亲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猛发展。
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浸润,傅高义对迥异于西方的东亚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他享受到了“人情”带来的利好,广交友、善结缘是他每次访谈都会提到的。深度访谈是他最常用的社会研究方式。在中国,傅高义有很多长期交往的老朋友,他们多是身居要职的政府人员或学者,当他们因公职身份不便说话时,傅高义会以朋友聊天的方式推进他的工作,他认为,“朋友之间谈话,彼此会更加坦诚。”哈佛大学教授与费正清研究学院前院长的身份让傅高义得以接触到他希望接触的许多人,而一次次深度访谈则为他积累了足够的人脉。随着众多朋友不断成长、在各自领域担任要职,傅高义拥有了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人脉资源。
2012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证实了傅高义积累近五十年的人脉资源的分量:他的访谈对象包括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身边工作过的高级干部和深度参与时代进程的各界人物,还有与邓小平有过接触、对邓小平有特别认知的国外政界、学界人士。这本书让傅高义在中国享有盛名。
傅高义彬彬有礼、面带笑容,这让他深陷的眼窝、突出的鼻翼、占脸长三分之一的耳朵都变得柔和。采访中,他对目前的国际局势有点感叹,“现在全世界关系太复杂了,不能分开。要相互理解,相互合作,避免正面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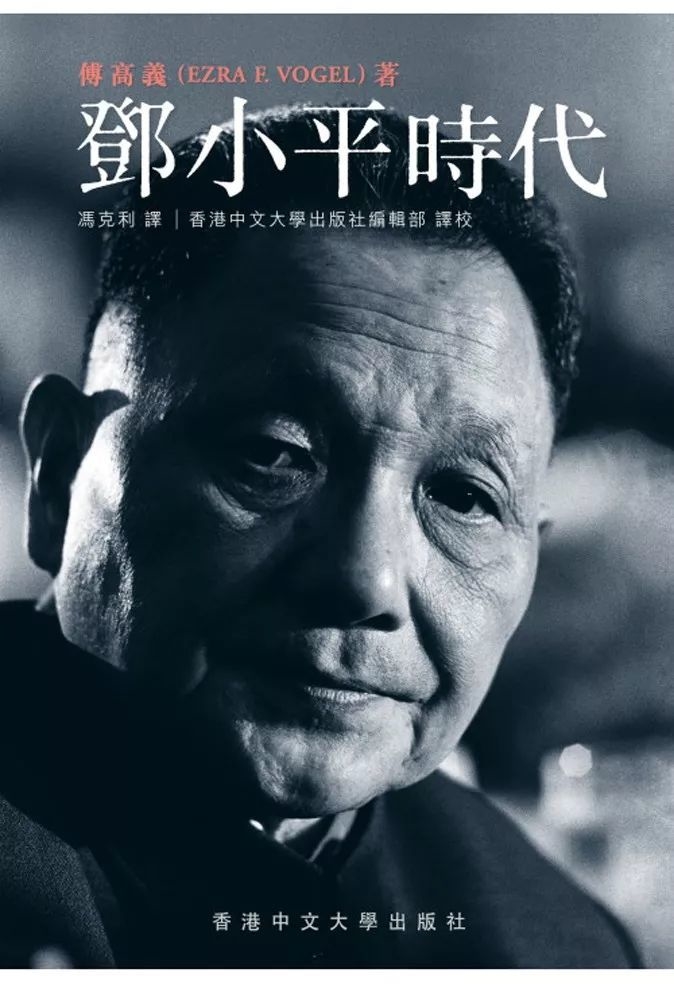
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
尽可能准确地了解两方面的看法
人物周刊:您现在访问中国和日本的频率是怎样的?
傅高义:我开始去日本是1958年,呆了两年。以后我每年都有一次访问日本,80年代以后,我每年去看中国。为什么我要写这本新书?是因为中国人觉得,与日本的关系要看历史,但日本人看历史看得不够。为解决两个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多了解历史。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在您之前中国和日本两国各自对两国关系的研究?
傅高义:日本人做中国研究,记录详细,哪一年某某人做什么事,这类详细的事情,他们特别成功。中国呢,解放以后,中国政府当时对日本有什么看法会影响中国学者对日本的研究。虽然他们是看日文的,看得比我多,但是他们的分析带有政治色彩。日本没有统一的思想和政治,各种各样的内容,右派、左派、中间派,文学的、学者的看法都有。
人物周刊:您从中国的角度研究中日关系,实际上是在研究中国。
傅高义:对。我想知道中国人怎么看日本。应该了解:为什么中国人是这样看?是依靠什么经验,大家有了这么一个结论?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都要用这样的研究方法,那是我的目标,尽可能准确地了解两方面的看法。
人物周刊:您这本新书最后一章写1992年到现在的中日关系,里面有很多信息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可能是中国这边的,但日本那边怎么看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
傅高义:我认为一个旁观者应该多了解,应该多学,应该尽可能正确地了解92年以后中国人怎么看,日本人怎么看。爱国主义运动以后,中国人写日本,是按照爱国主义来的,比如90年代后期去中国,我在宾馆看电视,会看到抗战影片。90年代很多中国朋友对日本的态度,我认为也是受了这些老电影的影响。
人物周刊:日本民众如何看中国?
傅高义:不一定是客观的,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也有自己的角度。比方说2005年,当时有中国人去砸日本的企业。这些日本的记者会看见,日本的电视也可以看到新闻,对中国的偏见也可能出现。日本人会感觉,中国人这么恨日本。你可以说那是客观的看法,也可以说是偏见。普通的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比较复杂,不能那么简单地按照电视上看到的情况判断,不全面。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的思想,但是不能说他们没有偏见。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旁观者,您看到了哪些中国和日本学者在两国关系研究中没有被重视的部分?
傅高义:两个国家的学者我都认识,都是朋友。我认为第一流的学者都比较客观,他在文章里不一定能谈到自己真实的想法。日本人想什么就写什么,把详细的事情写得非常好。但是他们的分析,我认为有的部分可以考虑不一样的结论,所以我看他们怎么说、怎么研究,尽可能了解他们的看法。
人物周刊:您觉得最大的冲突在哪里?
傅高义:中国方面,我认为二战的影响比较大。对于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的援助,中国人写得不多,有的中国人了解,也写,但是我发现较少谈到日本对中国发展的贡献。日本方面,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人的批评感到愤怒。他们看到的90年代以后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是太恨了。这不一定是客观事实。
人物周刊:您在书中提到中国和日本有三个比较关键的时间段,第一个是日本学习中国,那是古代的时候,后面两个时间段中国学日本,近代和现代。在您看来,日本学习中国传统的第一个时间段,他们的学习到现在有哪些留存?
傅高义:很多,比如文字,他们的文字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也有相同的。现在中国人去日本看铺子的招牌,他们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不一定完全了解。还有佛教,历史上,佛教对两国的影响非常大。两个国家的和尚比较容易谈得来。还有文学,杜甫这一类的。日本喜欢中国古代文学。鲁迅、茅盾在日本待过、学过,所以鲁迅也受到日本的影响。还有儒学。虽然儒学不断改变,但是儒学基本的思想,我想两个国家也类似。从西方来看,儒学的影响还存在。特别是1930年,在日本的一流高中里,儒学的思想非常多。希腊罗马的影响在全欧洲、在美国都有,各个方面都是受了希腊罗马的影响,所以我想同样,日本也受了中国的影响。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帮助在哪里?
傅高义:一直到二战时期,非常多的中国人去日本学习,那时候学医学、学工业、学文学、学法律都是学西方思想,周恩来也在日本学习过。我想那个时代的各个方面都不是很系统,因为那个时代不是中国统一的思想、不是政府派人去学习,是家庭和个人想去,所以很复杂,什么都要学。1905年科举废除了,年轻的中国人想做什么?那个时代很多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他们工业化、思想意识都要学,所以他们受的影响比较大。
人物周刊:您认为这几年中日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什么新的变化?
傅高义:2014年以后,两国关系比较缓和。最近五年更稳定,不能说完全好,但是我认为危险性减少了。日本有个说法,“政冷经热”。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右)与父亲福田赳夫在家中下棋。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在任期间,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008年,福田康夫在任期间,中日两国又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世界关系太复杂,要相互理解,相互合作
人物周刊:我看到您说以前通过买中国报纸,比如《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来了解中国,现在您通过什么渠道了解中国?
傅高义:有很多办法看中国的一些材料。我每天看美国报纸。同时我有这么多朋友,每个礼拜见几个,各种各样的中国学者,也有在政府工作的。很多都是老朋友,跟老朋友谈话,他们很直爽。我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来了解情况,比较重要。今天早餐是跟我的两个哈佛学生一起吃的。他们跟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他们是美国商人,跟中国的接触很多,所以我通过他们的看法来学习。
人物周刊:您最初开始中国研究,是因为裴泽教授的建议。是什么事情真正激发了您对中国的兴趣?
傅高义:我研究日本不是因为我喜欢日本,是为了多了解,我的目标是做研究。后来我开始研究中国,我想我的工作是了解。
人物周刊:您研究中国这么多年,哪些人改变了您对中国的认知?
傅高义:我就是想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中国的情况是有改变的。80年代很穷,现在中国已经很有钱,势力很大,在非洲、南美搞建设,在全世界的影响很大,实际情况改变了。所以我想了解中国,应该看现在中国怎么样。在90年代,因为经过改革开放,中国人很多认识改变了,我觉得不是他们自动改变了认知,而是中国的确有改变。一些美国人觉得中国的势力很大,是对外国的威胁,是偷美国的技术。你想中国这么大,要是偷美国的现代化技术,中国公司的利润增加了,美国怎么办?所以我认为在华盛顿,现在很多美国商人对中国没有好感,不仅仅几个,而是很多商人都这么看,他们影响力很大。
全世界的问题太复杂,不能不跟中国合作。为了避免冲突,应该积极合作。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关系太复杂了。不能分开,要相互理解,相互合作,避免正面冲突。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学者的责任。
人物周刊:您有没有喜欢的中国作家?
傅高义:我特别喜欢茅盾,我认为茅盾的确对社会非常有研究,当时为了做研究,看了一些摘要。我想知道中国人的看法,比方说茅盾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老舍关于旧北京的看法也很不错。还有古代人写的《红楼梦》,我都看了一些。因为最开始我不能去中国内地,很多研究是在香港,找内地的人谈话。那时另外一个研究方法是看内地的小说。
人物周刊:您喜欢中国的哪个城市?
傅高义:不是喜欢不喜欢,是能不能做好研究。80年代,我认为做研究对我来说非常方便的是广东,改革开放从广东开始。后来研究邓小平,我认为在北京是最方便、最好的。
人物周刊:距《邓小平时代》出版已经过去7年,现在再去北京,您感受到哪些新的变化?
傅高义:每年来的变化都太多。我刚开始到中国是1973年,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很快。你说变化是什么意思?是建设的变化、现代化的变化,还是人的思想的变化?人的思想很难了解。但建设方面的变化,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每年都变化太大了。新房子、新建设,现在也包括手机,手机的用法也有很大的发展。1973年,当时中国人都怕跟外国人见面,谈得也不多。我大概是1980年在广州待了两个月,当时他们对外国人还有点怕。虽然改革开放是从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了,但是当时看不见变化,因为没有新房子,没有新路,旧的东西还在。变化要到80年代后期才可以看得出,有了新房子,本来乱七八糟的变成了干净的。我当时在广东,有的地方是现代化,但是很多地方没有改变,改革开放是一步一步改变的。但是跟别的国家比较的话,我认为80年代后期开始可以看出每年的变化非常多。2001年,我在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每天骑自行车绕天安门一圈,现在不能这样了,骑自行车没地方了。1980年我在广东也有自行车,在广州什么地方都能骑自行车去,那时候机动车不多。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对东亚社会和东亚文化一直保有热情的原因是什么?
傅高义:写这本书之前我的目标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包括《邓小平时代》。这本书我认为我的目标是(帮助中国和日本彼此)了解。
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
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
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