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伟】日本NHK纪录片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形象:以《彝族终身大事》为例

【摘要】《彝族终身大事》作为一部表现彝族社会变迁的纪录片,在NHK拍摄的少数民族有关纪录片中极具代表性。纪录片以服饰、建筑等作为民族符号的同时展现不同的民族习俗,从而建构起了异于现代社会的彝族社会。本文进一步分析纪录片中对彝族社会地域与女性地位的表现,发展其均是为了顺应纪录片的情节发展而把彝族社会置于偏远、经济落后、女性地位低等与现代社会相对的位置。
【关键词】NHK纪录片;彝族;形象建构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金项目“NHK纪录片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形象建构”,项目编号:20巧zyxs69

从1953年NHK电视正式开播至今,大量涉华纪录片的播出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持续关注。从这些纪录片来看,NHK把目光投向中国少数民族始于1980年中日合作拍摄的纪录片《丝绸之路》。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NHK纪录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关注达到了一个顶峰阶段:《西藏:去世界之行》揭开了西藏地区的神秘面纱,《秘境云南》与《秘境西藏》相继深入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此外还有《大黄河》《秘境:兴安岭之行》等系列纪录片中均出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身影。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较为动荡,但在此期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并未出现明显恶化,以上一系列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的纪录片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8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也反复被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所冲刷,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在此过程中产生。国内纪录片开始关注少数民族社会变迁与社会情感,表现其生产与生活状态,绘制现代化的中国表情。随着日本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与全球性资讯爆炸,NHK纪录片对中国少数民族表现方式已不再满足于单纯自然风光展示与民族文化介绍,与这一时期中国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类似,NHK也逐渐开始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社会问题。
《彝族终身大事》是NHK与日本铁木真电视公司合作拍摄的纪录片。纪录片讲述了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的彝族女子选择婚姻的故事,以主人公选择时面对的矛盾来表现彝族社会变迁。该主题在NHK近十年拍摄的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纪录片中极具代表性。
一、纪录片中的民族建构
纪录片把彝族社会与现代社会塑造成为两个不同的社会,矛盾在此基础上得以形成。而彝族社会的建构基于与现代社会的差异,纪录片通过彝族特有的服饰、建筑等物品与民族习俗等建构起一个异域社会。
(一)民族符号:服饰与建筑
彝族服饰区别于现代服饰,以这种异质性为基础,服饰成为纪录片中的彝族符号,在纪录片中强调彝族的民族性。纪录片的第一个场景就是主人公穿着彝族传统服装放羊,旁白介绍安妮是“少数民族彝族的女子”,受众由服装获得对彝族的第一印象,且这种印象延伸至安妮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在安妮家日常生活的画面之中,安妮、母亲、小姨均穿着彝族传统服饰,他们的彝族人身份由此得到强调。而纪录片中,当安妮去家以外的小镇街头与丽江时,她的穿着又变为了与周围人相同的现代服装。彝族传统服饰在这一层面上也协助了彝族区域社会的划分—穿彝族服饰的时候强调处于彝族社会以内,穿现代服装的时候暗示已脱离传统彝族社会。
彝族建筑也起到了与彝族服饰相似的作用。摄像机首先从二楼往下俯拍,展现出安妮家的整体布局,旁白说道:“这是两层楼的木造房子,围绕着院子而建造。”接着镜头切换到院子侧面的房屋,房屋木质结构清晰可见。最后镜头切换,给了挂在屋檐下的牛角一个特写。旁白与画面对房屋木质结构的强调与最后牛角的特写均是在突出异质性,强调彝族建筑与现代社会建筑的差异,从而把安妮生活的彝族社会与现代社会建构为两个区别开来的社会。
(二)以习俗差异建构民族
物质性的服饰、建筑之外,纪录片对于彝族社会的建构进一步基于其对民族风俗的表现。民族风俗习惯与物质性的服饰建筑不同,难以通过画面直接表现,纪录片中的风俗习惯多是由旁白或片中人物进行讲解。
日常生活场景中,主人公安妮起床后为火塘加柴。火塘在彝族具有的特殊意义并不能通过加柴的动作表现,旁白添加了解释:“对彝族来说,炉火熄灭意味着家族灭绝,从房子盖好的那天起,这簇炉火便一直燃烧至今日。”安妮与小姨中午外出采集落叶时,旁白说道:“彝族一天吃两餐,他们不吃午餐。”安妮描述她理想中的婚礼后解释道:“因为我们彝族崇拜自然教,很喜欢跟大地在一起的。”彝族群体以外的人对于风俗习惯的理解有限,所以解释成为必要,但同时这种解释也把彝族群体内的人和受众区分开来。在这些风俗习惯的解释中,‘彝族'每次都会被强调,从而突出风俗习惯是彝族所特有,以此来划分彝族群体的边界。
二、彝族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
在建构彝族社会的基础上,纪录片进一步以画面与旁白营造出彝族社会的概况,从而支撑起片子的故事情节。它将主人公安妮回家的生活置放到消极的语境之中,同时将其与女性在非彝族社会的生活对立起来,以这种矛盾作为纪录片故事性的基础。
(一)纪录片中的彝族社会边界及其意义
围绕主人公安妮的生活,纪录片的叙述中共出现5个不同地点,以每个地点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属性为基础,通过纪录片中的旁白描述及画面呈现,一幅从边缘地域到中央的地图就此被绘制。
纪录片在开始的前两分钟就介绍了安妮家的地理位置。画面首先给出一个群山连绵的大远景,随着镜头推进,画面聚焦到整个大远景中的唯一一栋房子。旁白说道:“宁菠彝族自治县,位于中国云南省境内,地形多山而崎岖,海拔超过两千米高,安妮的家位于小丘山顶上。”画面以推镜头方式表现安妮家周围环境与具体位置,旁白刻意描述地形“多山崎岖”与海拔高度这两个画面无法完全表现的特点,从而使安妮家位置的偏远与交通的不便成为其在纪录片中的第一属性。
纪录片15分钟时,主人公安妮去了弟弟上学与姐姐居住的小镇。画面对于小镇的表现手法与安妮家相似,但这种相似的表现手法却传达出了相对的信息。大远景中的小镇建筑并不高大,但其密集程度却与安妮家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小镇与安妮家的不同还表现在镜头中车来人往的小镇街头,人口的密集程度进一步说明了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程度远高于安妮家的地方。相似的表现方式使碍安妮家与小镇发展程度的对比更为明显。旁白这样解释这个小镇:“离安妮的村子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安妮的弟弟在这里上小学。”表面上旁白是在通过安妮家与小镇的距离来说明小镇的位置,而实际上这段距离衡量的是安妮家与小镇的经济发展程度的距离。于是小镇与安妮家几乎被放到了对立面,小镇是现代的代表,而安妮家仍处于传统之中。小镇同时也在纪录片中成为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线,小镇距离之外的地点均被划到现代的范围之内。
纪录片35分钟时,安妮回到自己曾经上舞蹈学校的丽江市。旁白把安妮从家到丽江市的旅程称为“短期旅程”。这说明丽江在小镇的距离之外,但又并非与安妮家距离遥远。而在纪录片最开始介绍安妮的经历时,旁白说道:“安妮在14岁那年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和“城市”两个词成为形容丽江的关键词,“外面的世界”是相对于安妮家的描述,“城市”是纪录片与社会对丽江的定义。安妮家的社会圈子范围以丽江为分界线结束。
在丽江与同学相聚时,两人提及从前的同学们现在一半在昆明一半在丽江。昆明与安妮家之间的距离比起丽江更为遥远,同时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发展程度也更为超前。纪录片中并未有对昆明更多描述,但因其省会城市的属性,地名出现的同时它也就成为了与北京相似的刻度,标示着程度与距离。
安妮家地域偏远的属性在纪录片的一开始就被确立,一把地区发展状况的度量尺随之出现。安妮家与北京成为度量尺的两端。离安妮家越近,地域越偏远,发展越落后;离北京越近,地域越中心化,发展越超前。彝族社会圈子被划分到城市以外,局限于乡镇。安妮家更是处于传统的村落当中,被排除到现代社会之外。主人公安妮从自己家到丽江再到北京最后回到自己家的过程就被塑造为一个从偏远地区走向中心城市最后又回到偏远地区的过程。纪录片中安妮回家的选择也就被赋予了消极意义。在此基础上,纪录片中矛盾与冲突的叙事才得以展开。
(二)彝族社会女性地位及其意义
纪录片在最开始的旁白中介绍主人公安妮为“少数民族彝族的女子”,表明了安妮少数民族与女性的双重身份。少数民族在纪录片中通过其特殊生活风俗习惯与地理位置等得到表述,而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展示中,主人公安妮的女性身份得到了更多的书写。这些书写多强调了彝族女性在群体中或家庭中的社会地位。
在对安妮家地貌的简要介绍之后,纪录片进人了对于安妮家庭日常生活的叙述。安妮家族中女性与男性有着不同的作息时间,旁白刻意在此作出强调:“早上八点,安妮的一天揭开序幕。”在安妮与母亲把早餐准备好后,画面中安妮的父亲出现,旁白说道:“早上九点,全家人等父亲阿宜伦起床后一起吃早餐。”八点与九点之间一小时作息时间的差异从钡叮面表明了安妮的家庭之中父亲的地位:父亲不用早起做家务与准备早饭,家务是女人的工作。
纪录片进人情节高潮在表现安妮对于婚姻的思考时,旁白明确说明了彝族女性的家庭地位:“在安妮住的村落里,大家还是过着传统的生活,村里几乎完全自给自足,这里的女人不仅要做家事,还要照顾耕田、牲口,安妮到北京去,因为她想脱离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她对年迈母亲阿嘉的担心,又让她回到这个村子。结婚后,必须年复一年重复这种生活。”通过对女性家庭地位的描述,纪录片营造出了另一层对立意义。在传统社会的女性家庭地位描述中存在一个与现代社会的隐性对比:观众来自现代社会,因此了解在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女性在安妮家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与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也就形成了对立。
婚姻仪式开始的当天清晨,新娘在进人男方家庭的院子前需在门外“接受日光的洗礼”,这时候的旁白加人解释:“传统上,新娘的父母不能参加婚礼。”在婚礼宴席上,以祝福的歌声为声音背景,画面给了新娘一个脸部特写,这时候新娘的脸上没有笑容,旁白特意强调:“庆祝宴席已经开始,在座的只有两方的男性亲属,新娘没有座位,她只是安静地站在屋内一角。”宴席结束后,新娘送走自己的亲人,画面在此呈现出新娘不停流泪的面部特写,旁白说道:“宴席持续一整晚,次日清晨,新娘终于可以自由活动。她与亲人告别。”以画面与旁白为主导,纪录片强调了这场婚姻仪式是以男方家庭为中心,而新娘(女方)以及女性都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从而说明了在主人公安妮生活的彝族社会,女性低于男性的社会地位。这时候再回到纪录片故事的主线时,主人公安妮从女性与男性社会地位平等的“现代社会”回到女性社会地位低于男性的彝族传统社会再次被涂抹上消极的色彩。
三、文化变迁的叙事方式
彝族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位置推进了纪录片叙事。主人公安妮去丽江与北京后,受那里生活的影响而改变了自己的婚姻观。在涉及文化变迁尤为常见的是将差异性或空间性转化为时间性,即西方现代性/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被置换为父(母)一代与子(女)一代的对撞。纪录片叙事正是通过表现在婚姻选择上安妮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来反映这种文化变迁。
主人公安妮接受了外来文化,在家庭与自我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纪录片以婚姻为载体来表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彝族的传统观念与现代婚姻制度;二是主人公安妮的婚姻选择与父母之命,这也是影片的主题。
片中表现了安妮父母与安妮两代人不同的婚姻观。安妮父母代表了彝族传统,去城市生活过的安妮在彝族社会中代表了现代性。安妮的母亲在影片中展现出的是一个为家庭辛勤付出的形象,甚至为了家庭香火的延续,愿意结束自己与丈夫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是一个奉献者。而安妮父母话语间也传达出了对婚姻的观念:重视子嗣、父母包办婚姻、结婚须趁早(纪录片中解释彝族女性结婚年龄是17岁)。但安妮因为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已不愿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安妮对于父母安排婚姻的拒绝,既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更是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
四、结语
通过以上方式,纪录片把彝族社会置于现代社会的对立面,将彝族传统社会描述为地域偏远、经济落后、女性地位低的一个具有消极意义的异质社会,从而突出其冲突性与故事性。大量旁白的使用一方面加深了受众对片中情节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也使得纪录片充斥着制作人员的主观态度,减少对拍摄对象文化的直接理解。作为一部以电视观众为主要受众的纪录片,冲突性与故事性成为《彝族终身大事》的侧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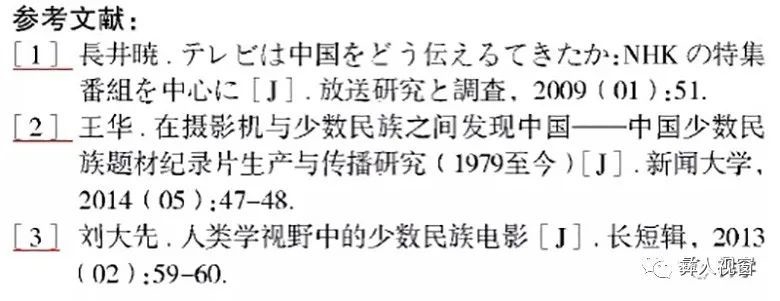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
(文字来源:彝学公众号,主编:巫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