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人间词话》:当文学遇上哲学,才是最唯美的人生三种境界
 2020-06-02
2020-06-02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最早听闻《人间词话》便是从这三句话开始的。那时人还年幼,只道词是词,诗是诗,美就可以了,怎还能上升到境界的程度。可如今再次偶遇这三句词,却也能够品味其中的唯美与孤寂。

王国维出生寒门,母亲早逝,父亲一人既当爹又当妈地将他抚养长大,一心想着他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奈何偏偏他厌恶八股文考试,止步秀才,便不再参加科举。
1898年,王国维独自来到上海,在同乡的引荐下进入《时务报》担任校对兼门房。
那时,他同事的薪水是二十块钱,而他只有十二块,投诉无效,他又无处可去,只能学着忍让和苟且。他在自己的扇子上写下:“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以此明志。
后来,他遇到了自己的伯乐——罗振玉,命运至此发生改变。罗振玉将他请到东文学社,委任他为学社“庶务”,并且每月发给他三十元工资。
正是在那段时期,王国维接触到了康德和叔本华,并满腔热情地研究起西方哲学来。王国维将这段时光定义为“独学时代”。
后来,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又跟随罗振玉前往北京,《人间词话》便是诞生在那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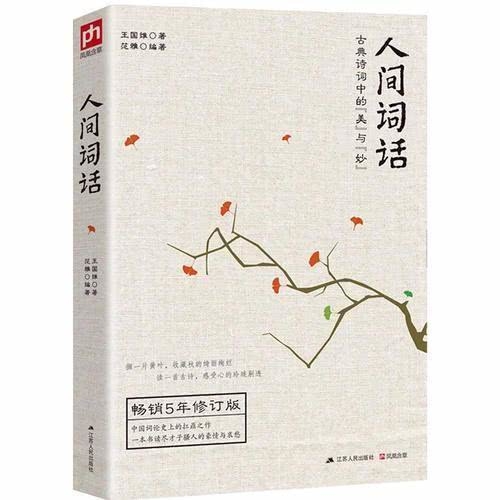
从古至今,文学批评有“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却使文学与哲学在另一种高度相融。
或许,这是因为王国维追求的不仅仅只是一般的学问,而是一种真理,一种信仰。正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碑铭》中所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优劣。王国维对于境界的定义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出自出自北宋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整首词都透露出一种悲凉寂寥,这也正符合了王国维“独学时代”的特征。
叫我说,这句话本身的起点已经是高了。
少年人常感迷茫,惆怅,些许小的烦恼立刻能掀起轩然大波。于是,诸多对于人生的困惑便会从心而生,你想要寻找答案,只能不断攀爬,排除干扰,一路向上,直到“望尽天涯路”,放能看清未来的方向。
于创作者而言,这是最初的酝酿时期,需要大量的准备和积累,这个过程痛苦而漫长,但你只有坚定自己的目标,方能站在别人仰望的高度,厚积而薄发。
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句出自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比之第一境界,这句话中包含了苦涩之味。
找到目标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你需得矢志不渝地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前路漫漫,未有期,你或许会经历沙漠、雨林、荆棘,运气好的,能遇高人指点,顺水推舟,运气不好,你甚至难辨东西,被困其中。
你唯一有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虚幻的目标。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会让你憔悴不堪,你需要一层一层剥去欲望的外壳,忽略得失,不忘初心,做到“终不悔”,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这也是创作的第二个过程:反复推敲、琢磨、修改。这需要强大的自律,战胜恐惧和惰性,让创作成为一种自然属性,才能达到飞跃的进步。
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这里的“那人”自然不是指佳人,而是真理。
经历了大风大浪,见惯了风风雨雨,最终便会明白,一切皆是身外物,无常才是永恒的有常。正如所有的英雄故事中,英雄们踏上各自的征程,无论在外经历何种磨难,最终都将回到起点,回归自己的内心,因为答案就在你的心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写道: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自古以来,诗词最重要的便是寄情于景,哪怕是写小说时,大部分的作者也多多少少会将自己代入其中,以我的主观感受看世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而「无我之境」乃最高境界,它是要将作者摘出,不带有任何个人情感地去描写一段情景,就须得有足够多的积累,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辛,才能做到同「自然」一样,无喜无悲,却创造出了常人无法逾越之美。
遗憾的是,先生自己未能达到此种境界。他的时间永远地停留在了1927年6月2日上午。
那天上午,他在清华研究院交代完工作,独自前往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鱼藻轩,点燃一卷烟,对着湖面沉思发呆。约莫过了两个小时,他选择了投湖自沉。当人们将他的尸体捞上来时,在其口袋发现一纸遗书,短短十六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与他所崇拜的屈原,所钻研的《红楼梦》是否有关,已无从考证,然而必与他所读之书无可分割,毕竟,他也是位「以血书文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