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意识获得永生?你准备好成为电子人了吗


我曾在一场婚宴上调查了几个朋友关于永生的看法。假如你明天就能把意识上传到电脑,从此以人机结合体的形式永远生存,你会乐意吗?我向一对来自旧金山的高学历夫妇提了这个问题。
丈夫今年 42 岁,拥有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对我的提问毫不犹豫地答了“会”。他说自己眼下从事的研究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内结出果实,他想亲眼见证那些果实是什么样子,“另外,我也想看看一万年后的世界。”他的妻子 39 岁,拥有艺术史的博士学位,她的选择同样坚决。“绝对不要,”她说,“死是生的一部分。我就想知道死亡是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这位妻子的回答会不会使丈夫担心,但是出于礼貌,我没有追问下去。不过这个问题可不仅仅是餐会上的闲谈。如果相信一些未来学家的理论,那我们迟早需要应付这类事情,因为照他们的说法,我们正在朝着一个后生物学世界进发。在这个世界里,死亡已经成为过去式,或至少是一个我们可以左右的现象了。

奇点临近
对这个超越性的未来想象得最充分的是雷·库兹韦尔 (Ray Kurzweil)。他在 2005 年的畅销书 《奇点临近》 (The Sigularity Is Near)中预言,人工智能很快就会“囊括所有的人类知识和技能”。一旦有了纳米尺度的脑扫描技术,我们就能“逐步将自己的智力、性格和技能转移到非生物的载体上去。”与此同时,数以十亿计的纳米机器人将在我们体内“摧毁病原体、纠正 DNA 差错、消灭毒素并执行许多其他任务,改善我们的健康。这样我们就能够持续生存,永不衰老。”
这些纳米机器人还会“在神经系统内部创造出虚拟现实”。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生活在虚拟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创造的质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你很难把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区分开来。
库兹韦尔所谓的奇点,是指非生物智力大大超越所有人类的智力,从而促成 “人类才能的颠覆性剧变”。根据遗传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再参照技术进步的指数式速度,他将这个奇点出现的时间定在了 2045 年。到今天,仍有几位奇点论者在坚持这个日期,人工智能中有一个称为“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领域发展迅速,更是坚定了他们的信心。
然而多数科学家认为,人类变成电子人不可能很快就会实现。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承现峻教授(Sebastian Seung)主张,上传意识也许永远无法实现。人脑由1000亿个神经元组成,它们彼此通过突触连接,这些连接的总和称为“连接组”(connectome),有的神经科学家认为,连接组是解开我们身份之谜的关键。即使我们的技术真能以库兹韦尔的标准进展,需要描绘和上传的连接数目也显得太多了。况且连接组也许只是开端:除了突触,神经元还能以其他方式互动,这类“突触外相互作用”(extrasynaptic interactions)也可能是人脑功能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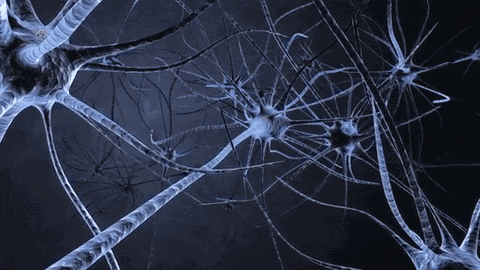
如果真的如此,就像承现峻在 2012 年的著作《连接组:造就独一无二的你》(Connectome: How the Brain’s Wiring Makes Us Who We Are)中认为的那样,要上传的就不仅是每一个连接或每一个神经元了,还要包含每一个原子。承教授写道,这项工作需要的运算能力“是绝对无法达到的,除非经过了遥远的天文时代,我们还有后代在从事相关研究。”
不过,无论我们成为电子人的可能是如何遥不可及,都会产生一些重要的伦理问题。眼下已经有严肃的哲学家在认真辩论这些问题了。即使未来的技术不能完全达到库兹韦尔的要求,在身心两方面的强化也能使我们更加接近目标,到那时,我们就要问问自己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了。
哲学家戴维·查默斯(David Chalmers)是纽约大学心智、大脑和意识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nd, Brain and Consciousness)的主任,曾在文章中讨论上传意识、保存自我的最佳方法。我问他是否相信自己有机会长生不死,50 岁的查默斯答说他不信,但他也说过:“再过一个世纪左右,这绝对会成为一种切实的可能。”
罗纳德·桑德勒(Ronald Sandler)是一名环境伦理学家,也是美国东北大学哲学和宗教系的主任。在他看来,谈论我们是否会变成电子人“会让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不过,思考长远的未来,也会使人们对短期的情况多一些了解。”
当然,即便只有一线希望能在死亡和作为电子人永生之间选择,活着的人也最好从现在就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选择。除了可行性,我们还有必要考虑一些更加根本的问题:永生真的好吗?如果我的大脑和意识都上传到了一个电子人体内,我又会变成谁呢?我对家人和朋友还会有爱吗?他们还会爱我吗?说到底,我还能算一个曾经的人吗?
超人类的道德
哲学家常常思考人与人如何相处的问题。在一个后人类的世界,我们还会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吗?桑德勒在几年前与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讲到过这个问题,题目是《超人类主义、人的尊严以及道德地位》(Transhumanism, Human Dignity, and Moral Status)。他在文中说,“强化”后的新人对常人还是有道德义务的,“即使他们在某个方面得到了加强,还是必须关心常人”。我不认为他这么说有什么错,只是,我不认为这样的假设会变成现实。
其他哲学家则主张“道德强化”(moral enhancement),也就是运用医学或生物医学的手段对我们的道德原则做一次升级。如果我们拥有了高超的智慧和强大的力量,就必须保证权力不落到邪恶博士的手里。哲学家朱利安·萨乌雷斯古(Julian Savulescu)和英格玛·佩尔松(Ingmar Persson)在不久前写道,我们的科学知识“已经可以触及直接影响人类动机的生物学或生理学基础。这表示或者用药物,或者通过基因选择、基因工程,或者用外部装置就能左右人脑、左右学习过程。利用这些技术,我们就能克服人在道德和心理上的缺陷,使它们不再危害人类。”

2016 年 5 月的一份《华盛顿邮报》上刊出了一篇专栏,题目是《科学即将使人更道德》(Soon We’ll Use Science to Make People More Moral),作者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是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的生物伦理学家兼副教务长。休斯在文中主张强化人类道德,但是也强调了只能通过自愿,不能强制执行这种措施。他写道:“有了科学的协助,我们就都能依靠技术找到自己的幸福和德行之路了。”现在,休斯还领导着一个激进的超人类主义智囊团——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Eth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地球。永生不仅会改变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会改变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永生的我们会对环境关注得更多还是更少?自然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桑德勒对我表示,“奇点”描述的是一个最终状态。要到达奇点,我们还要经历多次技术变革,而“技术能迅速有力地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当我们能够上传意识,并在虚拟和现实之间随意进出时,我们肯定已经对周围几乎所有事物都做出了幅度巨大的改动。“等到奇点来临的那一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肯定已经大不相同了,”桑德勒说。
虽然不愿承认,但是在目前有限的生命中,我们对自然界的各种系统还是非常依赖的。不过到了人类永生的未来世界,这样的依赖关系就会改变。如果不需要用肺呼吸,谁还会关心空气污染呢?如果不需要种植粮食,我们和土地的联系就会彻底断绝吧。
同样,在一个无法区分真实和虚拟的世界里,一个由数字模拟的自然或许能和户外的真实自然一样,给予我们同等的享受。人类和真实自然的关系将会变化,两者将不再有感官的实际接触。
这个变化将对人脑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便那时的人脑已经由硅片构成。研究显示,接触自然能够深刻地改变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和自然的联系,即使是在潜意识层面的联系,或许也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基本特质。
桑德勒指出,等到我们不再依赖自然,也失去了与自然亲切交流的能力时,“环境保护的基础就会由人的福祉转移到自然本身。”到那时,我们处理环境问题的手段就会超出今天的想象(比如能控制气候)。但那时的我们,还会觉得自然具有任何内在价值吗?如果还会,那么生态系统也许会变得更加健康;如果不会,那么也许其他物种和它们依赖的生态系统就要遭殃了。
人与环境的关系还和时间跨度有关。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眼下的这场物种灭绝危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以当前的人类寿命来说,它却是一件严重的大事。
桑德斯问,等到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对于人类以外的环境,我们提问和思考的角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时间的跨度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我们会因为寿命无穷而对环境更加关心?还是会因为获得了更开阔的眼界而不再介意环境?
“我们几乎不可能想象那时人类的心态,”桑德勒说,“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的视角将会变得和今天迥然不同。”
和专家讨论这些问题的时间一长,就会掉进一个奇幻的氛围中。我忽然发现,自己会一本正经和对方说着一些现在看来不着谱的话题。有一次休斯对我说道:“未来可能真会出现X战警式的基因疗法,人能从眼睛里射出激光,或者侵入别人的意识。”到那时,想要获得类似异能的人就必须通过特殊的训练,并且考取执照才行。

我问他:“你是想打个比方,还是真的相信这会实现?”
“关于人类会进化到什么境界,我们一般不会对新手说得太夸张,”他的回答颇为含蓄,“等你经过了四级振荡,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全人类都变成纳米机器人的未来了。”
忒修斯之船
等我们统统变成了纳米机器人,又会担忧些什么呢?毕竟忧虑可以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
永生会使忧虑消失吗?当我不再需要操心健康和账单的问题,也不会因为年老体衰而无法旅行、写作养活自己,那时的我还会是我吗?我会变成一个无欲无求的机器人吗?那样的我又会幻想些什么呢?我会不会因此而丧失抱负?如果能长生不老,那么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拖到下个世纪再动笔也不迟吧?
我还会是我吗?查默斯认为,“无论在哲学层面还是在实际层面上,这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从直觉上,我不太相信大脑在上传之后还会保持原来的我。即使我像查默斯建议的那样,一个一个神经元地上传,其间始终保持意识清醒,硅的比重由 1% 逐渐上升到 5%、10%,最后得到一枚 100% 的硅脑,肯定也会发生变化。这就好比是那艘忒修斯之船:将船上的木板一块块地替换成更加结实的新木板,到最后,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如果不是,它又是从哪块木板开始变成一艘新船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休斯说道,“寿命越长,经历的变化就越多,到最后,你会觉得长寿已经没有多少意义。现在的我,和 5 岁时候的我是同一个人吗?如果能再活 5000 年,那时候的我又和现在的我一样吗?在未来,我们将能够共享记忆,人类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将变得不再重要。”听起来可真没意思。
奇点论虽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却也流露出一点宿命论的意味:除了这样,别无他法。我们要么与机器融合,要么死去——或者更糟。
可如果我不想变成一个电子人呢?
库兹韦尔也许会说,那是因为我的生物学大脑太过局限,使我无法看见未来的真正魅力和潜力。未来的种种选择,包括随意更换身体、遨游虚拟现实、无穷的创意表达,以及移民到外太空生活,都会使我现在的肉身存在显得渺小而可笑。而且说到宿命,还有什么比肉身必有一死更宿命的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生而为人的感觉。我喜欢知道我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灵是用一样的材料做成的。甚至对于肉身的脆弱,我也有着一份眷恋。我喜欢自己温暖柔软的身体,不想变成动作电影里那些坚不可摧的超级机器人。我喜欢静脉中流淌着温暖的血液,不太想把它们换成纳米机器人。
有的伦理学家主张,人类的幸福感正是源于生命的短暂、脆弱和相互依赖。在一个人机结合的未来,我们又去哪里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呢?
库兹韦尔曾经写道:“在我看来,人的本质不在于我们的局限……而在于我们能够超越局限。”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死亡向来是这些局限当中最根本的一种,也许超越了死亡,反而会使我们的人性加深?
然而一旦超越了死亡,我觉得人性也将不再留存。死亡当然不是我们的特有的性质――一切生物都会死。但是我们对于死亡的觉察和理解,我们在短暂的一生中对于意义的追求,却是人类精神的一部分。
来源:环球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