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经典儿童文学对我们的情感养成究竟做了什么?


经典儿童文学《彼得·潘》内文插图
不同的时代中,
同一个情感关键词的内涵总是大相径庭。
说起经典儿童文学,你会想到哪些书?《长袜子皮皮》《丛林之书》还是《彼得·潘》?这些国际畅销书尽管出版年代久远,却在一代代孩子那里流传,为塑造儿童情绪起着独特而显著的功能,这种功能被称为“情感教育”。书中奇特且迷人的世界诱惑孩子们拿起书本,透过其中的故事获得对自身或其所处世界的知识,通过阅读别人的痛苦与喜悦而获得情绪体验。
在19世纪中叶,儿童情绪成为心理学中备受瞩目的话题,实际上自18世纪末,对儿童的情感研究便已萌生,19世纪至20世纪这类研究才日渐活跃。它们深受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发展的影响,深化了从前人们对儿童模仿学习的朴素经验,其研究的基础在于这样一种假设——儿童透过阅读模仿文本中人的情感反应模式,从而实现社会化。
如果我们好奇于童书的魔杖究竟对孩子们的情感养成和情绪反应模式(换句话说,也是对人们一生的情感发展)悄悄地发挥了什么作用,那么不妨与《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我们也曾在第12期童书新品联合书单中推荐过这本书)的作者们一道,展开对儿童文学和经典儿童教养手册的历史“追访”之旅,看看不同时代里的儿童是依照自己的才智来发展的主体,还是等着转变为成年人的教育对象。

《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德]乌特·弗雷弗特著,黄怀庆译,光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
01
情感书写给出的
是一个“何以成人”的衡量标尺
《情感学习》这本书由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研究中心主任、耶鲁大学德国史教授乌特·弗雷弗特主编,集合数位情感史研究专家共同撰写。
这些学者通过对60本左右已被经典化的国际畅销童书的考察发现,尽管随着时代的演进,其中的道德训诫被淡化,但重视“道德的作用”却仍然是童书不变的特色。人们越来越重视情绪,其在文本中的呈现也越来越多样化。
情感书写变得更加自由包容和幽微复杂,但背后指向的始终是人们对下一代寄托的价值强调和道德希望——我们不得不承认杰奎琳·罗丝在《彼得·潘——儿童幻想小说的不可能性》中说的“无论儿童文学多么具有颠覆性,毕竟仍受成人掌控”——“成长”意味着总要经历哪些情感困境和情绪波动?由于书中提出的信任、同情、爱、痛苦、恐惧、思乡乃至无聊等情感,总是归属于“儿童的成长”,即与儿童主体性建构息息相关,故而可以说,童书情感书写实际上给出的是一个“何以成人”的衡量标尺,是在协助定义“成长(所必备)的道德”。

《彼得·潘》,[英] 詹姆斯·马修·巴里 著,杨静远 译,浪花朵朵 | 大象出版社2020年1月版
不过,不同的时代中,同一个情感关键词的内涵总是大相径庭。以“信任”感的建立为例,深受强身派基督教影响的19世纪中期儿童文学作品最终往往把它归于上帝信仰。在这一时期的经典范本《汤姆求学记》里,主人公的精神榜样、病弱男孩阿瑟正是一个将自身的精神品格发展托付给上帝的男孩。
非常有趣的是,在当时这类流行的校园小说和教养手册里,“虔诚的信靠”被认为是“阳刚气概”的组成内容之一;而到了20世纪初,尽管仍然承认宗教情怀的重要性,斯坦利·霍尔在其著名的教育手册《少年期》和《青春期》里却已将“信任”定位为“阴柔情绪”,告诫男孩应当避免受之影响;学者们发现,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童书才开始真正走出基督教文化的笼罩,帮助儿童与青少年去适应一个新生的多元主义时代。这本书以《上帝,你在吗?是我,玛格丽特》为例,少女主人公面对祖辈和父辈不同的宗教信仰深感夹缝中生存的两难压力,最后她以独属于自己的方式定义了自己的“信仰”和“上帝”。
从上述童书文本的“信任”书写演变轨迹来看,少儿的“信任”情绪逐渐走出了“神”与“权威成人”的双重历史的束缚。这本书的其他章节也多次论证了这一观点,即现代童书的道德是挣脱神权、世俗父权等一切社会等级秩序的道德,它们暗示着儿童需要逐渐成长为对自己的情感和情绪负责任的主体,这可能既给儿童带来了压力亦赋予了自由。
这种成人对儿童的“放权”,正是这本书考察的时代,即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童书情感书写和教化的整体趋势。
02
儿童文学情感书写
逐渐强调长幼关系的平等化
童书情感书写背后包蕴的民主化倾向主要可以从两大方面见出,即长幼关系的平等化和同侪关系的重要化。
从前的儿童文学中,孩子是被动受教的一方,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童书越来越多地对不平等的长幼关系做出反思。《情感学习》中对“痛苦”的探讨就重点考察了暴力体罚带来的身体疼痛经验在现代童书中承担的独特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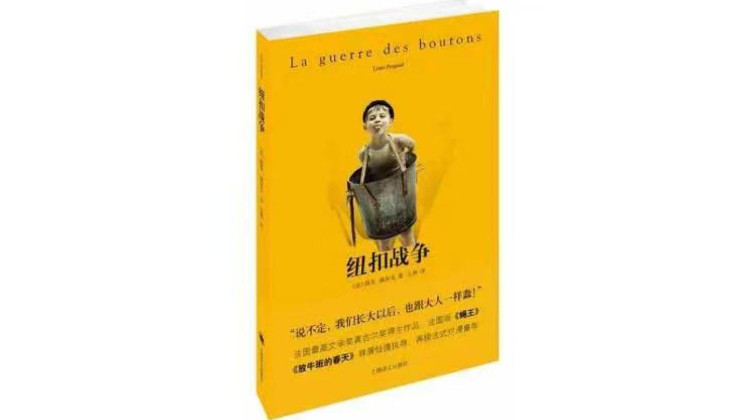
《纽扣战争》,[法] 路易·佩尔戈 著,左林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4月版
以儿童小说《纽扣战争》为例,故事将“体罚之痛”与父辈的教育无能相关联,即向读者暗示了“儿童的痛苦”是一种由成人教育者控制的教育工具,是权力的炫示。随着儿童的被“发现”和重视,人们越来越相信在他们身上施加痛苦与对成人如此行为一样,都是破坏其人格的恶劣行为;同时,儿童文学也不遗余力地告诉读者,痛苦体验往往会衍生出一系列“成长问题”,如逃跑、以暴制暴、酗酒甚至自杀,以此带领现代读者建立暴力情境下的“合乎寻常”的情感反应式(供儿童模仿),以及“痛苦”情感与“问题行为”后果之间的紧密关联。
由于最终促成“成长”的乃是少儿主人公自己对弱者的痛苦的同理心,收敛了自身的暴力行为,而非父母加诸其身的强制,《骑鹅历险记》和《秘密花园》里主角的变化从另一面向上暗示了父母暴力的无效。因此在某种角度上,秉承了平等和博爱理念的儿童文学非常直接地告知人们——并非体验痛苦或苦难,而是克服造成别人(尤其是弱势族群)痛苦的行为,才是“现代社会中成熟人格”的重要标志。

《秘密花园》,[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 著,李文俊 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假如成人教育者放纵自己的权力对儿童施加痛苦,那么童书将越来越毫不留情地剥夺他们的教养职能——就像《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父亲失去了继续为父的资格,而家长的失败却成了承受痛苦与挫折的主角儿童后续的“单独或同侪”行动并成为“英雄”的主要催化剂。事实上,这一类儿童文学也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让共读的成人教育者同理了“痛苦会生成痛苦”、施加痛苦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和客观后果。
而在另一方面,童书中儿童的同伴关系越来越发挥中心作用。同样是暴力行为,在同侪之间,打架往往被解释为释出情绪、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同侪暴力总是发生在没有父母干预的空间内,教育手段不是父母而是儿童自己的暴力或阻止暴力(见凡尔纳的《十五少年漂流记》)。
我们也不难发现,早期的儿童文学中,“成长所需的道德”是与性别话语紧密关联的。19世纪中叶,以《汤姆求学记》为代表的英国公学小说常常写到男孩团体中的学长霸凌现象,男孩们如果要拒绝战斗必须提供“高尚”的动机(往往是符合基督教要求的),男孩间的暴力被视为男子气概的证明和男性团体“入会仪式”;而到了20世纪中叶时,儿童文学同侪暴力不但更少被鼓励发生,其间的性别差异也相对减少了,《红发卓拉》《曾曾曾祖父的荒岛藏宝图》中的团体均有女性成员——不过,总体看来女孩们还是较少出现在肢体冲突情节里;而到了更晚一些时候,在《小淘气尼古拉》这样的作品里,打架更被强调其游戏性,孩子们直接从永无止境的打架和制造痛苦中获得乐趣。可见,越是到了晚近的作品里,儿童的“痛苦”就越呈现出差异化和个体化的趋势,这其实意味着儿童的感情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层次的思考。

《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法]勒内·戈西尼 著,[法]让-雅克·桑贝 绘,戴捷 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7月版
民主化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同情殖民地土著”相关议题的脚本中。在该书考察的一百多年内,欧美儿童文学对殖民地土著的感情经历了鼓励儿童同情并将此种同情心视为“文明”标志,到怀疑前述“文明性”、鼓励儿童学习土著的“原始性”以保留自然狂野气质(本质上仍是对殖民地的“他者化”),再到二战后真正质疑欧洲优越的观念,可以看到第一世界的儿童文学写作者总的来说还是走在自我反思和纠正的“人本主义”的路径上。
自此我们再度返还佩里·诺德曼和彼得·亨特等人对儿童文学的“定义”,将更深层地理解“儿童文学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为特定类型的读者书写、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样的说法——“儿童文学”是诞生于现代社会、承载现代价值观的文学。从对童书的情感研究来看,儿童文学致力于建构儿童的主体性,在漫长的探索和发展历程中,它尝试着逐步丢掉神权、父权、宗主国特权等等级秩序的绞缠,从长幼、性别、国族和下文要提到的阶级等各个维度出发,向着“平等、多元、博爱”这些动人的信念百折不挠地行进。
03
“新左派”扮演的特殊角色
和国内作品中少见的“无聊”议题
新左派思想对儿童文学“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在对儿童“离家远行”后的思乡情结的考察中,《情感学习》发现东德社会曾将“思乡病”当作一种现代性批判。
20世纪70年代时,都市环境被人们视为冷漠疏离的,儿童则被认为会因此失去确定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一些东德作家的童书里,主人公全家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搬到了城市公寓。此时的“思乡病”不再是早期儿童文学作品里儿童人格健全发育的“过渡期情绪”,不再是不成熟、需要克服的表现,而是“孩子被硬拉进去的新环境对让他们感到孤立的父母所表达的合理批评”,是对父母权力和现代化要求的抗议。

《海蒂》,[瑞士]约翰娜·斯比丽 著,朱碧恒 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1月版
从“困境解决”的角度看,像《海蒂》这样的早期作品中主人公被允许回归山林,但晚近的作品里儿童主人公则必须学会直面城市社会和现代生活的流动性,发挥其能动意志,和新同伴们一起,在城市空间里想方设法开辟出由儿童自己定义、构建的“新天地”,思乡情结在批判作用之外,也彰显了晚近童书对儿童能动性和自由的期许。
同时,新左派影响下的欧美儿文作品有时候会发现父母极端情绪的根源是他们的工作问题,而父母保守的性教育理念与他们满满当当的工作挤压掉了感情的肉体化表达有关。这些劳工视角的观察与分析思路、对资本主义劳动制度的思考,很值得原创儿童文学借鉴与思考。
而欧美儿童文学作品对“无聊”主题的书写或许是国内写作者最陌生和可深思的部分。20世纪中叶以前的旧左派童书停留在阶级压迫和社会正义这样的写实性议题上,但70年代以后,在新左派背景影响下,欧美儿童文学开始关注像“无聊”这样的现代主义文学经典题目,也就是围绕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虚无所纠缠的情绪(而非具体生活或环境)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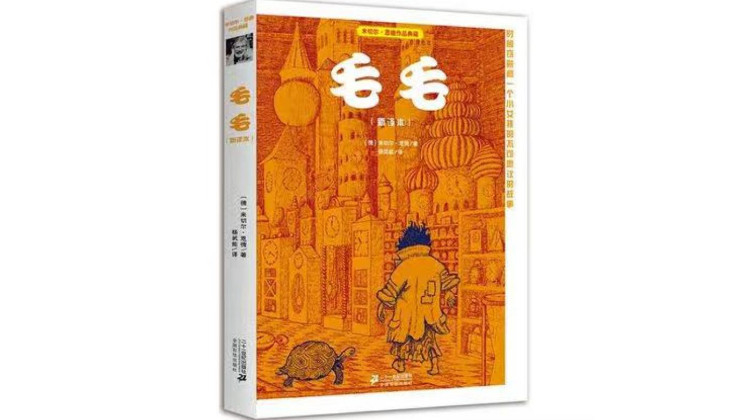
《毛毛》,[德] 米切尔·恩德 著,杨武能 译,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7月版
《情感学习》以米切尔·恩德的《毛毛》为例,指出了晚近儿童文学作品对善于运算的、反情绪的“理性”的反思,指出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筑构成的居住空间加重了现代人的“无聊”情绪,也谈及全自动的“完美设计”玩具限制了儿童想象的空间。
成年人角色在这类作品中总是扮演着“资本主义理性”,计算着实用、安全,筹谋着效率和利润,穷人和儿童的肉体与情绪总是被忽视的对象。新左派同样把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带入了最近的儿童文学思考中,消费社会无法通过昂贵的玩具和化妆品实现它们承诺的幸福,除去大量生产消费符号和单调的消费行为,人们失去了更具个性化的寻觅和实现幸福的途径。
相比之下,我们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尚且停留在对儿童思想及情绪的引导上,至多不过赞美了威廉·布莱克所谓的“天真”性(及其相关价值合集,如勇敢、游戏精神、善良等通常属于“儿童”一端的属性品质)。纯粹道德的关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教化”性而非“平等视之”的体现,我们的儿童文学可以说完全没有触及像“无聊”这样的现代文学标志性议题——当我们的成人文学作品中早已大量拥有该议题的探讨,原创儿童文学的写作者们仿佛从未敢设想、又或者是不屑于设想儿童和儿童文学可以也会与这样严肃深刻的现代性困境产生关联,遑论思考上述“儿童性”对这类现代性困境有何独特意义。
因而归根结底,这是我们的原创环境存在根深蒂固的对儿童与儿童文学的傲慢与偏见使然,以至于像“虚无”这样的哲学与情绪困境于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歧视的围墙”中颇为诡谲地成为了更“高级”的题目,反过来又巩固了这道围墙。
正如《情感学习》的作者们指出的,我们观察儿童文学内的情感书写,是为了发现儿童对书籍人物的模仿并非简单复制而是转化它们。每一个孩子会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放入自己的理解,而这又势必受到其所在的文化环境影响,其中权力差异和文化霸权更是我们不应忽略的重要因素。
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理解儿童的情感学习提出了挑战,但有一些简单而重要的事情或许能成为我们试图学习和理解“情感”的法门:有时候误读他人情感并不可怕,只要保持阅读或沟通行为,与书中人物或现实他人未知情绪的协商就会持续进行;随着现代社会人本主义的发展和对情绪的幽微世界的关注,人类对不同情境下如何感受自身不同情绪以及其他行为者会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可以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对“情感”的认知有更多的灵活性,谦虚地学习、不断地自我调整和改善、最重要的是“真诚”地感受和做出反应——这是百年儿童文学以持续不断的热心尝试告诉“未来的成人们”的,那么此刻的成人又何必羞于从中获得给养?
撰文|王帅乃
编辑|申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