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小说述评丨“成长”书写:儿童小说艺术发展的“命脉”

作为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委,我在平日阅读的基础上,用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集中阅读了四年里出版的参评作品。在评奖过程中的总体感觉是,整个社会对儿童文学的认知度、关注度在提升,儿童文学集结了越来越壮大的作家队伍(成人文学作家的积极介入是重要成因之一),与此相应,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数量和质量都有一定提升,其中尤以儿童小说的创作最为明显。
本届评奖的合格的参选作品中,儿童小说这一门类占了55%,青年作者短篇作品中,小说占了45%。就数量来说,儿童小说毫无疑问是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上的半壁江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儿童小说的创作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水准。
近几年的原创儿童文学述评类文章,从多种角度论及儿童小说的艺术表现,比如,对儿童小说书写“战争题材”“历史与乡愁”“小‘历史’”与“大‘历史’”“情感深度与叙事结构”“乡土、地域文化”以及成人文学作家“跨界”书写等都作了具有一定思考深度的评述。本文因篇幅所限,为了避免面面俱到带来的泛泛而谈,所以聚焦对于儿童小说艺术最具有涵盖性和统摄力,可以说是儿童小说艺术发展的“命脉”的“成长”书写,对近几年来儿童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一综合性论述。
“成长”书写决定着
儿童小说的艺术水准
儿童文学是立于儿童的生命空间的成长文学。反映和表现儿童的生命世界,尤其是表现儿童的心灵成长,与诗歌、童话、故事等文体相比,小说文体(包含写实小说、幻想小说、动物小说)更具有艺术功能性。几乎可以说,儿童小说中的优秀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在书写“成长”。
就近几年的儿童小说创作来说,放眼望去,《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杨志军)、《驯鹿六季》(黑鹤)、《有鸽子的夏天》(刘海栖)、《陈土豆的红灯笼》(谢华良)、《焰火》(李东华)、《隐形巨人》(张晓玲)、《建座瓷窑送给你》(彭学军)、《孤单的少校》(薛涛)、《假装被风儿吹走了》(陈梦敏)、《猫王子》(肖云峰)、《野天鹅》(翌平)等上乘佳作,都是在“成长”书写方面建功立业的作品。有些优秀作品,如叶广芩的三部“耗子丫丫的故事”、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曹文轩的《樱桃小庄》、秦文君的《云三彩》、汤素兰的《阿莲》、黄蓓佳的《野蜂飞舞》、胡永红的《上学谣》等小说,即使并不对儿童“成长”的拔节处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但是,也会令读者感受到儿童人物身上的那股成长的力量。拿评论者们交口称赞的“耗子丫丫的故事”来说,虽然采用的是“并列型”故事形式,也没有书写人物性格的发展,但是,在丫丫充满活力的心理和行动中,特别是丫丫与成年人老七的唇枪舌剑、斗智斗勇中,我分明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压抑不住的成长力量。
我认为,“成长”书写决定着长篇儿童小说的艺术水准。最好的成长小说一定是长篇儿童小说中的极品。在“成长”书写上建功立业,儿童小说创作必然是一片“柳暗花明”的前景,而如果做得不好,将会反过来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
“成长”书写
需要写好“发展型”故事
儿童文学是故事文学,儿童小说尤其如此。对于儿童小说创作,故事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离开故事,却是万万不能的。就整体意义来说,故事好则儿童小说好,故事差则儿童小说差。在本文中,我之所以聚焦于“成长”书写,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目前儿童小说创作在创构故事方面不如人意。
我将儿童小说中的故事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并列型”故事,其形态是在一本貌似长篇规模的书中,作家分头讲述了多个故事,这些故事之间并没有情节发展上的直接联系,有时删除某个故事并不影响整本作品的结构。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就是典型的“并列型”故事,本次评奖的获奖作品《耗子大爷起晚了》也是“并列型”故事的上乘佳作。另一种故事类型是“发展型”故事,其形态是由一个主线故事贯穿全书,故事在发展中环环相扣,前有车后有辙,就像穿起珍珠项链的主线,如果剪断主线,珍珠就会散落一地。本次获奖作品中的《有鸽子的夏天》《驯鹿六季》《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就是“发展型”故事。要写好这种发展型故事,不仅需要具有更强大的构思技巧和整体结构的建构能力,而且还需要对成长中的儿童的隐秘心理世界有深邃的洞察力。仅就故事层面而言,与“并列型”故事相比,“发展型”故事的创作难度更大。还有一类是“松散型”故事。这种故事不是像《城南旧事》《耗子大爷起晚了》那样有意不将作品写成长篇,而是拿出写长篇故事的架势,但是却没有规划出主线故事,叙事上又缺乏凝聚力和结构性,从而呈现出茫然若失的散乱状态。就长篇小说来看,“松散型”故事很难成为书写“成长”的优秀作品。
“成长”书写与故事叙事形影不离,相辅相成。虽然“发展型”故事未必就带来“成长”的书写,但是,书写“成长”却必然要采用“发展型”故事。
成长故事的创新性
儿童文学的一个铁律是,要表现儿童的“成长”,必须把故事写好。在近年那些真正称得上是成长小说的优秀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面貌迥异的创新故事。

在近年的儿童小说创作中,成人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不约而同地反顾童年,从自己早年的人生体验中挖掘可资儿童汲取的精神营养。在以作家的“童年”为艺术资源的儿童小说写作中,刘海栖的《有鸽子的夏天》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它经过了深度的艺术点化,是一个书写“成长”的“发展型”故事。在小说前部看似散漫的叙述里,作家不动声色地藏下了伏笔和暗线,随着叙述的深入展开,构成了下有蔓上有瓜、前有车后有辙的小说艺术逻辑,进而强化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在小说后部的高潮处,作家巧妙地设置了合理的矛盾冲突以及令人信服的解决方式,从而使主人公的成长形象跃然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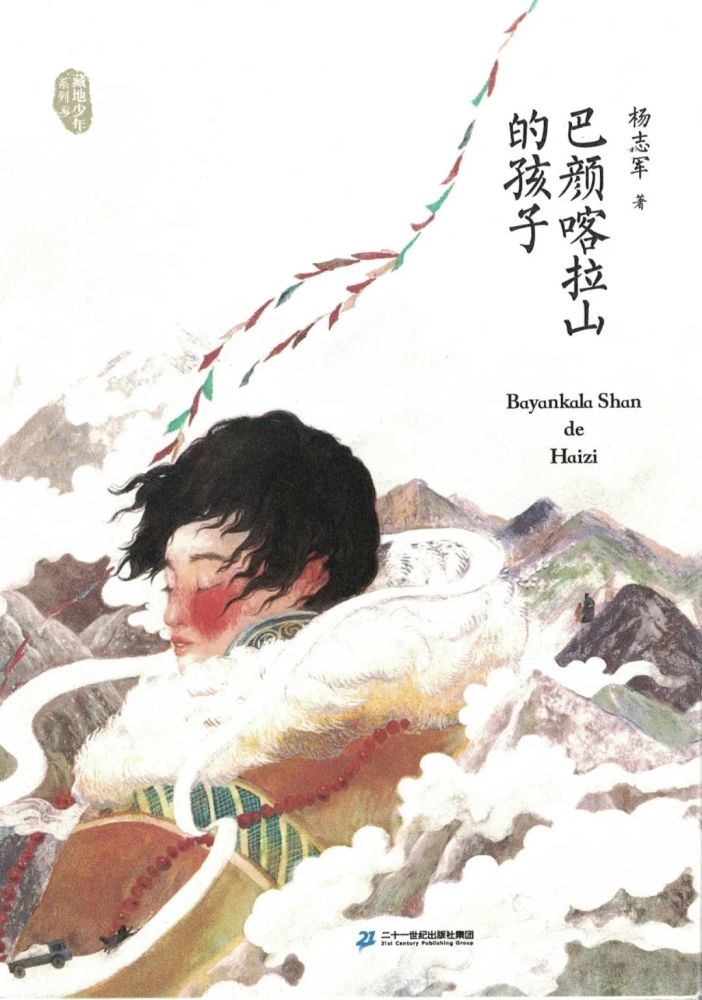
杨志军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在故事情节上也有匠心独运的巧妙设计。小说在开始便设置了伏线,就是寻找珍宝的情节,发展到后来就引出了仁青岗的车祸事件。这一设置其实把好多情节都穿起来了,比如说奶奶撒盐。作家最初明确交代,奶奶撒盐是因为坡陡路滑,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后面才得到揭示,于是,德吉的身世也被交代出来。这一情节设计非常精彩,表现出主题传达上的功能性。德吉到了城里后,他知道了钱的重要,要改变命运,要过更好的生活,于是他决定去寻找珍宝。珍宝到底是什么?最后在德吉的仁青冈寻宝的过程,这个“谜”才被解开了。与金银财宝相比,人间的爱和真情的无私奉献才是真正的珍宝。正是这种峰回路转的情节设计,才具有表现“成长”的强大功能,德吉的脱胎换骨般的转变性成长才清晰可见、真实可信。
黑鹤的小说创作像他笔下的那些动物,一直在不停地成长。在我眼里,与黑鹤此前的获奖动物小说《黑焰》《狼獾河》相比,《驯鹿六季》是有着重要而可喜的艺术发展的自然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不是典型的情节小说,但是故事的主线却清晰而结实。在儿童小说中,存在着通过书写心灵创痛的治愈来表现成长的作品。《驯鹿六季》写的就是这种故事。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治愈失去亲人的伤痛(小说中的“我”因为伤痛而失语)有很多方法,而作为小说家的黑鹤依凭其自身独特的生活资源和对大自然的深刻理解,找到了他所独有的方法——在大自然中,在与驯鹿鄂温克人秋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少年“我”的伤痛的心灵渐渐得到治愈,一方面可以接受妈妈离自己而去这一事实,一方面将妈妈永远珍藏在爱的记忆里。
黑鹤书写的成长故事的创新性也表现在关键性的细节上。失语的“我”的心灵治愈的外在形式当然是重新开口讲话。黑鹤令人佩服地将“我”开口讲话之日,安排在走失半年多的驯鹿海德薇的归来之时。海德薇是“我”亲手养大的一只白色驯鹿。“海德薇”这个名字出自哈利·波特那只白色猫头鹰的名字,而“‘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我是与妈妈一起看的。”我在黑鹤这样的安排中看到一个隐喻,海德薇的归来意味着少年的新的“我”的归来。
《猫王子》也是写伤痛治愈的成长小说,但是,作家肖云峰另辟蹊径,以超逸的幻想故事,以报纸上一个平面的现实报道为构思起点,创造了一个立体型的灵魂深处的挣扎和解脱的拯救故事。在接受委托的猫王子帮助失去胎儿的年轻准妈妈“我”祛除悲伤幽灵和回忆星云的过程中,两条线索逐渐交集。“我”救下的男孩,就是猫王子的小主人,而小主人在落水之前,正在张贴寻找离家出走的猫王子的广告。原来,猫王子与“我”其实是同病相怜,互相治愈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构想奇妙的双线交织的成长故事。
综上所述,对于书写“成长”故事的作家,写故事的戏法人人会变,但是写出的故事却各有巧妙不同。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根本上还是由作家对“成长”的精彩书写所带来的。因为,优秀的成长小说无一不是在塑造性格和命运特异的“这一个”人物,而作为人物成长的历史的“故事”,也必然是独特的“这一个”。
“成长”书写
应该成为感性心理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文学艺术就是一种感性心理学。成长小说是最具有感性心理学质感的一种文体。儿童小说作家如果具备走进儿童的深层生命世界,洞察儿童隐秘的心理动态的能力,可以说就具备了儿童小说创作的重要艺术能力。
我注意到,近年的优秀成长小说如《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有鸽子的夏天》《驯鹿六季》《焰火》《隐形巨人》《猫王子》《假装被风吹走了》《孤单的少校》,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在成长小说中,“我”这一叙述视角的设定,对于作家走进人物那深邃而隐秘的心理世界,有着最大的帮助。

李东华的《焰火》是近年来成长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小说以富于质感的语言表现,通过对主人公镜像认知的描写,抵达人物隐秘的心灵深层,在抽丝剥茧的故事展开中,揭示出少女艾米找寻自我、探究人生的心路历程,显示出作家对少年成长的深邃洞察力,是一部撼动人心的作品。就心理描写来说,这部小说是写得较为密集、细致、婉转、贴切的成长小说之一。在小说中,八仙花、歌声、琴声等等事物背后的心理描写随处可见,而那些描写都细致入微而丝丝入扣,像热了时吹来凉风,渴了时遇到清泉,让人感到及时又熨贴。篇幅所限,这里仅举一例。“我”嫉妒哈娜会弹钢琴,她不希望哈娜去养老院给老人们弹钢琴,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忘记了在电话里有没有跟哈娜说是在学校北门集合。我跟她说了是在学校门前集合,但有没有说是北门呢?或者是北门我也提到了,但没有用强调的语气,在说到北门的时候,我有没有飞快地滑过去?总之,第二天早晨,当大家都聚齐了的时候,哈娜并没有来。”你要是想知道,潜意识中的念头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之间影响人的言语或行为的,《焰火》里的这种心理描写就能告诉你答案。

黑鹤的《驯鹿六季》也有十分精彩的感性心理学的笔墨。少年“我”亲眼看到妈妈遭遇车祸而离世。“后来我无数次地回忆那一刻,而且,在每一次回忆中我都在不断地丰富那些几乎被我忘记的细节。她本来将所有的注意力都倾注在正通过手机谈的事情上,在看到我的那一刻,笑容浮现在她的脸上。她经过仔细打理的发卷,随着她的动作轻轻地颤动,我甚至记得她闪动的眼睫毛。”读到这里,我们会以为这是“我”对真实记忆的讲述,可是作者紧接着写道:“但后来我才意识到,在那个距离,我是根本无法看清这些细小的细节的。我明白,那是我在下意识中努力地完善我能够回忆起她的最后的画面。”这一笔写出了心理学所研究的在事关重要的记忆上,人的主观的情感、愿望对其发生的改变性影响。恰恰是这一感性心理学的笔墨,写出了少年对失去的妈妈刻骨铭心的怀恋,也为创痛打击下的“失语”作了真实性的铺垫。
我相信,优秀的儿童小说的“成长”书写所表现的“感性心理学”,为包括成人文学在内的整个小说艺术,提供了独具价值的艺术形式,丰富和提升了整个小说艺术。
“成长”书写的艰难之路
行文至此,我都是在讨论优秀作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年的长篇儿童小说中,这样的优秀作品的比例其实并不高。我们面对的远不是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创作状况,甚至毋宁说是一个值得担忧的状况——很多儿童小说作家笔下缺乏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的儿童形象,很多作品对儿童形象的心理和行为的把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真;很多长篇小说在叙述上不能想象和创构表现生命成长过程的“发展型”故事;在主题表现上,有不少作家思想上苍白无力,缺乏对人生、对成长、对教育、对未来的独到的理解力、阐释力和洞察力。我认为,解决这些重要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就是在长篇儿童小说的创作中强化“成长”书写意识,将“成长”书写的能力作为长篇小说创作的通行证,将“成长”书写的水平作为衡量长篇小说作家是否优秀的终极标准。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成长”书写就是中国儿童小说艺术发展的命脉。中国的儿童小说创作不走好“成长”书写这条路,将是半途而废的,而“成长”书写这条路又是崎岖难行的。艺术的辩证法是有难度才有深度,有难度才有高度。期盼中国儿童小说超越“成长”书写的难度,走向一条柳暗花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