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瓷器的一生,都要经历些什么?

跟随瓷人,走进人与物、物与心的轮回
做陶瓷,是以物为主体的一次前行与参悟。秘密在泥土里蕴藏千年,经不同代际的匠人反复推敲,瓷的一生,也蕴涵着成人的道理。NOWNESS和 PRONOUNCE一起踏入景德镇,用镜头跟随三位当代陶瓷匠人的指引,书写《瓷的一生》。
“景德镇延裹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借此食者甚众。”清代陶瓷艺术家、督陶官唐英曾经在《陶冶图说》中,描绘了自古“瓷都”景德镇由手工匠人们的聚集而生成的庞大地理画像。瓷的生命力,由自然孕育灵气,再由人通达天下。
在20世纪初关于景德镇考古的文献照片中,其中一张黑白照片里的昌江河岸开阔绵延,其中厚厚地嵌着数不清的白色瓷器和陶土碎片,整片土地与不知源自何朝何代的碎瓷交揉混杂合一,仿佛陶瓷碎片就是原始大地。古人的无心投掷,被今人有意捡拾。这样的景致与近一个世纪之后,PRONOUNCE设计师李雨山来到景德镇所看到的画面惊人一致。这个以瓷蓄气的城市,也因为瓷的韧性,阻隔了时间的翻云覆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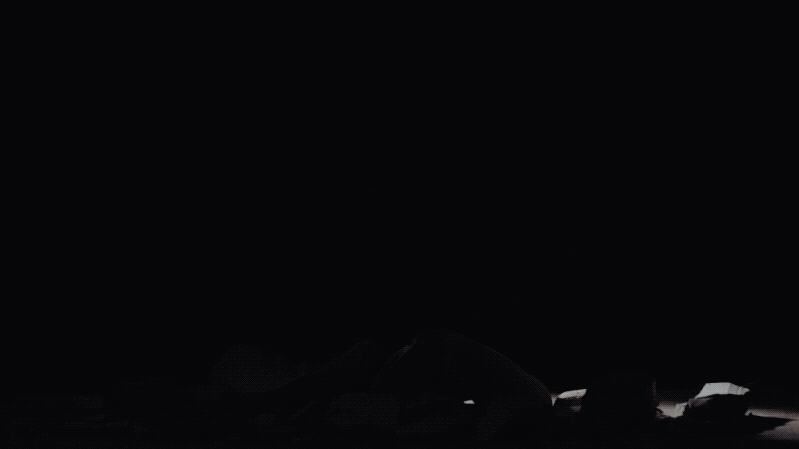
“每一个来到景德镇的人,都会首先被这些掺杂在泥土里的陶瓷吸引,甚至也可以说是碎瓷里混入了泥土。”李雨山回忆起最初来到景德镇的感受时说道:“我当时从水里捡了两个瓷片,带回了工作室。这个城市,就是给人这样沉静的感受,它不浮躁,有耐力,有耐心。”
景德镇的制瓷工艺传承了上千年,数十代人挖掘、淘洗、调配瓷土,制作瓷器,也通晓瓷器。到了如今,新一代的手艺工匠们逐渐聚集。许是采集,抑或扎根。无论是制坯人Karman,金缮修复师王科开,艺术家梅琳玉与继物师尹福国,还是服装设计师李雨山与周俊,他们各自的故事集合在一起,正是当代景德镇新人文物语的一帧剪影。

广东女孩许迦羿Karman手指纤弱有力,一双灵动的眼睛如鹿一样警觉机敏,身体上的细枝末节暗示着她与生俱来的倔强与叛逆。两年前搬到景德镇,Karman从零开始学习制陶,曾经在成长经历中缺失的孕育与关怀的情感关系,在制陶的过程中逐渐被寻回。她将这看作是一场修行,而河床与陶土,就是她的心灵所栖。
湿土、捏泥、塑形、晒干、再装窑,Karman秉承着传统的制陶工艺,手捏陶土的过程无声且漫长,需要的心力可想而知:“陶瓷完全就是‘真的’。一旦自己体验过动手创作之后,它给你的感觉就像是一次修行。”Karman说道。她将每一个自己制作的陶器“视如己出”,除了制作过程的手工交付,还有情感的浇灌令其作品承载了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脾性:“陶器特别像一个孩子。我从选泥巴的材料到上釉,然后到烧制各种不一样的试验的阶段,会有一种怀孕的错觉。你需要不停地去给自己补充知识、能量和营养去孕育这个孩子。”


开窑的瞬间,永远是最期待的,但同时也可能是痛苦的。如果没有烧制成预想的样子,难过的情绪多少都会冲淡期待的雀跃。但如果“烧到了”,甚至烧出一个意料之外的形态,惊喜之情不言而喻。在Karman看来,每一个成品无论饱满残缺,都凝结着超越了血肉关系的血缘感情,是她的“孩子”。
她并非对这样的心路历程完全陌生,这与自己的原生家庭环境不无关系。六岁时,Karman由养父母的一次突然告知,得知自己并非亲生。血缘二字背后裹挟的沉重含义从此盘踞在她的成长脉络里。亲生父母的不辞而别让“家庭”的面貌突然模糊,对养父母的疏离、对家庭成员的规避、与亲生父母的隔阂……她长久以来无法清楚认知在这些关系网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这些因素的交叠,催促着她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伴随敏感与成熟快速自立。

人从破碎的状态中自我重组,才可以更坚强地走出来。Karman如今回想起还未来到景德镇学陶的2019年之前,身体的病痛与精神的枷锁让她越来越喘不过气。她换了居住地,也换了新名字,景德镇的风土浸润了她焕然一新。安静从容的生活氛围让她找到了追寻自由的最终目的——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宁静。那正是她在日后无数次与陶土相对、独自制坯的时刻。陶瓷改变了她的能量场。一旦进入了创作状态,Karman就像入定一般扎实地归隐。眼、手、心构成了最稳固的三角关系。
一件瓷坯,从开始捏制,到送入窑房的过程,需要制坯人精神状态的高度集中和稳定。在《浮梁县志》中曾提到,这样的工序在古时需20人左右的工作量。可以想见当群体作业范围缩小到个人,更需要何等的精神聚焦:“每一个不同材质的创作,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的创作。做陶瓷,对我来说是精神上的状态。借着这种材料来表达你精神上的东西。”

以肉身的力量说服生命本身,这正是孕育的神奇。Karman说自己的陶瓷是不规则的、扭曲的、变形的延展。有朋友告诉她,无论是她的陶瓷还是绘画,都能从中读到一种冲破网捕,向上飞升的力量。她喜欢这个解释,因为这与她改掉自己名字的初心不谋而合——“羿”,像一只羽翼丰满的小鸟,正在向上扇动着翅膀:“我的能量场始终是向上的。做陶瓷是我心里的‘底’,但是我与我的‘孩子’,始终都在向上飞。”

与古陶瓷修复师王科开见面的时候,院子里的火苗正旺。他在火堆中投进果皮、树叶等自然物质。“嘶啦”一声,果皮与树枝被火舌吞噬,留在瓷器身上深浅不一的印记是它们曾经存在的证明。这样的“证明”带有随机性。王科开正在尝试用坑烧的方式,钻研瓷器自身发生的偶然与想象——这是一种带有韵律的美。
烧瓷,本身就是与意外打赌。每一只器皿永远只呈现为“现在”这一刻,器成,人走,过去即成为连绵不断的此刻。器皿的纹路表象下蕴含着一系列流畅的动作、思索和决断,如匠人不停的思路与判断力。对于王科开来说,烧瓷是个人修养与专业延伸的一脉相承。


王科开来自四川广元。2016年进入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2017年到三宝国际陶艺村,师从“一善门”首席继物师学习金缮修复。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对于古陶瓷的修复介绍,基本映照了他平日里的工作内容。但与之不同的是,相较于年纪略长的老师傅,王科开生于1998年,这个“一善门”里年龄最小的修复师,对古物修复的着迷,仿佛来自天生。
在如今景德镇古陶瓷的圈子里,活跃其中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喜欢随机地去室外的泥土地里捡拾残碎的瓷片。从现今的考古资料看,景德镇最早的中心地带位于浮梁县兰田村柏树下窑址。柏树下窑址是自晚唐到五代的民窑,依水流之势,占地面积逐渐扩大,发展到后来因明代的官窑制度,大批量不达标的瓷器被直接砸碎销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景德镇的土地里被深埋了几代的瓷器碎片。这些瓷片是王科开与同伴们寻找古迹的现实脉络:“那种老瓷片,我感觉刚来的时候还没有见识,都感觉像宝贝一样,而且到处都是宝贝!”


破碎的物品并没有失去它本来的美,这关乎审美观的通达与世界观的塑造。与完美无缺的商品化物品相比,王科开更欣赏的是破碎但生命力依旧存续的美。王科开专攻金缮。人们熟知的当代金缮工艺,是金漆瓷器修补技艺。本质上是漆艺的范畴,常用作于瓷器破损后的修复工艺。将破碎的瓷器,粘好后在接缝处用金粉进行绘画。在王科开看来,金缮的美在于它不光保留了残破的感觉,还有包括修复师在修复上的微妙处理:“比如说那条金色的缝线,我们给它勾出这条线的韵味。粗细虚实,转折的地方有顿挫,像是书法的走向。这里面也有一种韵律感。”

王科开自小学习中国传统乐器,二胡、古琴、琵琶,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乐音轻重缓急之间亦有抑扬顿挫。他经常潇洒地拿着乐器,享受在景德镇亘古通今的自然环境中徜徉其间的快意感觉。拨弄琴弦,也像是拿着刮刀与圭笔。在器物之上修补的过程,是另一个更细致维度之上的“轻拢慢捻抹复挑”。一点点打磨,一点点精细。他慢慢认识到,对待金缮,不光是将它视作最贵重的金属,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对最珍贵、最深刻的物件之心去相对。景德镇是珍贵的“天成”,无论是破碎还是完满,传至他这一代人手中的宝贝,是万万不能被怠慢的。

静默的工作室里,因为电钻的声响、大漆颜料的码放,此刻显得更像一个实验室。2015年,江西人梅琳玉在景德镇创立了“一善门”工作室,从事器物修复及相关工艺教学。围绕“缮”字,梅琳玉通过不同介质的延展和研究,生成了他的理解——对物修缮,源于人心的向善。
同样始于破碎的瓷片,梅琳玉与同为“一善门”的继物师尹福国将目光转向锔(jū)瓷。这是一种来自过去的修补手艺。中国人在劝诫他人小心分寸时通常会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然而,有了金刚钻,技术的升级和材料间如何相互配合达到效能利用之最大,就变得更为重要。东西坏了可以换新的,这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新的东西入手了,是否意味着旧的、坏的物件就可以舍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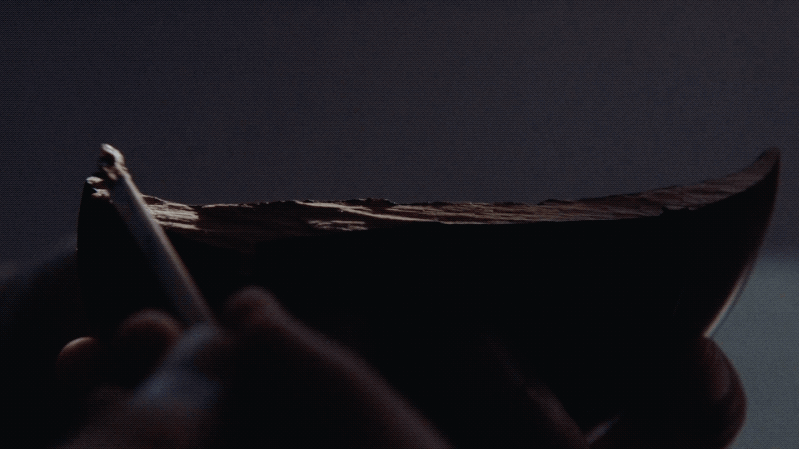
对锔瓷技术的重申,似乎正在为破损物件在当代生活中的尴尬处境重新定位。2020年,梅琳玉硕士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陶瓷与玻璃专业。正适逢景德镇迎来了新一轮的“文艺复兴”。他的作品关注材料的本身,以及不同语境下材料的可能性。

修旧如旧,仿古若古,是文物修复的定律。把新的材料用好了,才能最大程度上复活“旧”物。梅琳玉对材料的扬弃是一种直觉性的、非功利的探索。他记得家里以前留存下来的一把紫砂壶,上面有两三百个钉子,且都是一两毫米极微小的细钉,他惊叹于前人的精细与惜物之心:“你可想在那个时期这种工艺难度有多大?古代手艺人不会做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在上面。我们这边能看到最早的实物资料,有元代时期、宋代时期的一些老瓷器上的工艺,虽然铁钉已经氧化脱落了,但是它的痕迹还是在的,证实了当时的人对这件物品的喜爱程度和珍惜之心,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它完成修复。”


如今,材料得到更好的优化,银或铜质的钉子在硬度包括使用时长上达到了专业继物师的标准。放大到修复语境中,陶瓷和金属材料结合,将陶瓷本身已经携带的伤害适度地“可逆”,是对陶瓷工艺本身的尊重。梅琳玉与尹福国认为,陶瓷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信使密码,它本身自带信息,每个瓷片都是一个时代的入口。其上所显示的绘画、工艺,能够直接展示那个时候的生活面貌。能把这样的细节“修”出来,一定程度上,将复原一个时代的画像与风貌。
尹福国刚进入古陶瓷修复的行业环境时,还是刚刚踏入社会的青涩年龄。来自山东的年轻男孩带着家里人的嘱托,一定要“学一门手艺傍身”。然而随着景德镇的再度复兴,以及修缮事业的发展,尹福国感觉到这门手艺并不是仅仅“傍身”这么简单。他与“一善门”肩负的还有新一代景德镇人决心把手艺传承下去的责任感。手里这把金刚钻,修复的是断层发展下的历史与未来。

在PRONOUNCE一贯的故事伏线中,对众生相的观察,以及对平凡英雄的赞美,是始终不变的主题。景德镇中几代默默耕种的瓷人,就是从本土文化中,具象索引而出的“平凡英雄”。
因向内探求,而打下基底。PRONOUNCE设计师李雨山与周俊将这基底直指向对自身文化的了解和挖掘。聚焦景德镇,与景德镇中人,匠人们对于器物的敬意,对自然的亲近,与当代城市人群的遗忘和麻木形成了对比。古与今的差别映照,被信息时代的隔层逐渐放大。时装在此之中,能做些什么?

有水的地方,滋养着文化的生成。文化的生命力像水流一样汩汩向前。景德镇瓷器文化的实际传承中,志趣相投的有缘人逐渐聚拢。千百年来,景德镇人顺水而聚的特性未曾改变。正是借由河水的流动,发散了这一段以瓷为脉的历史。从2021秋冬系列在时装背景中对锯瓷的讨论与演变,到了2022春夏对于“圆”的形而上学式探索,雨山与周俊用东方式讲求“体验为悟”的创作方法,解释着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本土文化延绵与再创的理解:客观物像皆会因外力破碎,而能否修复和圆满则取决于自身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