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雕艺术家李忠荣获中国玉雕大师联合会认证玉雕大师、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叶 弥|金仁顺


有一次看了金仁顺的短篇小说《爱情诗》,发个微信给她:“你他娘的写得真好。”
——写到这句话,我考虑着是不是把“他娘的”这三个字拿掉。因为这是私聊,粗糙的话语秘不示众。但是我考虑了几秒钟就决定示众了。是写得好,他娘的写得真好。
然后金仁顺回话了,她一反常态地没有以糙攻糙,正常地对我说:“我喜欢听你这句话,如果有一天你写我,就把这句话写在文章开头。”
我终于逮到一个写她的机会了,我把那句夸她的话写在开头,无由地觉得有点感动。
每次和金仁顺相见,总是很高兴。当然每一次都是不期而遇,在某个与文学相关的活动上。我和她都属于慵懒之人,能不联系就不联系。忽然遇到,四目相对,彼此就会说出一些开得烂熟的玩笑话,当然是糙话。每次开过相同的玩笑,总是哈哈大笑。
我很羡慕男性之间相处时的一些粗糙,一些不计较,一些心心相印。与她这种玩笑让我感到女性之间的相处也能如此粗糙和轻松。可是谈到心心相印,我俩都不擅长建设这种关系。我最喜欢的就是和她从不联系,突然不期而遇,四目相对,糙话迭出,傻子一样笑——离心心相印也不远了,就是不高兴再走近一步。这是最好的关系,差不多像传奇的关系了。
我想,我们两个人本性上有相同的地方。但她是朝鲜族,我是汉族。她是70后,我是60后。想来想去,只能是艺术上的相通。
我俩相见时,除了八卦,艺术也谈了不少。有时候还想谈点科学。有一阶段我迷恋黑洞、暗物质之类,常常被这些宇宙科学吓得失眠。宇宙中的故事,比鬼故事更让人害怕。我把这些话对她说,没想到她兴奋地说,我要听,你讲给我听,我喜欢听。她的语态暴露了她的个性,她是好奇的、顽皮的。
谈艺术时,我们总是陷入一种虚无的严肃,两个人又像盲人摸象,严肃地摸来摸去,摸不到完整的象。但是两位盲人很满足,完整的象并不是必需的,甚至有时候虚拟的象也可以。到了一定的阶段,连虚拟的象都可有可无,就如京剧里某些超现实场景一样,比个手势就行了。这一点上我俩高度一致,也就是说,我俩是盲人摸象,却不约而同地摸到了同一只象耳朵或者象腿,这样我俩就很高兴,皆大欢喜。
但是谈小说与写小说还不一样。
她的小说没有虚无的严肃,有时候看她的小说,正觉得应了一句苏东坡的诗:“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她的小说有这样的气派,也有这样的气息。常常是,正看得惊险紧张,人物灰飞烟灭了。张爱玲的小说,常常也是灰飞烟灭。同样是飞了灭了,境况是不同的。譬如张爱玲写一位女子,写她怎样的讲究,怎样的留恋,种种情状。到最后,张爱玲告诉读者,世事其实无可留恋,人生多么苍凉。所以有时候看张爱玲,就像看洋化的“三言二拍”。
金仁顺有一阵子写话剧,我没看过她的话剧,不知道她写得怎样,我相信她会写得像她小说一样的好,因为看她的小说,常常看出来莎士比亚的味道。人物和故事也是朝着毁灭而去,男女主人公却一路悲壮,一路互相掐着脖子滚进万劫不复之地。
一个是自然的灭,一个是人为的灭。一个是不当解说员,一个是自已当了解说员。张爱玲是那么骄傲,她要居高临下地告诉读者,她写的人物是苍凉的、感伤的。金仁顺不是,她不骄傲。她小说里的人物,依托着故事,一步一步地走向某种毁灭。不是苍凉,不是感伤,而是让读者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生活真相。这里面综合了许多因素,有努力,有挣扎,有推诿,有反思,有调侃,有幽默,有幸灾乐祸,有一江春水向东去……当然,苍凉和感伤也有。反正我每次看她的小说很激动,不知道这一篇又给人什么样的真相。奇怪的是,她的小说常常写毁灭,但不给人沮丧的感觉,就像我们日常的生活一样。是的,这个女子的本事就在这里,她把不寻常的东西放在寻常里面了,掩盖得很好,说的都是正常的话,做的都是合理的事,让你看了不会产生不适感,更不会由文生情怀疑自己的生活,不会把自己代入她的小说。又像远远地离着她的舞台,远远地观着别人的戏,有着安全的距离。我是差不多看完了她所有的小说,掩卷之后,才突然一阵害怕。感到我的生活或许也在走向毁灭。不知不觉中,我已走近她的舞台,她小说中的人物已经成为我周围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都毁灭了,我有什么理由不毁灭?我即使不想毁灭也只好毁灭。
我对她有隐隐的恨,后悔把她的小说看了个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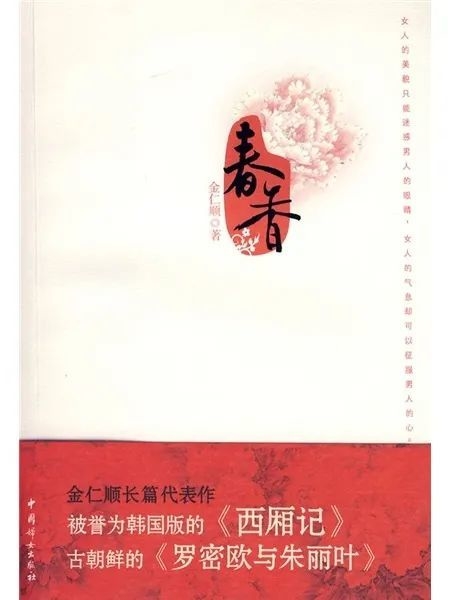
︽春香传︾金仁顺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版
再回到我俩盲人摸象的比喻。岁月更迭中,她渐渐地把象摸了个完整。这也是我恨她的理由。对于文学这头象,我也是千方百计地想摸个完整而不得。这里我想起魏微兴之所至评价我的一句话,大意就是叶弥写得还行,主要还是归功于叶弥懵懵懂懂的混沌状态。我可能有点混沌,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魏微、金仁顺这些狠人,对文学之象自然是了然于心。岂止是一头象,她们是写整个世界的作家。
看完金仁顺的小说,不夸张地讲,我想我不写也可以了,我看得很满足。作为她忠诚的读者,我喜欢看到她写小说时从不故作姿态,从不故作高深。她的小说是外松内紧的。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会看到她小说的精美,从结构上讲,都是一气呵成的,人物从头到尾始终不走形。她小说的语言,我尤其喜爱,读的时候就如一匹丝绸那样光滑无物,甚至不会特意去留心语言的优劣。读完之后突然惊觉,忍不住回首凝望读过之处。我经常读完第一遍,回头再去看她的语言。作为同行,我深知她这种貌似平实的语言更需力气,既要充沛的精力,又要屏声静气。要有语言上的野心,又要有足够的低调。要有艺术上的天份和本能,要有自信和底气。这些语言朴素、干净,来自于生活,与生活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正常,又有那么一点儿戏剧性。更重要的是,每一篇小说,不管里面有多少人物,这些特性表现在每个人物身上,各有声音又浑然天成。
金仁顺的小说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古典题材,一块是现代题材。这两大块泾渭分明,又不分伯仲。在艺术上,在分量上,在字数上是差不多的。中国好像没有哪个作家是这样写作的,反正我认识的一大批作家中没有这种情况。我曾好奇地仔细观察她,她没有分裂症的表现。
要得分裂症的人是我,看她的小说,真是分裂得不行。她写的古典题材,大多是写朝鲜族的事,她一本正经地叙说,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仆役、娼妓,于生活、工作的细节处,一一都详实可信,吃穿用度,全是史实。市井风貌、农桑耕织,全有源头。每个人的行为和语言都合乎各自的身份。所有的可信,所有的平常,都被她纳入一个故事之中,这个故事往往是有着巨大的荒诞。看完之后,你对荒诞想要怀疑点什么,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被她一点一点地拉进她的小说世界,你也成为了她的一部分。不仅来不及,还力不从心了。她的小说看似平静,实则粗野有力,是开拓者的那种力量。
古典题材绕不过她的长篇小说《春香》,这部小说被誉为韩国的《西厢记》。但《春香》与《西厢记》那么的不同。《西厢记》可以说是孙悟空用金箍棒划出来的一个圆圈,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相恋到最后分手,全在一个圆圈里完成。《西厢记》的标签是始乱终弃,崔莺莺之所以被塑造成一位被男人遗弃的悲剧女性,追根究底,还是怪那个圆圈。欲望与身体有关,她的身体囿于一块小地方,除了自己的房间,只有后花园能进行爱情的布道。她的灵魂再叛逆,也无法走出自己的世界。听过这么一句话,汽车的发明,解放了妇女。当然,世界上第一位驾驶汽车的人也是一位妇女。因为妇女比男性更渴望外面的世界。
金仁顺深谙此理。她的《春香》非但不是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的圆圈,很多时候,《春香》里面的女人简直是孙悟空本人,闪挪腾移,世界广阔。香夫人也是被男人所弃,但她选择了接纳更多的男人。在接纳更多的男人同时,她把自已的住所打造成一个美丽奢华的“香榭”,香榭和她本人一样成为南原府的一个传奇。这样,遗弃她的男人只能成了她生命中的众多过客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春香》里的女人们也经营着一个住所,她们像蜜蜂似的在里面劳作,也主宰着自己的住所。她们的住所与崔莺莺的住所不同。第一,崔莺莺足不出户,香榭里的女人们却与社会紧密关联。第二,崔莺莺不是一个劳动者,对于风花雪月,她只欣赏不劳动。香榭里的女人们都是劳动者,包括香夫人和春香。她们创造可以欣赏的一切风景。也创造了一个传奇。第三,香榭里的女人们常常会做梦,美梦与恶梦。崔莺莺从不做梦,她所有的梦就是张生。张生走了,她的梦就灭了。
说到底,小说里的人物都由作家赋予生命。在《春香》中,我看到的生命形态是自然的,美好的,也是强悍的。
《春香》里有一章这么写到梦境:
我的梦境都与鲜花有关。香夫人说这是我常年洗花浴造成的。季节好的时候,香榭被玫瑰花笼罩得密密实实的,我们每个人的气息都沉浸其中。到了冬天,花木凋零,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香榭里的草木,各自拥有不同的味道。
面临着被情人遗弃,春香是这么对待的:
李梦龙绷紧了脸,俊美的脸庞上线条明朗。
“春香小姐,我很抱歉无法对你的未来做出承诺。回到汉城府,宛若进入茫茫大海中,我连自己身上会发生怎样的变故都无法预料。”
“你用不着抱歉。”我对李梦龙说。
……
“那么,”我李梦龙说,“我们就此告别吧”。
男女爱情从古至今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态度。女人在爱情上用了多少的劲,影响她对待爱情以外的事。香夫人在爱情上的洒脱,使得她还有心情和精力营造出一个招蜂引蝶的“香榭”。
金仁顺这一类的小说中,女性全都承受着压力,社会的、家庭的、性别的。但这些女性几乎有着同样的坚韧。她们受难,她们靠自己救赎灵魂和身体。金仁顺写得铿锵有力,质地细密,不由分说。
《盘瑟俚》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文学作品中经常见到子弑父,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女弑父?女弑父这一命题在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也没有人研究过这个现象。一般来说,生活中和小说里,母女常常是一对矛盾,有女儿想杀母亲的,没有想杀父亲的。因为父亲代表着自古而来的父权,代表着男权的力量。而女儿则是柔弱的,是处在下风的那个人。但在《盘瑟俚》中,女儿杀掉了父亲——真的下手了。这一下手,就把文学的内涵拓宽了。这篇五千字不到的小说,是金仁顺一个上午写成的,用她的话说:“哗啦啦地一口气写完。”
我也哗啦啦地一口气看完,然后反复五个哗啦啦——看了五遍,欣赏这位低调的女作家出色的文字表现,为她的力量感到惊讶,并自愧不如。
这篇小说写得干净利落,可以说是教科书式的写作,没有一字游离漂浮。情节仔细道来,一分一毫也不差,却一节一节地往上走,挟着雷电声、刀剑声。当父亲逼迫女儿像她妈妈一样操持皮肉生涯时,女儿的杀机已经暗伏在心。
“盘瑟俚”是朝鲜族的一种曲艺样式。它生来的使命就是娱乐,但在金仁顺的笔下,它成了拯救那位弑父之女的武器。府使大人正想杀掉弑父之女,老艺人玉花请求唱一曲盘瑟俚。一曲唱完,全场感动。有人高喊:“放了这位可怜的姑娘吧。”
嗯,也放了我吧。我已看了五遍了。每次都看得心酸。
好想听一听盘瑟俚。
叶 弥|金仁顺


我问过金仁顺:“你觉得现代题材中,自己写得好的是那些?”
她就一本正经地向我推荐了六篇,还说:“你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
我遵嘱把她推荐的六篇仔细看完,得出一个结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她的现代题材,我最喜欢的不是她推荐的那六篇,而是她没推荐的《爱情诗》。就是我一开头说的,他娘的写得真好。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年轻男子安次接到一位陌生女人的电话,经陌生女人的提醒,他才想起对方是一家酒楼里的“第一美女”——陪酒女赵莲。当时,他给赵莲还背了一首北岛的诗:“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朝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交出现在,/决不交出你。”
看到这里,我隐隐地感到,这位背诗的安次,就等着上陪酒女赵莲的当吧。
赵莲给安次打过电话后,两个人就见面了。赵莲说,她碰到了坏人,想占她便宜。她逃了出来,希望安次帮她。
这个故事看上去是用来引诱安次的。
安次就把赵莲带去酒店开房。这个行为表明了安次已接受赵莲的引诱。故事真与假都无关紧要。
从去酒店开始,安次渐渐反客为主。两个人唇枪舌剑,女方继续使手腕,但明显很焦急。而男方却悠哉悠哉,不慌不忙。
一直到最后,两个人才成了情侣。而赵莲,仿佛明白过来,问:“你从什么时候起打我主意的?”她不知道的是,安次想的是另外一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曾经把这首诗读给他听。
这里,作家给读者留出了空白,没有交代安次给多少女性背过这首诗,也没有描述他被爱情伤了多深。只写了一句:安次的心却空落落的。
他得到了赵莲。是他用他的方式得到了赵莲,而不是赵莲引诱了他。但他还是失去了爱情的方向。这与那首充满理想的诗大相径庭。
赵莲还在问:“你敢说你的诗不是故意读给我听的吗?”
这一句话暴露了一个事实:她才是猎物。她并没能填满安次的心。安次大约会用一生去填补失落的心吧。
所以,这是一个爱情如何伤人的故事。金仁顺没写爱情伤人的过程,而是写了一个男人被爱情伤了以后的失落和无路可走。没有写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而是写了男主人公和女二号。当然,我们不知道,女二号之前,还有过多少女二号。
这就是小说的高明之处。
2021年4月24日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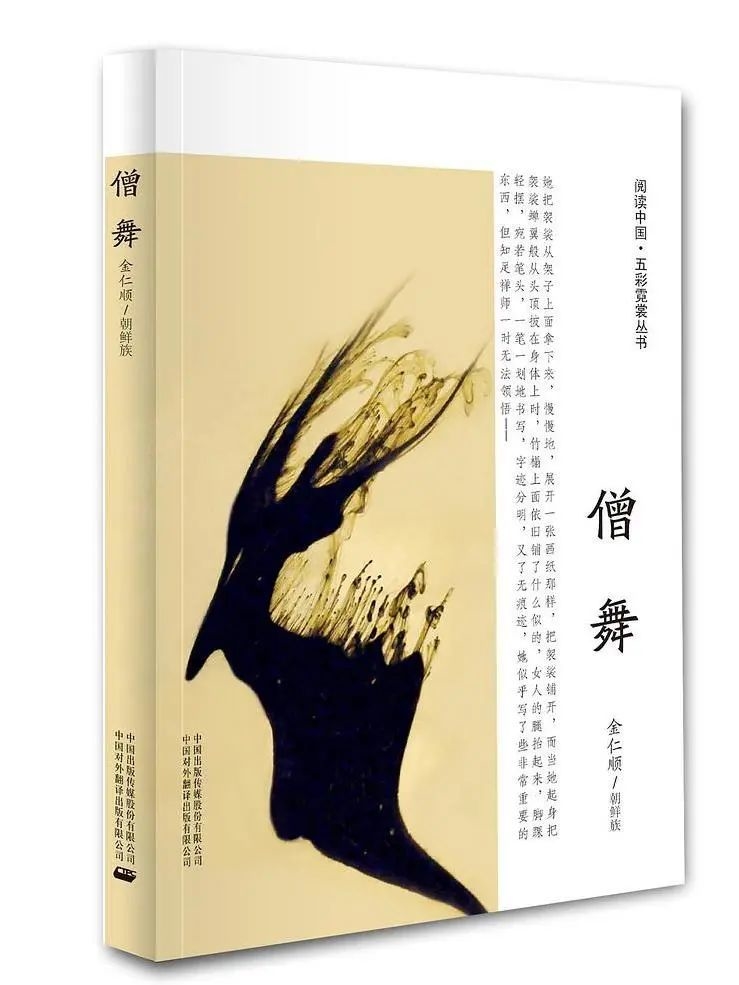
︽僧舞︾金仁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版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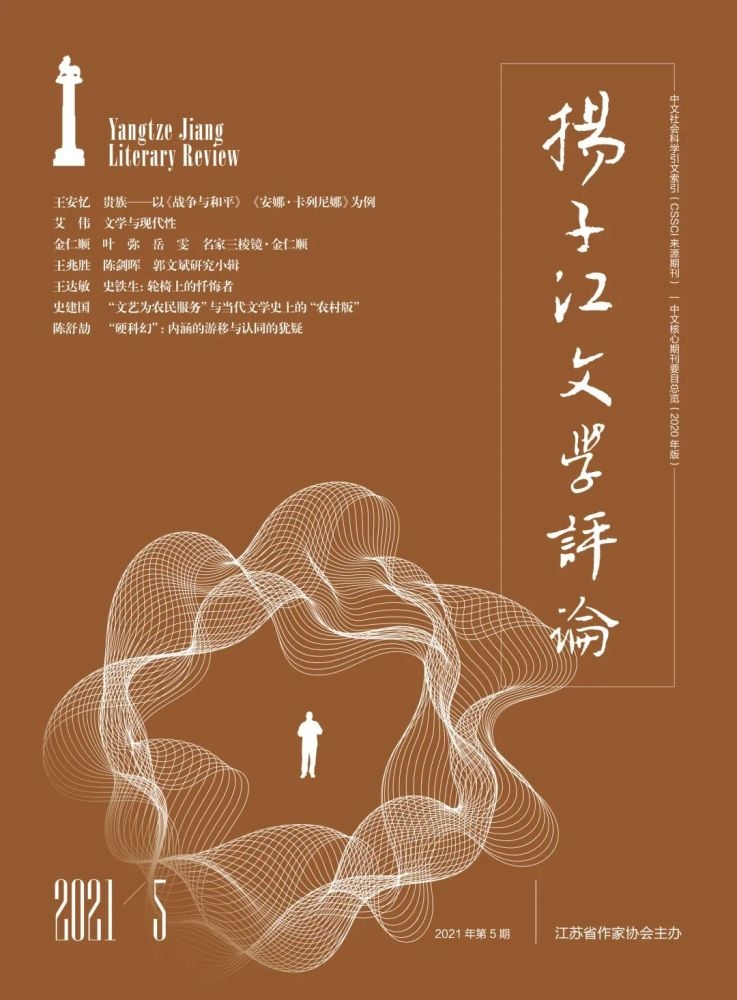
大家读大家
王安忆| 贵族——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为例
艾 伟| 文学与现代性
名家三棱镜 金仁顺
金仁顺| 写作这件事
叶 弥| 艺术的本能——试论金仁顺的小说特质
岳 雯| “莽林”与“神迹”——金仁顺论
郭文斌研究小辑
王兆胜| 精神生态与绿色写作——郭文斌散文的价值旨趣
陈剑晖| 安详哲学与诗性文化——郭文斌文化随笔论略
班易文| 时间的乡愁与记忆的传承 ——文化记忆视野中的《农历》解读
新作快评
李 振| 孤独的骗局与契约——阿乙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
思潮与现象
陈舒劼| “硬科幻”:内涵的游移与认同的犹疑
顾奕俊| 知识分子的“神话”与“肉身”——八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知识分子书写管窥
文学史新视野
史建国| “文艺为农民服务”与当代文学史上的“农村版”
庞秀慧| 混沌与困境:论新世纪以来乡土叙事中的“权力书写”
周 鹏|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书写与乡村文化变迁
作家作品论
王达敏| 史铁生:轮椅上的忏悔者
冯祉艾| 都市荒漠下的诗意栖居——论潘向黎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书写
顾星环| 数字化时代的吴语叙事——以《繁花》网络初稿本为例
赵苓岑| 象征、悲剧意识与“偶尔的疲惫”——关于余华的长篇小说《文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