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永恒与时间之间的张力和结果
 2021-09-23
2021-09-23

学界传佳音,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新作《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以下简称《现》)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詹姆逊的文学理论从来都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诸如《政治无意识》中对《老小姐》、《吉姆爷》和《圣经》的令人难忘的阐释;对处于跨国资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主题的敏锐发现。他在新作《现》中,又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首次对“现实主义”进行现象学直观分析,更加注重作家作品的内在精神的直觉发掘。在对左拉、托尔斯泰、加尔多斯作品解读中,他抛开过往的“三层阐释法”,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中重新获生命的体验。对于一位肩负着马克思主义使命的理论家而言,此书不啻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理论与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一、对现实主义的本质还原
在西方近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是一个最具歧义性的概念。它被层层覆盖,直至失去本来面目。我们讨论现实主义,所有的思考都没有击中靶向,而是偏移到其发生及消散的两个端点,并陷入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中:现实主义与传奇、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且这些二元对立无不具有复杂的政治意义,都试图引导读者对现实主义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经过这样的考察后,詹姆逊发现现实主义歧义就在于其内在的二律背反,这样他必须做一番现象学的本质还原。
詹姆逊在《现》中反复强调作现象学意义上的考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他首先指出了卢卡奇对现实主义的讨论,也是针对它蜕变为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批评;而罗伯-格里耶倡导“新小说”,不过是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技巧已经穷途末路,难以展现当代现实。显然,他们都是针对现实主义的消散端。倘若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界定现实主义,把两个端点的要素剔除,就会呈现一种历史的断代式的描述——它不过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种文学思潮。而这种立足于历史断代的描述有可能把文学史置于笼统的文化史,继而进入基于生产方式的历史模式,这就对复杂文艺现象进行了历史的大简化。并且又因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一对立概念本身已经是一种历史叙事,因此,它也不能被视为某种结构或文体问题。凡此种种,都表明我们很难把现实主义确定在某种固定的意义中,因为它已经逾越了自己所属的那个历史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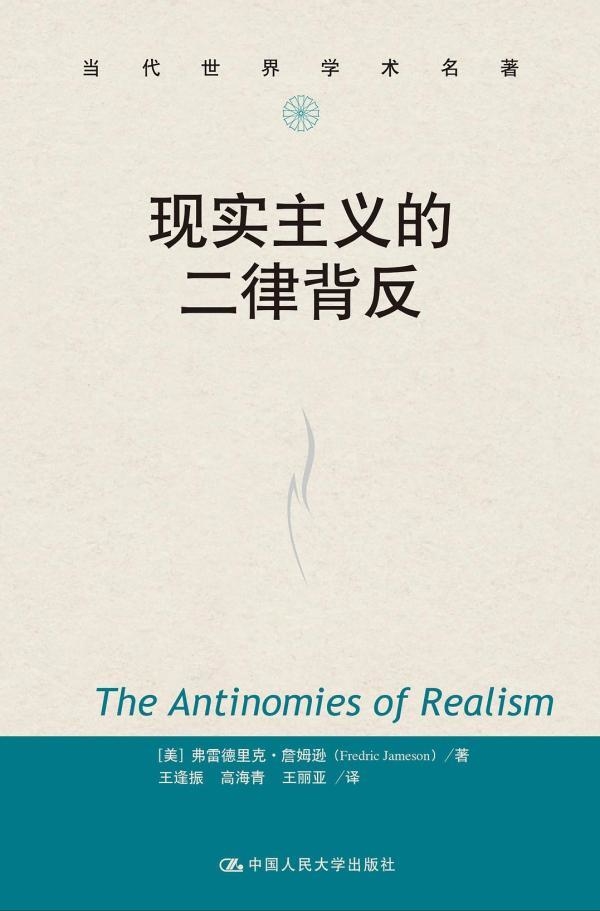
《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
作为现实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卢卡奇在论述小说形式与历史关系时,他的态度却是含糊的。他在《小说理论》一书中认为,形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将表征问题化,使得形式能够记录一种完全世俗的现代性及其无法调和的矛盾。卢卡奇在后期的著述中,又把现代性视为资本主义,把小说看作现实主义,认为小说的功能在于揭示历史动力。在这些把现实主义小说置于形式问题的解释中,形式是否记录了某个社会发展状况,或者形式本身就是社会对其发展状况及其潜在问题的自觉意识?面对这些问题,卢卡奇模糊而含混的立场,为现实主义添加了又一层覆盖。因此,詹姆逊感到有必要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对现实主义进行本质还原。
首先,作为一种形式,现实主义在历史上一直与去神秘化相关联。去神秘化主要表现为手法的多样性,在《堂吉诃德》中就是对传奇的不断拆解,使得那种通过美化骑士价值展现社会特征的手法被大大削弱。塞万提斯正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消解了西班牙社会结构中的心理与价值残余,让读者感受到现实主义叙事的力量。当现代主义小说开始建构全新的主观体验时,这种对社会的否定功能就开始衰减,去神秘化就转变为陌生化。此时作品中的情感色彩形始衰退、放弃或妥协,直至走向带有现代主义冲动的新认识。
其次,现实主义的内容总是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形式密切相关。这里,形式往往通过内容加以展现,恰如一幢建构物,由现实主义和叙事共同参与完成。叙事所含有的批评从来都是有针对性的:它直面资产阶级社会,却没有展示人们所希望看到的一面。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得以彰显出来——诱导读者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现实:舒适、个人主义和金钱。也就实现了现实主义小说巩固社会秩序,增强资产阶级社会抵抗历史,抵制变化的社会功用。这样的分析是基于詹姆逊一贯的政治无意识的。
在詹姆逊看来,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概念,人们经常把现实主义与小说相提并论,往往把二者看作同一对象:小说的历史无异于现实主义小说史。他认为很难用某种统一的标准来界定现实主义。如果我们希望从现实主义中获得某种社会认知,最终得到的却是意识形态;如若我们希冀获得一种审美满足,结果只看到了一些过时文体或点缀品。因此,詹姆逊倡导辩证地看待现实主义,聚焦于它的二律背反。他精彩地描述了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运作:作一个历史进程和演变过程的现实主义,其间否定与肯定互相缠绕;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它自我分化、拆解和消散的过程。这是一个悖论,一种不规则现象,詹姆逊把它描述为一种矛盾结构,或两难之境。当对立面消融为一体时,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同时也作用于这一现象,促使其瓦解。统一体不是混合,而是对立,在互相吸引又彼此排斥中的较量与统一。这正是詹姆逊试图要揭示的二律背反在现实主义内部运作方式。
总括起来看,现实主义不过是由各种不同素材不断混合,直至演化成了小说的形式。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成分:民谣、广告印刷品、报刊摘要、回忆录、日记与书信、民间故事、童话的样式。作家依据其叙事成份,从这些繁芜的书写样式中挑选出典型,并凭借叙事总动让小说一气呵成,诸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两个端点也清晰展现出来:一是关于讲述故事的谱系及其故事,二是感受在文学展现中的呈现;前者指向过去,后者指涉未来。倘若我们同时把握这两个端点,才有可能对现实主义进行新的界定。当纯粹的讲故事形式和场景描写(尤其对主观感受的描绘)共生互惠时,现实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二、现实主义的两大驱动力:叙事冲动与感受
探究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们必须先辨析现实主义与叙事的区别,因为人们通常把现实主义视作叙事。为了辨析这一问题,詹姆逊提出了“叙事冲动”。这是叙述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它先于现实主义小说,并在现实主义小说兴起之后如影形随。叙事冲动的直接产物就是“故事”。这里,詹姆逊从现实主义的显性动因叙事切入,层层剥离直至叙事冲动,进而呈现出叙事结构多样性、变异性。
叙事不外乎是要讲述关于个人生活或命运独特性的故事。詹姆逊赞赏萨特从哲学和意识形态角度洞析故事与小说的差异对立,把莫泊桑的短篇故事解释为资产阶级的生活场景。萨特认为小说应该讲述关于真实的存在之事在时间中的展开。叙事的时间属于过去,所述之事在叙述开始之前已经完成,属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是,小说却能够展示对自由发出召唤的此时此刻,同时赋予尚未明确的未来以开放性。一言以蔽之,叙事的目的在于展现未来的开放性,即便过去的时间一成不变,人类也得用行动对其进行重写,使之发生改变。亨利·詹姆斯把叙事与小说之间的界限表现为“讲述”(telling)与“呈现”(showing)之别。如果事件由叙述者讲述,就是复述;如果是从事件发生时刻进行展现,则为呈现。这两种策略在小说中交替使用,并且从一种转换到另一种的过程中具有了形而上意义。例如,《十日谈》中著名的《猎鹰》故事:为了得到一位贵妇人的爱,费德里哥散尽钱财,最后只剩下一只猎鹰。当贵妇人来访时,他已经家徒四壁,只好把心爱的猎鹰做成美味招待客人。后来当贵妇人得知事情真相后,改变了原先对他的看法,答应了他的求爱,嫁给了他,而他也因此又成了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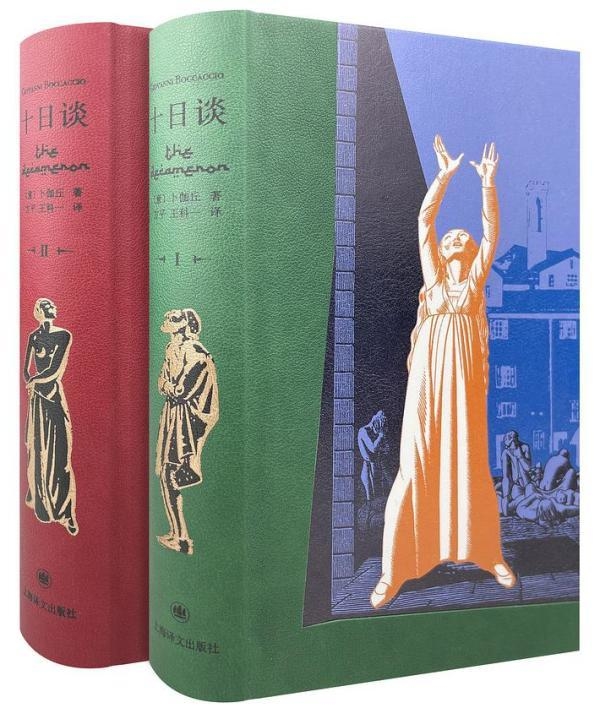
《十日谈》
在这个故事中,作者把不同的意义汇集在“猎鹰”上,将叙事时间浓缩为一种特殊的感受,时间使得空间中的那件事显现为一个“特殊时刻”。这里的“猎鹰”不是某种象征,而是起到了统领与深化故事的作用。“猎鹰”就是主题,并担负着相应的叙事功能。“猎鹰”是费德里哥的全部,同时也是一个替代物,代表他对贵妇人的热烈情感,因为对方无动于衷让他备感绝望。正因为如此,他才把猎鹰当作自己的全部奉上。对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具有重要意义,若不是为了她患重病的爱子,贵妇人也不会专程拜访费德里哥的。如果小男孩不是生命垂危,他也不会让母亲去见费德里哥。“猎鹰”使三人的受挫感情结合在一起,令故事完美,带给读者一种凄美而圆满感。
尽管已发生之事不可逆转,但是,它在现在或未来被重写、修正,因为读者永远处在现在,并将不同的时间带入叙事过程。这就涉及到意识中的现在与线性时间的问题。意识中的现在属于非个人的,是永恒的、存在的现实,它从外围控制着纯粹的场景,即呈现。事实上,叙事与小说、讲述与呈现所展现的是命运与恒久的现在。在詹姆逊看来,现实主义来自对立项之间发生重叠后的界面之中,现实主义是永恒与时间之间的张力及其结果。
感受是现实主义的第二大冲动,詹姆逊把它视为叙事的对立面。因为叙事的所述之事均已发生,故事里的所有事件都以线性时间先后呈现。当经验还原到无限期的现在时,它只能依附于身体。具体而言,身体被孤立在无期限的现在,它开始感知更多的感官信息,即感受。这里的感受指身体的感觉,而感情则属于意识到的状态。例如,巴尔扎克对伏盖公寓的描述:“房间里散发着一股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气味,只能作公寓气味。那是种封闭的、发霉的、酸腐的气味,吸进鼻孔觉得潮湿油腻,还有一种阴冷直接穿透衣服;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碗碟、救济院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这里的描写展示了第一印象,即感受。它没有确切的名称,难以分类,但是,人的感官却被调动起来。这种气味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媒介,把感受凸显出来。事实上,感受的感染力——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气味的结果。但是,这里的描述不仅是为了引发感受,而且表示某种意义。在对巴尔扎克而言,任何一样看似属于生理范畴的感觉——霉味、腐臭、油腻的布料——都具有意义,是一个符号,或者某个故事人物相关的某种道德象征,象征其社会地位的寓言:体面的贫穷、肮脏、暴发户的装腔作势、旧贵族特有的那种高贵。总之,这种感受不完全是感觉,它本身已经是一种意义、一种寓言。
福楼拜比巴尔扎克晚了十年,采用的方式则是对叙事话语进行精心安排。两位小说家用不同方法调整语言方式,展现历史变化中的真切感受,叙述主体及其感知的差异。詹姆逊从语言及其展现的现象学意义对感受进行探讨,有助于从历史维度揭示对感情进行命名的符号体系与无名称的身体感知之间的张力。
三、对左拉小说的精细解读
在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当中,对感受进行最丰富、最生动展现的当属左拉。与卢卡奇一样,詹姆逊倾向于把左拉视为现实主义小说家。左拉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中,以“有缺陷的遗传基因”,把各种人物及其关系编织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族谱。透过这些关系网,读者看到有关“人类命运”的演绎,即一个基于生物学立场的叙述结构。这种叙述结构在离奇曲折的情节推进中演变成一种厄运,左右着人物的命运。
普法战争以及突然崩塌的第二帝国,为左拉观察社会、调整视角提供了千载难遇的机会,这便是《贪欲》的创作背景。历史素材直接摆放在左拉面前,由他设计合适的创作形式。左拉用一种实验姿态替代此前的政治立场,其观察的对象不仅仅是感受,而是被命名了的某些情感,即情感的美学表达。如何处理人物历史与故事情景,这是左拉必须面对的问题。他借鉴刚刚兴起的印象派绘画艺术,用语言展现图画场景。这种语像方法要求叙述者像摄影师那样,对准物体同时移动摄影机,使每一个聚焦对象依次进入镜头,就像早期电影中的景物一样。
左拉笔下的描述没有过多的隐喻意义,主要是关于现象及其或然性的记录,包括赤裸裸的生理与身体现象,感受就在这种描写中得到显现。《巴黎的肚子》的开篇,故事背景是新落成的巴黎中央菜市场,黎明之前新上任的巡视员弗洛朗突然来到这里。此时,载满货物的货车也纷纷抵达。菜市场里大量的蔬菜,一堆堆血淋淋的动物肉类,还有奶酷、香肠……左拉从描写鱼的种类开始,一页接着一页写下去,各种鱼类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怪物与异类。正是这种视觉现象孕育了感受:当某种被命名了的感情逐渐丧失其力量时,用于描述这种感情的词语反而为描述的话语提供了新的空间,使得某些未被展现的、未被命名的感受一同涌入词语空间,继而开辟自己的话语空间。在气味的作用下,弗洛朗的身体经历了一种感觉引发另一种感觉,并互相叠加,他感到阵阵恶心。
在左拉所有的作品中,叙述中心常常从一个人物切换到另一个人物,表面上看毫无章法,实际上却形成了双重视点,就像画家对绘画艺术的探究那样,把主人公对世界的探索一并呈现。他没有让前者的视觉取代后者,而是让它们平行发展,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立体的视觉画面。左拉采用此方法的目的在于将感知从具体的观察者(个体)中释放出来,使观察独立于人物。弗洛朗长期远离城市生活,久未与人打交道。更重要的是,眼前景象不同寻常:市场里人声嘈杂,各种气味,闻之欲呕。在此情况下,他的观察变得不同寻常,感知记录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强烈冲击。

《妇女乐园》
在《妇女乐园》中,小说细致描绘白色的桌布和床单,呈现人物的幸福感。主人公慕雷沁入白色的幸福感极其强烈,诱惑着投资人,引发各方竞争。展现在小说里的这一幕犹如管弦乐中重复出现的合唱,每一次重复内容都一样,但每一次重复都清晰可辨。故事人物探索着存在的意义,左拉把那些与感觉相伴的信息以一种自我呈现的方式摆在读者面前,故事人物开始显得可有可无。随后,左拉就让这些人物的欲望得到了释放,并把那些富有商业意味和解释功能的名词收集在一起,刺激着读者的感官。这里有两个隐喻层:一是感官的,它在现实生活中以各种方式存在,便于人们辨认不同物品——鱼、奶酪,及其属性;二是与故事中那两位闲聊的女士具有呼应关系的某些象征意义。在她们眼里,各种各样的事物在周边频繁发生、从不间断。这种现象与流言的传播方式具有相似性。就弗洛朗的例子而言,他的个人生活、触犯国家法律的不良记录,以及难以启齿的流放经历,终究会真相大白,就像难闻的气味一样,总有源头。左拉提醒读者:“有那么一会儿,你会觉得勒科尔太太和萨热小姐散布的流言蜚语,就是这股难闻气味的源头。”
此外,左拉小说中的感受的展现具有自动指涉的特点,它显现为形式,但在展现过程中又将其变为自己的内容。他对感受强烈程度的强调也因此成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用以解释他的小说实践。左拉的小说犹如一个巨大场地,形形色色的身体数不胜数;这些身体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并在不同的空间中,如房间、街道,形成各种交叉点。《小酒馆》里散发着恶臭的黑暗角落,《萌芽》中昏暗的地窖,象征第二帝国腐朽的洛可可风格客厅,这些空间里挤满了各种身体,个个形象生动、毫不雷同。至于外部空间,新的建筑与断壁残垣一并涌现,大写的历史与其他历史构成的现象学图景拥挤在一起,不断向周边扩展。在这里感受变成了一幅对照图,强化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效果,同时又不至于使这一效果滑向其对立面。
詹姆逊对左拉作品的精致而引人入胜的阐释令人激赏。这一切都是他在对现实主义进行一番现象学考察之后,剥离出它的内在动力——叙事冲动与感受——的基础上展开的。要准确阅读和理解詹姆逊的《现》,就必须考虑这一点。而这一点在任何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中都是反复出现的,恰如管弦乐中的合唱一样,左拉如此,托尔泰、加尔多斯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