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蛐蛐大乾坤,秋虫折射天地盈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秋风起,蟋蟀鸣。作为民间古老的娱乐活动,“斗蟋”成了秋季重拾传统的热门游戏。“斗蟋”可不仅是玩儿,作家白峰多年来不但养蟋蟀,还和大家分享“斗蟋蟀”的趣味与文化,他出版了多部关于蟋蟀的著述,这些研究折射出历史的变迁和民间的风俗画卷,很难想象,小小秋虫竟大有乾坤。
从小玩虫
练就“斗蟋达人”
白露之后蟋蟀玩家四处斗虫忙,其间最大乐趣就在于蟋蟀相斗一刻的精彩刺激。斗蛐蛐是以前孩子们常玩的游戏,许多人的童年是伴随着蛐蛐的厮杀长大的,虽然多数只是业余爱好,但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走进白峰家中,他正在侍弄蛐蛐,书房的地面上、架子上,放满了大大小小的蟋蟀盆,估计有几十只,每只盆内皆有秋虫居住。白峰是齐鲁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现任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杭州市蟋蟀协会顾问,宁津蟋蟀协会名誉会长、宁阳蟋蟀协会顾问等职务。他担任过《山东文学》编辑,1994年开设了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曾引领了济南的一股文化风潮。

白峰在斗蟋蟀
面前这些蟋蟀可都是白峰千里挑一,精挑细选出来的“大将军”。只见他手持着电筒,扫射着几个罐子里的蛐蛐,不时给各个罐中的蛐蛐喷水或者“打草”(用草梗挑逗蛐蛐,检测体质),有时还用放大镜细细查看……听着秋虫此起彼伏的鸣叫,非常惬意悦耳。
伴随着蟋蟀们的奏鸣曲,白峰谈起自己成为“斗蟋达人”的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七八岁的白峰刚上小学,跟着院里大孩子们一起玩,因为那时没有多少玩具,斗蟋蟀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有一年,他抓到一只好虫——“正青白牙”的蟋蟀,这只虫战无不胜,咬败了院里几乎所有的蟋蟀。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从那时开始,白峰乐此不疲,后来逐渐走上玩家之路。
斗蛐蛐
是纯粹的中国民俗
每年随着8月初“虫季”的开始,白峰就转战于宁津、宁阳等地,寻找彪悍善战的“猛将”……
花鸟鱼虫之中,斗蟋只是虫类之一端。“斗蛐蛐这个活动辨识性很高,是纯粹的中国民俗。”白峰说,蛐蛐出现的比人类还早,早在侏罗纪时代的化石中就发现了。《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用细致的观察、饱含深情的语言,从生物学的角度介绍了蟋蟀的习性,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不过,若论千年来中国玩家对蟋蟀的认知程度,恐怕连写《昆虫记》的法布尔也难以企及。
虽是小虫,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描绘。从《诗经》开始,无论是汉赋、两汉乐府诗、魏晋南北朝文学,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对这种小虫都“青眼有加”,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白峰的蛐蛐罐盆
中国人自古喜欢斗蛐蛐,欧洲的西班牙人喜欢斗牛,美国西部牛仔喜欢马术和骑野牛运动。白峰认为,这些不同的习俗并非偶然产生的,它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
白峰说,中国人较早地确立了农耕的生活方式。物候、节气,都是在农耕生活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自然的认知,这和中国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代甲骨文中的秋字,其形像就是蟋蟀或蝗虫,古人把蟋蟀鸣叫的季节叫做“秋”。可见,秋虫蟋蟀就是“节令虫”,它与季节密切相连,成为一种物候特征的反映,或者叫“物候虫”。
蟋蟀自古鸣唱至今,除了作为季节虫,古人还发现了它的咬斗习性。据白峰考证,从宋代开始出现斗蟋的文字记载。也有说唐代出现的,那是清代人以讹传讹,唐人诗歌以及记载中主要是以感秋为主,并未提及一个“斗”字。北宋时的陆佃(陆游的祖父)在《埤雅》一书中以三百余字描述了蟋蟀的习性,但并未提及蟋蟀有咬斗的习性,可见直到北宋时斗蟋还没有形成风俗。斗蟋最早是从南宋的都城杭州兴起的,十二世纪中期普遍出现了斗蛐蛐的游戏,从那时开始,历千年时光,这一民俗活动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成为世界上独有的文化景观。
遵王世襄所嘱
完成“古谱评注”
在养蟋蟀的过程中,白峰与一些大家结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王世襄先生,两人的交往成为一段佳话。
白峰与王世襄结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段缘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蟋蟀。王世襄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收藏家,更是著名的“老玩家”。在传统观念中,斗蟋蟀是和“玩物丧志”连在一起的,难入文化殿堂。王世襄花多年时间纂集《蟋蟀谱集成》,收集历代有代表性的蟋蟀古谱十七种。书成以后,又写《秋虫六忆》以为附录,将蟋蟀这一民俗活动引入到文化史的视野当中,让秋虫也“登堂入室”。
白峰说,刚开始读《蟋蟀谱集成》时,感到如坠云里雾里,倒不是不认识里面的字,而是集成中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谱,常常各家所云莫衷一是。比如清代和民国谱产生巨大差异,其中很多地方相互矛盾,让人越看越糊涂,究竟谁说得对呢?而且有很多难解之谜。“像我们现在玩蟋蟀的人首选是山东宁津、宁阳和河北产地的蟋蟀,明代宣德皇帝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就近在山东、河北选蛐蛐,而从南方的苏州进贡?”白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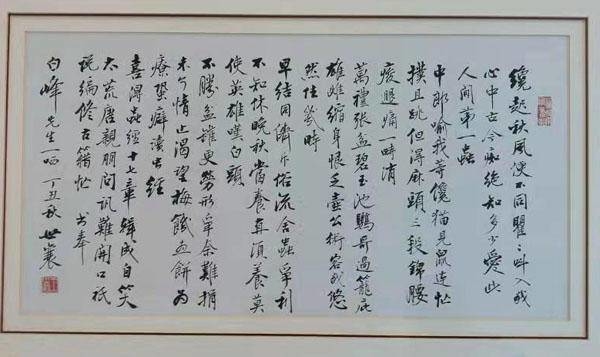
著名收藏家王世襄为白峰书写的《秋虫六忆》
当时被很多问题困扰的白峰特别想向王世襄请教,到北京三联书店工作后,经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先生的帮助见到王世襄,且成忘年之交。 “老一辈学者特别含蓄,他想成全你,却不多说,只交代你去哪里找谁办件事。范用先生拿了一张王世襄的照片,不动声色地说,麻烦你顺路把照片给王世襄带去,然后就告诉我王先生的住处。”白峰说。
到了王世襄家,茶已经沏好,看得出他是知道我要来的,应该是范用先生提前打过电话了。白峰将自己诸多困惑向王世襄先生求教,有的获得解答,也有他难以解答的。
当时,白峰提议王世襄先生能不能做一个“评注本”或是“眉批本”,给广大蟋蟀爱好者提供一个通晓的蟋蟀谱文本。但王世襄先生当时正忙于整理“鸽经”,还准备着手“摔跤”等数项写作,无暇顾及。不过,王世襄嘱咐“你有此心,又真心喜欢,所提问题有些我也没想过,倘假以时日,能处处留心,你可以做做此事。”此后,白峰常去拜望王世襄先生,畅谈养狗斗虫、民俗文玩,每至秋时,王世襄也来电话询问今年山东出没出好虫,有没有得到好蛐蛐。
令白峰感到欣慰的是,他已遵王世襄所嘱完成《蟋蟀古谱评注》一书,他著述的《中华蛩家斗蟋精要》《解读蟋蟀》《斗蟋小史》等专著也是对王世襄先生的致敬。目前,他正着手《气候作用力——蟋蟀值年将军初探》一书的写作,试图解读自然界的奥秘。
蟋蟀的优劣
是气候变化的生动写照
有了王世襄的鼓励,白峰开始留心蟋蟀方面的史料和一些相关的问题。白峰说:“后来慢慢地居然读出点意思来。比如我发现了中国历代的气候变迁和地缘的关系。蟋蟀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个玩物,实际上它关联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情感方式。”
“比如,紫黄(蛐蛐的一种)虽然从清代以来被抬得很高,但事实上,明代嘉靖本《秋虫谱》里只是视为一般间色虫,位列真青、真黄、真紫之次。”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别?是因为历史上气候冷暖变化起起伏伏,几千年来有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寒期暖期,气候冷暖既影响着蟋蟀的不同色类,也使最佳产虫带产生南北移动。明代宣德皇帝之所以不要山东、河北的贡虫,而到苏州寻找贡虫,是因为当时气候偏冷,最佳产虫带南移的结果。“蟋蟀谱由于跨越数百年,所以不同时期的人对蟋蟀色类有不同趣味,也折射了气候变迁。蟋蟀本身就是物候生物,其战力受到自然条件严苛的制约,蟋蟀的优劣实为气候变化的生动写照。”白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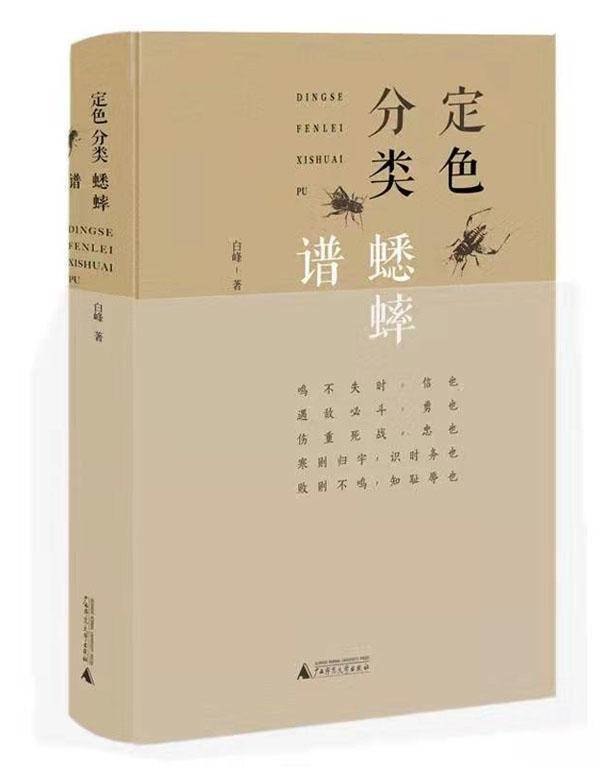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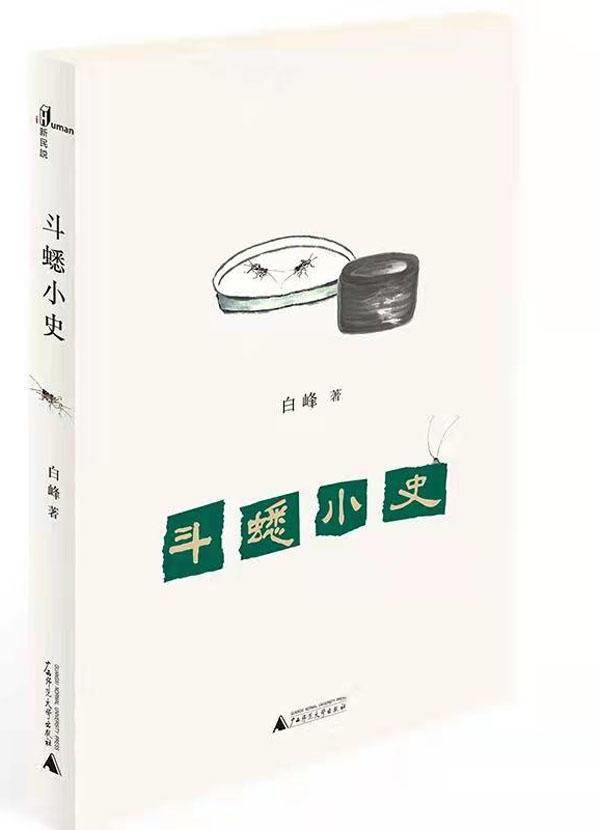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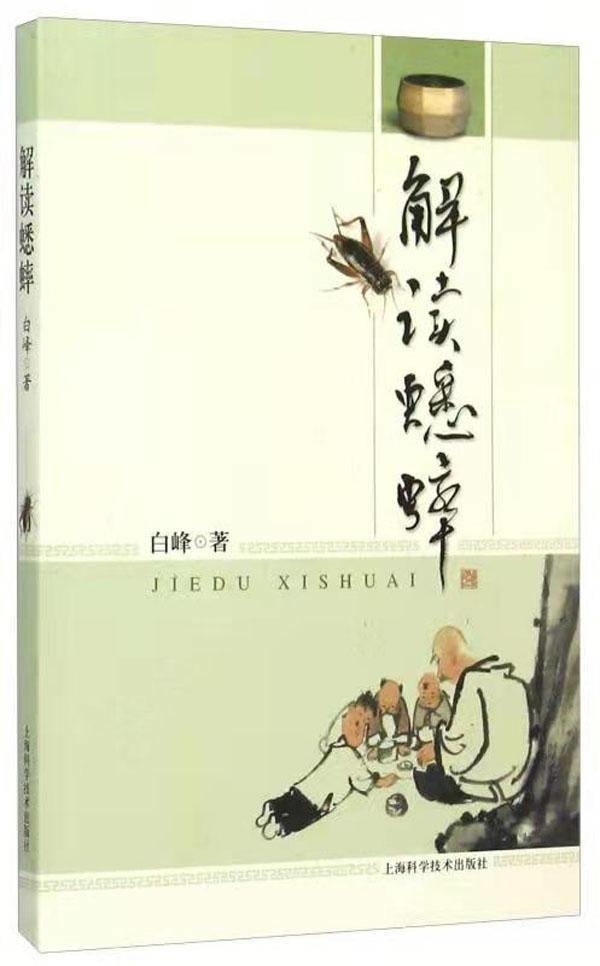
白峰出版了多部关于蟋蟀的著述。
杭州成为南宋斗蟋中心,也与气候变迁有关系。白峰说,较之唐代,北宋的气候较为寒冷,唐代长安城里盛开的梅花、宫中栽种的柑橘,到了宋代都已经不能存活了。到了北宋末年,气候的变化忽然加剧了。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12世纪是一个寒冷的时期,当时杭州每年的最后一场雪,一般是在阳历3月中下旬,最晚的记录是在阳历4月中旬,这相当于今日河北北部、辽东半岛的情形;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跑运输的马车,可见当时温度之低。
“几千年来,蟋蟀可以视为中国人宇宙观念的一个缩影,是对天地规则自然观的一个体现。”白峰说。
白峰还运用《黄帝内经》的理论,深入地解读蟋蟀,梳理出一条适应天时地利选养和分辨各色蟋蟀的途径。他在书中深层次解读了蟋蟀虫性、虫品、虫色演化与大自然运行规律的因果关系,这在以往的蟋蟀著述中从未涉及。他认为,自然界的季节变化、风寒暑湿,全部都影响着生命的内质和表征,人类如此,蟋蟀亦如此,这与中医理论似乎是一脉相承。气候变异,虫势也会变化,运用五行六气的方法,找出虫色逐年生化的规律,对分辨选养蛐蛐极具价值。而且用这种方法研究蟋蟀的准确率很高,他经常告诉朋友,今年该收哪一种虫,哪一种色的,哪个产区的,有一个大的方向。
白峰曾在文章中写道:悉天地之盈虚,率阴阳以出入,是为“蟋蟀”。这小小秋虫折射出天地的盈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