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依然严重的今天,亡羊补牢是否还有意义?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在可预见的未来,生态灾难将会对人类造成严重影响。这是怎么发生的?亡羊补牢是否还有意义?
美国圣母大学教授维托利奥 赫斯勒早在三十年前,就在哲学层面分析了与生态危机相关的种种问题,并提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前提。为此,必须重塑以自然的观念为核心的人类价值观,必须找到可行的方法,帮助我们自己及未来的人们摆脱生态危机。
三十年过去了,对于《生态危机的哲学》中提到的问题和提供的解决路径,赫斯勒教授(以下简称“H”)如何看待?三联书店特委托本书译者邢长江做了一个简短的访谈。(后附本书译者序)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电影《星际穿越》剧照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从哲学层面思考生态危机
访谈
赫斯勒教授您好!现在,我们全世界对气候和环保议题越来越关注,各国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从《生态危机的哲学》到现在的几十年中,您认为我们在生态领域中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H:一个自相矛盾的社会事实是,我们的经济成功助长了生态危机的加剧。虽然我很高兴今天全世界的贫困人口比1990年少了不少,但我们的确需要彻底的改变,例如,我们的能源政策,必须让当前的这种增长在未来也能持续。
事实上,我在翻译这本著作的时候想到的是,您的“生态危机的哲学”在我的国家可能引来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的观点来自学院派。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会认为,只有纯粹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第一哲学”)才是重要的,实践哲学,特别是生态问题的哲学是没有意义的,是不重要的。另一派观点可能来自于社会大众。他们也许会认为,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看法可能过于脱离实际、迂阔而又缓不济急。您这么看这两种观点?
H:我当然认为,哲学的基础是“第一哲学”的问题。但我同时也认定了,哲学必须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回馈社会,而这只有在哲学对其时代的关键问题提供答案的时候,才是有可能的。生态危机是超越任何独立学科的问题,它的根源还在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理解——因此,它需要哲学的处理,首先需要扭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理解和观念。
您在这本书的扉页向您的朋友汉斯·约纳斯致敬。您如何看待汉斯·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和他的实践哲学?它对您的工作有何启发?
H:我崇敬汉斯·约纳斯,他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父亲的形象。他悲惨的一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及时设法离开了德国,而他的母亲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他曾参加过反德国的犹太旅),他曾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一些伟大的名人的学生,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布尔特曼。他在许多不同的哲学领域工作——他以极好的原创方式研究了诺斯底主义,他写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生物哲学之一,他试图将我们的道德能量从天真的乌托邦思想转向更温和但至关重要的任务,让这个星球在未来仍可供人居住。
您是一个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大家,但是您又是一个关注实际问题的实践者,您如何理解这两重看似互相完全矛盾的身份呢?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过,想要在现实中实践规范性的价值理念,最终注定会失败,因为这是哲学力所不能及的。哲学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黄昏的时候才能起飞。您觉得黑格尔对实践哲学的消极态度对您有影响吗?
H:并不。关于“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我更像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而不是黑格尔主义者,即使我把黑格尔的社会制度理论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我关于黑格尔的书(《黑格尔的体系》)不只是热情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体系做了辩护,而且也提到了它的许多缺点。因此,我不会称自己是黑格尔主义者,而是客观观念论者。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开始的传统,黑格尔就属于这个传统。我试图用更谦虚的知识手段来延续这个传统,但也意识到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简单地重复经典的答案而不加以修正。
《生态危机的哲学》一书是由20世纪90年代初您在莫斯科的一系列演讲的结集,而您本人也在圣母大学的德语和俄语系任教。可以谈谈俄罗斯文化,谈谈本书诞生时的俄罗斯和莫斯科给您的总体印象吗?
H:我的俄语知识不够好,我只是偶尔教授俄罗斯文学。但我深爱俄罗斯语,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俄语一直相当接近古老的、传播路径曲折的印欧语系,所以当我说俄语的时候,就觉得很接近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另外,我喜欢腭音的发音方式。听俄罗斯歌剧与听意大利歌剧的声音体验截然不同,但都不失为崇高的体验。
1990年的莫斯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密不透风的管控正在消失,人们充满了希望,戈尔巴乔夫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你几乎可以畅所欲言地谈论所有的事情。同时人们所谈绝不是空洞的,而是事关存在层面的深刻的东西。我一生中从未如此鲜活地感受历史的气息。
在《生态危机的哲学》问世的那个“历史终结论”流行的时代,您就反驳道,我们面对的未来必将是一个纷争加剧的时代。现实状况证明了您的先见之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无疑分歧加剧了, 甚至有人认为是更加分裂了。您觉得,立足当下的时世,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H: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正如我在最近的《全球离心力》(Globale Fliehkr fte)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我在书中声称的本世纪的黄金四等分之一(1991-2016年)已经结束。但自从乔·拜登接替了有史以来最灾难性的美国总统,并且宣布美国将彻底改变其气候政策后,我感觉稍微乐观了一些。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具体的环保问题。在现实情况下,保护动植物、保护环境的过程很容易触及当地居民正常的生存权利。要让野生动物与当地居民相安无事,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谐的生态环境,那么,就不能对当地人忧心的问题视而不见。解决问题从来没有简单的方法,总归需要采取综合手段。让当地社区全面参与规划、实施管理,生态保护工作的成效可能会更持久。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些成功的案例可以分享吗?
H:显然,我们必须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之间进行调和,而这确实应该通过与受影响的人协商来进行。但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认识到,更简单的生活方式更为崇高,最终它不仅会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更好的地球,而且,比起世界正在走向的普遍消费主义,极简的生活方式也会给我们带来更为持久的快乐。
要让生态保护能够持久、形成机制,就很大程度上要让大家都参与分享环保红利。这方面欧美似乎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H:我曾两次在圣母大学教授生态哲学,第一次是在本世纪初,第二次是在2019年。学生们的态度完全变了——从对“绿色思维”的敌视到热情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的年轻人明白,如果不彻底改变,不只是他们的孙子孙女,就连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也会越来越受到生态危机的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书中多处谈到中国古典智慧对您的启发,也专门为本书的中文版撰写了序言,而且,《生态危机的哲学》就是以庄子的故事起头的。您也提到,生态危机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现代性必然结出的恶果。但并没有像海德格尔这位同样爱好庄子的哲学家那样全盘否定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
H:是的,我喜欢庄子! 但我不是一个寂静主义者——我们不能让事物简单地流动,而必须行动,有时是为了让事物重新自然流动。为了负责任地行动,我们需要海德格尔不喜欢的科学和技术——但我们必须用强有力的伦理学来弥补科学和技术带来的缺憾。海德格尔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握住现代性的进展背后的积极的道德理由,比如对正义的渴望。
译者序
文 | 邢长江
关注自己所处的周遭世界可谓是人最为基础的本能之一,人们都会随时关注环境,并且及时对周围的变化做出回应。而生态环境,是全人类不得不共同面对的一个“周遭世界”和“环境”。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共享大循环中互相连通的水源。生态环境的变化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宿命。而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是由此带来的生态危机,都逼迫着我们必须给出积极的应对。
确实,全世界范围内的环保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各国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并努力贯彻,人们也日渐意识到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但是不得不说,仅在生态领域做出这些现实的、具体的改善又很不够。众所周知,随着生态、环保的实践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棘手。事实上,甚至产生了更多的迷茫,引发了更多的猜忌:我们真的面临生态危机吗?我们有必要改变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吗?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真的有效吗?环保实践的合理性何在?这些都是我们在试图保护生态环境时通常会面对,也确实需要回应的质疑。否则,对生态危机的一切现实应对都只能是盲目的,只不过是诉诸人最基础的本能。
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生态危机的哲学”的理念是必要的。因为哲学正是在关注周遭世界的基础上,才能深入地做整体性的理性反思。它从根本上能够补足生物本能和现实行动的缺失,能够对后者起到引领作用。这本《生态危机的哲学》就有志于做这种有意义的哲学回应。
本书的作者是著名哲学家维托利奥·赫斯勒教授。赫斯勒教授年少成名,与伽达默尔、阿佩尔和汉斯·约纳斯等著名哲学家皆有深厚交往。从个人特征上看,赫斯勒接续了德国哲学厚重大气的传统,自觉把柏拉图、维科、康德、黑格尔等大家的哲学主张化作自身的思想资源,是当世少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学术大家。我曾经有幸跟随他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常见他拿着希腊文的古代作品边读边译,也曾在芝加哥美术馆中听他侃侃而谈,因此长久以来都希望能向中国读者介绍他众多的哲学著作。但是没有想到,一天上课前,他送给我一本亲笔题赠的《生态危机的哲学》,并表示期待我能够把它译成中文。他告诉我,相比于其他纯粹形而上学的皇皇巨著而言,他更加看重这本篇幅不大的作品,因为它代表了哲学这种象牙塔中的学问对现实世界的关怀,是一项更加紧迫的事业。
《生态危机的哲学》是赫斯勒 1990 年受苏联科学学术研究院哲学所之邀到莫斯科所作系列讲座的合集。为回应当时俄罗斯面临的历史剧变,在讲座的开篇,赫斯勒并没有直接切入生态问题的讨论,而是深入分析了“冷战”后世界的政治现实。随后他又把这一主题提升到哲学反思的维度,并提出警示:一切以政治为指归的思考方式本身是成问题的。它自动屏蔽了政治困境之外更为急迫的议题,即生态问题,从而有意无意间回避了生存论和价值论层面人类必须遵守的责任。
赫斯勒在讲座中还进一步探求人类沉沦到深重的自我毁灭困境中的思想根源。在他看来,眼下的生态危机并非一个尴尬而又可以侥幸避免的现实问题,而是一个根植于现代性文化逻辑之中的思想事件。现代性的经济发展和资本逻辑之所以会把自然看作异于人的对象,它导出的消费主义之所以会得到无条件的认同,是因为现代性的根本逻辑在于自然与人之间的二元对立,主体性被放在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赫斯勒指出,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从整体上看待世界,在于我们如何思考。
针对表现为政治乱局和生态危机的现代性难题,赫斯勒希望做出一个非常哲学化的观念论的解答。遗忘、放纵和沉默、压抑都是非哲学化的生存方式,而哲学的本质在于迎难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应从思想的根本的维度出发来重新寻找适合的方式,以此调整自己的行为。未来,必须从根本上使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最终需要达到的目的是人的思维和行动都被置于整体性的视野之中,进而使人类全部的生活世界都与“存在的整体”(das Ganze des Seins)同构,而不被破碎的视界和偏执的兴趣所割裂(本书第ⅩⅤ页)。赫斯勒暗示,相较于思想上的退缩和复古,他的客观观念论(objektive Idealismus)是一种更好的对待传统的方式:一方面它与现代流行的主观观念论不同,它不认为真理和实在仅仅是我们个人主观设想和构思出来的东西,而认为它们是客体和自然向人的呈现;另一方面,客观观念论又不同于任何一种前康德的独断论形而上学,它主张客观和自然呈现在一个自我反思的、人类精神逼近自然的观念论进程之中。因此,就这两端而言,在客观观念论的内部,主客观之间、“天”与“人”之间能达到统一。值得注意的是,赫斯勒认为他的这种思路与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有高度的契合之处。比如,书的扉页上就全文引用了《庄子 天地》中“子贡南游于楚”一节,提示了整体的自然观对“机心”的超克是回应生态危机的关键。再比如他一再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古人没有发展出现代的量化思维,并非因为他们的智慧不够,而是因为其朴素的天人合一的整全世界观。
当然,赫斯勒本人并不愿意成为把所有现实问题都回溯到形而上学的“纯粹哲学家”。相反,在后面三次讲座中,他依据客观观念论的体系蓝图,在现实政治安排、法治配套和社会建构等方面都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他谈到面对生态问题时,精英和大众扮演的不同角色,谈到领袖的魅力和号召力在实务中起到的作用,也谈到较高层次的法益和较低层次的法益之间的权衡问题。而这些都使得他的思想变革的构想颇具现实关切。
毫无疑问,赫斯勒的《生态危机的哲学》的整个论证过程经历了一条相当迂回曲折的思维路线:从现实政治到生态问题,从生态问题到哲学思辨,从哲学思辨再回到现实政治。这种奇特的迂回使本书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关注环保议题的著作,也使它与教授本人的其他作品呈现迥异的风格。这一方面说明了,在现代社会这个各种因素深度交融的关联系统之中,任何类似生态危机这样的单独的社会议题都离不开与之相关的一连串其他事务的参与。另一方面,赫斯勒也通过这种方式示范了“何为整体性思维”——当代人必备而又极为稀缺的思维能力。他指出,相对于生态危机,更为危险而又急迫的危机是我们知识体系的危机。现代性的学科建制的一大特征就是条块分割、层层叠叠,这使得知识分子不仅难以自如地面对眼下的这个成体系的庞大威胁,而且会消解依附于这个过分精巧的学科建制之下的每一个人肩膀上的道德责任。回看当代的古典学和人文学科的教育,又过度沉溺于繁文缛节、考据雕琢,所以更加不堪大任。
赫斯勒甚至呼吁人们注意,“生态危机的哲学”本身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今一切学科的新理智门类,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长时间培育的跨学科、成体系的学问。由此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赫斯勒最初用一把锥子点破当下迷雾中的种种危机和幻象,但最终他又展开一张挂满扣结的理性主义的大网,让人耐心求解。
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哲学的认识,以至于当我翻译完全书,坐下来重新省思的时候,能够更加理解赫斯勒教授的人生旨趣。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赫斯勒教授在学院中都是一个令人钦羡的天才、学术传奇:在 21 岁,当大多数同龄人刚刚获得学士学位的年纪,他却凭借哲学、古典学和梵文领域的初步成果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黑格尔的体系》至今仍旧是黑格尔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他在圣母大学校刊的访谈中曾坦言,求学过程中他考虑过中途放弃,转而去做医生或律师。因为他和大多数哲学求学者都发现,当代哲学越发成了一种求生的技艺,它主动放弃了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也放弃了提出和解答急迫而又宏大的问题的权利和责任。赫斯勒最终仍旧选择继续从事哲学工作,是因为找到了他追求的学术志趣,即广泛地了解世界,去治疗和求证— 为了他潜在的“患者”和“法律委托人”。在这个意义上,他真正实践着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种对待哲学和人生的态度,在我看来是值得追随的。
很想念每次课后与他一起步行回家时的“闲谈”。
邢长江
2021 年 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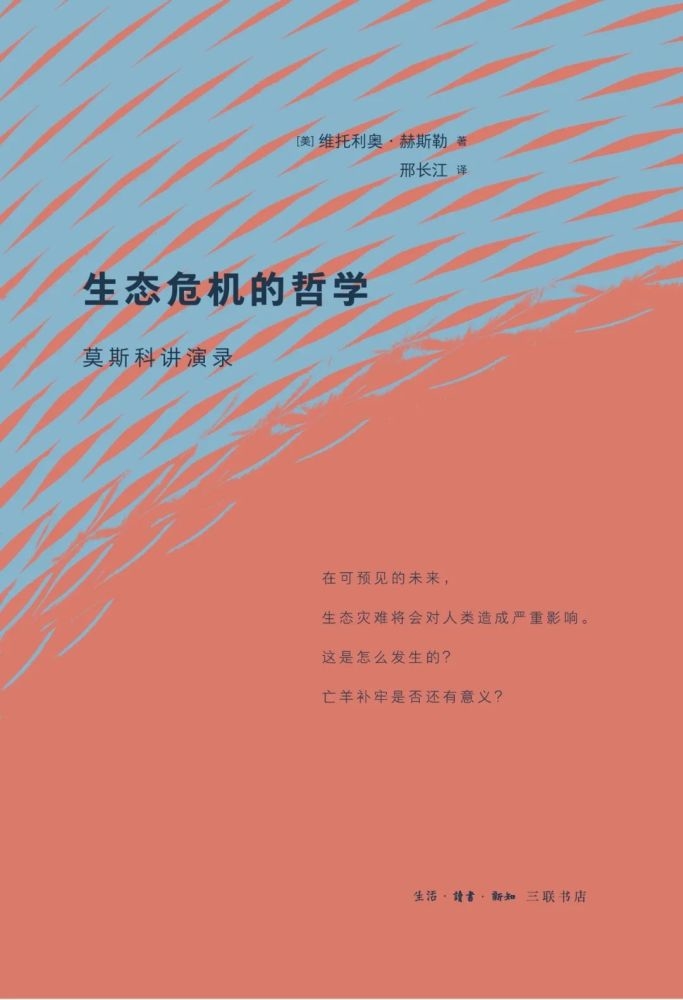
生态危机的哲学:莫斯科演讲录
[美]维托里奥· 赫斯勒 著 邢长江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