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让-吕克·南希:向着不确定的未来敞开
 2021-08-30
2021-08-30

当地时间8月23日,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去世。作为一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的去世也在国内掀起了波澜。不少学者和思想文化类平台都发表了悼念文章,或刊登了南希的译文以示怀念。然而,对普罗大众而言,南希的名字或许仍显陌生。人们固然也会为他感到惋惜,却很难意识到这样一位哲学家的去世与自身有何相关,更难以理解他所思考的“独一复多”“共通体”等话题为何重要。
注意到这样的落差,本期文章希望提供一段较为简短而通俗的介绍,让普通读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南希的思想理路和概念构成。本文无意成为一篇详尽的“思想传记”或研究性论文,笔者仅是希望,此文能让大家多少了解南希为我们贡献了怎样的思考,为且何他能凭借这些洞见成为一名值得怀念的思想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家可以因思考而不朽,而如若他的思考得到大众理解并进入他们的生活,或许其生命也就在大众中得以延续。

让-吕克·南希(1940-2021),法国当代哲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代表作有《无用的共通体》《素描的愉悦》《缪斯》等。
南希的思想脉络与主要论题
对于一位哲学家,在深入其思想体系前,人们往往倾向于先了解他所处的思想脉络,并大致掌握他所思考的主要话题与立场。而对于南希,我们的介绍同样可以从这些内容开始。
许多学者都曾为南希的思想历程划分阶段,一种较为普遍的划分方式大致如下:在70年代,他所进行的工作主要是评论性的,他经常和他的同事兼朋友——拉库·拉巴特一起对一些经典哲学家进行评述。在这段时间,他的评述对象涵盖了拉康、黑格尔、康德和笛卡尔等人。自80年代以来,他开始围绕政治与社群问题展开思考,其富于独到洞见的工作越发增多,也日渐声名远播。如令他名声大噪的《解构的共通体》即完成于这段时间。在九十年代,南希主要探究本体论、感觉的构成等问题,这段时间出版的作品对于理解他的思想体系尤为重要。同时,南希之所以能被广泛视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重要哲学家,也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这些作品。在90年代中期,南希发展了他对艺术和美学问题的思考;最后,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他还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基督教的研究。
如何定位南希在思想史谱系中所处的位置?这一问题涉及到哪些思想家对他的思考产生了关键影响。对此,不同学者的处理方案也有所不同:新泽西州立大学的学者哈钱斯(Hutchens)曾列出一长串名字,认为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巴塔耶、布朗肖、拉康和德里达都在南希的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剑桥大学的伊恩·詹姆斯(Ian James)则提到了海德格尔、布朗肖、列维纳斯和德里达。在这些名字中,海德格尔的重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人们普遍认为他极大地影响了南希哲学思考的总体特征和发展方向。更有甚者,有人称南希为当代的“新海德格尔主义者”。
据统计,截至2006年,南希已经发表了超过53部的著作(含合著)和四百多篇各类文章。对于如此卷帙浩繁的作品,学者们也曾尝试将其归入几个主要话题。在《新法国哲学(The New French Philosophy)》一书中,伊恩·詹姆斯就曾作出这样的尝试,他将南希论及的主要话题及其立场归纳如下:(1)南希试图以“共在”(co-existence)和独一复多(singular plural)的方式思考存在问题,形成一种独特的本体论;(2)他提出主体和主体性的问题,拒绝“在场”主体,强调主体的“缺席”;(3)他认为身体的接触构成人们把握世界的原初形式,先于概念性的认知,也先于任何符号意义;(4)最后,他也基于上述理念对政治、艺术和宗教等领域展开了思考。而哈钱斯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提出了两条论题,认为它们构成了理解南希哲学思考的主要线索:(1)南希哲学的主旨在于,探究并捍卫“独一性”(singularity),他希望这种“独一性”能免于实体主义(substantialism)的侵蚀,后者倾向于从普遍性和本质性的角度看待独一性。(2)其次,南希认为,仅仅在多元性中,独一性才是可想象的和可理解的。

James I. The new French philosophy[M]. Polity, 2012
无论是哪种策略,它们在帮助我们理解南希的同时,也涉及到了大量令人“不明觉厉”的论题和概念,而对这些它们作出解释和澄清,进而开辟理解南希哲学的进路,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
南希的本体论:
不可还原的独一性与面向多样的敞开
我们不妨从南希对主体和主体性的论述开始。在这一问题上,他的思考方式与海德格尔明显相关。对此,杰弗里·利布雷特(Jeffrey.Librett)曾在南希《肖像画的凝视》一书的英文版导论中进行过简要概述:
按照利布雷特的叙述,在主体问题上,海德格尔提供了“最强的反笛卡尔主义”。依照笛卡尔的主张,心灵的本质是思维,这意味着主体具有某种恒定的本质,且这种本质是“自我确定”的——即便外部世界全然不存,主体在自我反思中的存在也无可置疑。因此,它不依赖于任何外部条件。然而,笛卡尔主张的,主体的“本质性”和“内在性”都遭到了海德格尔的质疑。在后者看来,生命是“事实性”的,这意味着它是特殊、具体和偶然的,而不具有恒常的本质。同时,生命是“在世”的,它处在一定的语境之中,并且在时间中展开,有自己的历史。在展开的过程中,主体也具有“世界性”:这种世界性是由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以及主体与他人的关系("与人相处")中进一步构成的。因此,不同于笛卡尔,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主体的时空性和关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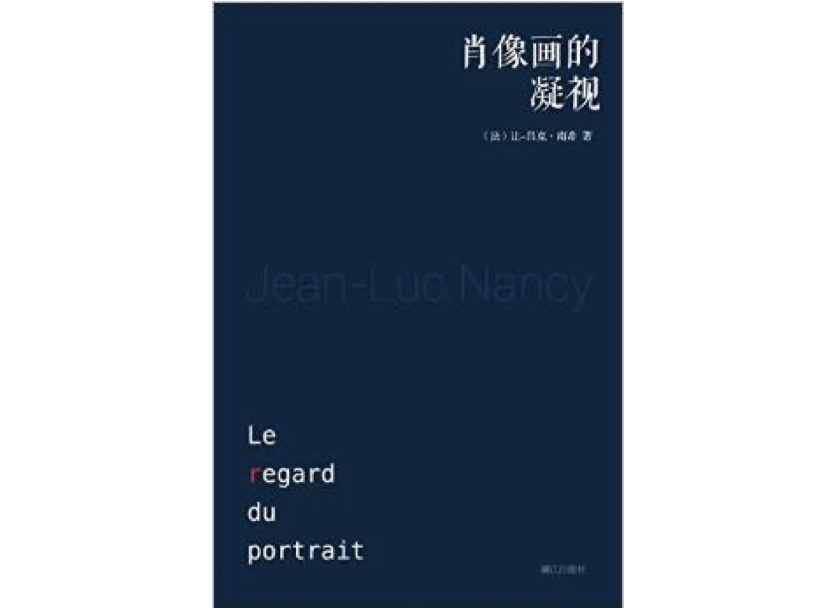
《肖像画的凝视》,[法国] 让-吕克·南希著,简燕宽译 / 张洋校,漓江出版社2015年。
和海德格尔一样,南希也坚持主体的时空性和关系性。但他更进一步,将自己的主体设定为一种“缺席主体”,这一观念带有列维纳斯和德里达的痕迹,与“在场形而上学”相对立。而“在场形而上学”即是强调事物的“本质”可以通过事物得以显现。德里达对此曾有过十分经典的论述:当我说话时,我力图让我说出的话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我的思想和运营在我观念世界中的概念。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的言语指涉概念的“在场”,概念就成为了那个通过事物得以显现的本质,而且语言和概念实现了同一。而“缺席”则意味着人们无从找到事物背后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他者”的踪迹隐含在主体之中,主体必须一直暴露在他者面前。例如,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语言表达常常“词不达意”或“言不尽意”,在这种情况下,概念在语言中“缺席”了,语言的意义被其他听到的人赋予。在南希的语境下,主体的处境也是如此,主体面向他者敞开,甚至由他者构成。
这也使得南希在他者问题上比海德格尔更加“激进”。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多少还抱有 “自我”和“本真”的概念。例如,他区分了“真实性”和“非真实性”。真实性与“我所有性”相关,指的是以第一人称方式被揭示的东西。就像许多电影刻画的一样,主人公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决定“做出自己的选择”,去探寻自己的内在,寻求发自内心的规范性力量。而南希则完全放下了这种“英雄主义的孤独”,全然向他者“敞开”,彻底反叛了在场形而上学。
这种对在场的反叛使得南希对主体的思考别有特色。南希的主体是“有限”的主体,因为它时刻被自身的时空性和关系性所“限定”,而不像笛卡尔的“我思”主体一样免疫任何外部限制。这种“有限性”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由于主体在任何时候都是具体而特殊的,所以它永远无法被任何形式的普遍性所抽象和归化。另一方面,主体的有限性也使得南希格外强调“身体”的角色。在他看来,身体是“有限性”的最好体现:身体具有鲜明的时空性,被限定在特定的时空和位置关系中。因此,身体所受的限制最好地说明了主体所受的限制——主体与世界的一切联系都源自于身体的经验和感觉。但同时,南希并没有被封闭在有限性中,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论述的,他仍然认为主体是“敞开”的——换言之,主体永远超越自身,暴露在他者面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体有无限的可能。正如夏可君教授所评论的:
“南希一方面承认个体的“独一性(singularity)”以及独一性向着其它独一者的偏斜性运动,而不是个体性(相对于特殊和普遍性,可以被层层归化的),即另一方面也认为,独一者也是超越自身而“共在”的,而且共在是先在性的。”
与此相关的,在南希本体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个概念是“独一复多”。利布雷特曾举例阐释这一概念的内涵:他说,人们在欣赏每一种艺术时都在调动某个“独一”的感官,如在欣赏绘画时调动视觉,欣赏音乐时调动听觉……但在每一种感觉的成功调动,实际都潜在地涉及到了其他的感觉,并以对其他感觉的调动为基础。举《琵琶行》中的诗句为例:“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可以形容琵琶的声响,但这一描述同时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若再深究,诸如“破”和“迸”这样的语词往往也需要通过触觉来理解。因此,纵然感觉是“独一”的,但这种“独一”中也充斥着他者的踪迹,向着多种多样的,其他类型的感觉无限敞开。
简言之,在南希看来,“缺席”是对存在的重要规定,这种缺席使得存在面向多样性和差异的他者无限敞开,如此构成的单一性也无法被任何普遍性和本质的逻辑所同化。

让-吕克·南希。
本体论的政治面向:解构的共通体
南希在涉及政治、宗教、艺术等领域的作品中都坚持了上述基本观点。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可以以南希论及政治的代表作——《解构的共通体》为主要探讨对象,以窥见其将本体论论题延伸至其他领域的尝试。
南希的“共通体”以“共同体”为对立面和批判对象。在他看来,共同体的逻辑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体现。他认为黑格尔的共同体理论是“内在主义”的。即是说,黑格尔为他的共同体赋予了本质性的规定,并认为这种本质内在于共同体之中。换言之,这种哲学就是在场形而上学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在《法哲学原理》中,共同体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演变,这一过程无非“一个通过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本质”。这个内在本质发展与展开的过程也就是“总体化”的过程。“总体化”的过程会同化与统摄一切特殊性,并将它们整合进总体化进程之中。例如,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仍是具有特殊利益的个体,但“国家”会在普遍性的意义上统一每个个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性。由此也不难看出,对组成共同体的人来说,他们也被黑格尔设定为同样具有内在本质并力图实现其本质的个体,而个体本质的实现恰恰就是在代表了普遍性的共同体。

《解构的共通体》,[法]让-吕克·南希著, 夏可君编校 / 郭建玲,张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人们从“内在主义”的逻辑中最终导出的是对“外在”的拒斥。首先,对于共同体而言,任何不符合其本质,进而无法被其同化的个体都会被排斥在外。其次,对于共同体中的个体而言,由于被设定为具有完全内在的本质,他们也无需与外界和他人产生联系,因而具有一种“人对人的绝对内在性”。南希认为,这一逻辑最终导向的结果是以纳粹为代表的“极权主义”。而这恰恰是人们所希望建立的共同体的对立面。
面对“共同体”和“极权主义”之间的纽结,南希试图用“共通体”的概念来拆解“共同体”,进而打开这一死结。有学者用两个概念来阐释“共通体”的意涵并彰显其与“共同体”的差异,那就是“共在”与“绽出”:通过用“共在”来界定个体存在的基本状态,个体被规定为一个关系性的概念,进而挫败了“内在主义”所主张的,内在本质的自我实现。“绽出”则与前文所说的“缺席”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指的是“自我意识对自身的超越”。换言之,个体不是自我同一的个体,而是超越了自我,隐含了他者的踪迹。正因这种“绽出”,南希的“共通体”和共通体中的个体不会像黑格尔的“共同体”一样封闭在内在本质自我实现的框架之内,而是始终对外界保持敞开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南希的共通体“乃是始终通过他人并为了他人而发生的共通体。”
最后,不妨以哈钱斯的评论做结:“也许南希正召唤我们进入一种无法预期的开放性,在这种开放性中,无论你对即将到来的惊喜做了怎样的准备,其所带来的惊喜也永远无法被你的准备消除。在这个世界上,不确定和开放性才是人类处境中的决定因素。”如今,人们越来越能对这种“无法预期的开放性”感同身受: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稳定,变动不居似乎成为了当代唯一不变的真理,面对眼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性图景,南希的思考或许可以为人们拥抱时代提供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