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春声:运用“区域”这个概念时,我们不能画地为牢

韩江是中国东南沿海主要的河流之一,其上游是分别发源于广东紫金县(明永安县)的梅江和发源于福建宁化县的汀江,两江在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汇合后始称韩江。自梅江源头至下游东溪口入海,全长470公里。韩江流域面积30112平方公里,加上不在其流域之内,但自然地理学家将之归入“广义的韩江三角洲”的榕江揭阳以下、练江普宁以下的平原部分,共约31760平方公里。韩江流域位于粤东和闽西南,北面的武夷山杉岭背斜是韩江、赣江的天然分界线;南面以阴那山及八乡山地构成韩、榕二江的分水岭;东面由凤凰山脉与独流入海的黄冈河分隔;其西部则为不大明显的台地与东江分水。
韩江流域的地势自西北和东北向东南倾斜,山地占总流域面积的70%,多分布在流域的北部和中部,一般高程在海拔500米以上。丘陵占总流域面积的25%,多分布在梅江流域和其他干支流谷地,一般高程在海拔220米以下,梅江上游与东江流域分水岭高程则仅157米,成为东江、韩江流域易于沟通的地点。平原占总流域面积的5%,主要在韩江下游三角洲,一般高程在海拔20米以下。
韩江上中游地区多山地丘陵,目前主要为讲客家话的人群聚居,韩江下游的三角洲平原,其居民则以讲“福佬话”(20世纪50年代后称“潮州话”)者居多。
关于各历史时期韩江流域的人口数量尚无可靠统计,大致说来,19世纪初该地区被官府登记的户籍人口超过了520万。其时官府户口登记的是“保甲烟户数”,“督抚饬所属按保甲门牌册实在民数,岁以十月同谷数造册送部”。这一做法的可靠性取决于州县官员负责任的程度。就广东的情况而言,该时期的人口统计仍然带有主观推测的成分,但比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前的编审数要可靠得多,应与实际的人口数更接近一些。
在明朝末年,韩江流域共设有21个县,其中包括广东省潮州府全府的11个县、惠州府的3个县以及福建省汀州府的6个县和漳州府的1个县。
本书讨论的“韩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包括表一所列属于广东省的各个县份,个别章节也会引用与福建省平和县和永定县相关的资料。
尽管从秦代开始,中原王朝就一直在韩江流域实行着有效的行政管治,但该地区基本上过着“化外之民”生活,居住于崇山峻岭之中,被称为“畲”和“猺”的人群以及生活于江河水道和沿海地区的疍民及其他水上居民,仍长期普遍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畲、猺、疍和其他未编入户籍的人群,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经过一系列充满矛盾、复杂曲折的与朝廷和官府的互动,逐步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接受朝廷制度和官府管治的过程,地方上广泛流传的许许多多这类有着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生动故事,构成了韩江流域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
明代中叶以后,韩江中下游地域社会进入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与包括“倭寇”“海盗”“山贼”在内的一系列地方动乱事件相联系,这一时期地方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聚落形态发生变化并出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以宗族组织和民间神祭祀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重新整合,户籍和赋税制度也有重大变化,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出现新的内容,乡村社会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变动。在传统地域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因应时局变化而采取的举措,最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地域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上活动也是本地文化传统中最具有长远历史根源的重要内容。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并以此作为重要的生计来源。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揭示的,即使在朝廷厉行“海禁”的明朝和清初,该地区民众的海上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有明一代直至清初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里,海上贸易一直被视为违法活动,康熙二十三年(1684)发布的“开海令”对本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其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出海贸易的生活方式,又成了具有合法性的行为。该地区因而成为清代东南沿海重要的近海帆船贸易基地。由于清政府奖励本国商人从海外贩运粮食入口,以及开放捐纳监生的政策,对于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百姓来说,从事海外贸易不但可以解决生计问题,发财致富,而且还可能因此获得功名与顶戴,改变社会身份,提升社会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韩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趋势,成为当时中国商品货币关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从而也成为最严重的依赖外来粮食输入的区域。与社会财富积聚同时发生的,是乡村宗族组织空前发展,民间庙宇系统整合加强,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重新调整且逐渐稳定,乡绅和商人阶层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明显增强。
近代以后该地区向“侨乡”的转变最为引人注目,而这一转变又以汕头等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发展为中心。19世纪60年代汕头开埠以后,韩江中下游地区民众悠久的海上活动的传统,明显地帮助了本地人向海内外的移民及其社会网络的发展。无论如何,民国年间已有许多观察者视韩江中下游地方社会为中国受海外移民影响最明显的地方之一,后来又有不少研究者以“侨乡社会”或“侨乡文化”之类的词语来表达对该地区社会面貌的理解。
不难发现,所谓“侨乡文化”,不仅表现于百姓的日常生计对华侨汇款的依赖,也不仅仅反映于华侨对故乡工商业的投资,更重要的是通过地方社会权力格局及其“合法性”的变化表达出来。具有跨国活动性质的华侨商人,在许多方面起着与传统时期乡绅类似的作用,在侨乡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侨乡”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建筑或文化“景观”,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生活的方式,它更重要地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地方的文化传统,在“侨乡”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若将上述进程置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中考察,有经验的研究者不难发现其学术意义。20世纪初以来,已经有许多前辈在与韩江流域历史文化相关的学术领域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其中也包括罗香林教授和饶宗颐教授等学者卓越的贡献。
最近三十余年,由于地理、人文、政治、经济和海外联系等多方面的缘由,从事韩江流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有许多人被自觉不自觉地划归所谓“客家学”或“潮州学”的范畴。
可以不太夸张地说,在近百年来关于中国区域社会历史林林总总的研究之中,有关韩江流域的研究,应该说是学术积累较为深厚、工作基础较为扎实、研究成果较为系统的领域之一。笔者因为各种机缘,也有许多机会参与到这些颇具方向感,且其独特的内在脉络正在逐渐形成的学术努力之中,从各位前辈和同行的研究中获益颇深。本书的工作,亦可视为这些具有长远意义的工作的一部分。
笔者和国内外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行,近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区域社会历史的研究,这一具有“历史人类学”取向的学术努力,也常常被称为所谓“华南研究”。我们希望能通过一系列对具体问题、具体事件、具体人物的描述,通过村落的、社区的、个案的研究,来表达在长期研究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区域社会史的一些基本理念。
通过对韩江中下游地域社会的研究,笔者逐渐体会到,“区域”在社会史研究的层面,是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被运用的。在运用“区域”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画地为牢,只是在一个有固定边界、很确定、很僵硬的区域里边,用某种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甚至只是读中国通史教科书获得的思想框架,去考虑问题。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笔者努力尝试通过具体历史过程和历史故事的描述,来展现和表达以下若干观念。
首先,“区域”的界定应该与人的活动和认知相联系。
把“区域”理解为一种分析的工具,其实就是要把“区域”与“人”联系在一起。社会史是思想着、活动着的“人”的历史,当“区域”与“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区域”这个词就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尤其不是可以用中学地理教科书的定义去理解的概念,而应该被视为一种与人的思想和活动相关的思考和分析场域。这样的表达比较符合我们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初衷。
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研究者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人的活动,即拥有某种地域认同的人群活生生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在某个地方发生过的事情。而人群是一直在流动着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地理边界也不能是僵化的,而应该是流动着的,我们研究的人群到哪里,区域的边界自然也就延伸到那里。
我们知道,在上千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韩江流域居民的族群认同、社会身份、生计形态、交往与聚居方式一直变化着,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更有着与生俱来的海上活动传统,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对“区域”的理解与界定。
例如,近代以后韩江中下游的许多地方被视为“侨乡”,我们在这些地方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本地人不时会讲到,本地人口是多少,但在国外还有多少乡亲,而且在外的人数似乎常常不比本地的人口少。这就提醒我们,实际上我们所研究的“区域”已经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可能需要更多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海外乡亲”们移居的国度与地区。
但与此同时,也得认真地考察一下,所谓的“海外乡亲”是如何被定义出来的?我们关注的这个地区的百姓移民海外后,世代更替,子孙繁衍,婚姻关系错综复杂,可能本地人提到的“海外乡亲”,或者具有四分之一本地人的血统,或者只有十六分之一本地人的血统,甚至更少的血缘的比例。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来说,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些流动的人群时,更重要的应该不是关注他们的血缘,而是关注其地域身份认同,即他们是不是仍然认为自己是“潮州人”或“客家人”,是否参加海外潮属社团或客家社团的活动等。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区域的“界定”要与人的活动及其认知相联系,在本质上,讲的是要与研究对象的身份认同相联系。
其次,“区域”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
在一般的意义上,研究区域社会史,似乎就是在研究一个地域空间的社会结构,但我们还是要明白,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空间结构是很长时间历史积淀的结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传统”“文化”“习俗”都是人的创造物,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因为其“意义”,而得以存留了下来。正因为如此,后人所看到的各种文化景观、许多所谓地域的“文化特质”、多彩多姿的民间习俗及其传说,其背后一定存在着时间很长的、复杂纷繁的被创造出来的历史过程。
以韩江流域为例,正如本书所力图揭示的,为本地百姓和众多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已经成为“风俗”或“文化遗产”重要内容的地方信仰传统、乡村聚落形态、宗族组织活动、民居建筑形式等,以及被学者、媒体和文史工作者归纳出来的“潮州文化”或“客家文化”的诸多特质,都是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不再相信有亘古不变的、天生的所谓“文化特质”的存在,而是要求研究者努力“还原”实际的历史过程,即努力把共时性的空间结构(包括思想的结构),还原成为历时性的历史过程。如果能够把这种历史过程揭示出来,一个区域就会自然而然地呈现自己的脉络,对于所谓区域“特质”或“特性”的描述,也就能够建立在比较有系统、有历史根据的基础上,而不是过多地凭着研究者一时的聪明去建构。这就可能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的专业特长、思维习惯、学术禀赋与性格特质提出新的要求,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还原”区域社会空间的历史过程,成为一种带有“解构”意味的学术工作。
再次,“区域”必须有其发展脉络与内在运作机制。
我们做区域社会史研究,其思维建构过程和学术表达方式,有点像是在讲一个很长的多条线索的复杂故事。而一个区域可以成为“故事”的单位,关键之处,在于研究者应能够发现区域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运作机制,而且,依照专业的规范,这样的发现必须是能够自圆其说的。社会历史过程实际运作的机制,不是研究者借着几分聪明,根据既有的理论框架或教科书模式,就可以居高临下地遵照逻辑规则去推导出来的。
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言,“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我们要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和体验,若是生活在历史时期,作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要办成某一件事,或面对某一种特定的场景,该怎样去做?或者自然而然地会怎样去做?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上,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行为、具体的细节是理所当然必定要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有自己思想和意志的人做出来的,每一项制度都是人的创造物,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想要具体地做成某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善于利用其所居处社会中某些很具体的、可操作的机制,有其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环境。
明白了这些运作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也就揭示了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本书旨在描述明清时期韩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历史变化过程,不如说笔者更加关心的是影响和约束这一过程的制度和文化环境的演变,由此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脉络和运作机制。
因为人文学者的学术传承和专业背景可能影响其构建“历史故事”的过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区域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很可能更多地展现为一种学理上的脉络。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史分析工具的“区域”,实际上带有明显的主观建构的性质。也正因为这样,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强调历史学家的研究“学有所本”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学者,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里面,我们讲“故事”主要不是讲给当地的父老乡亲听的,更重要的是让学术界的同行能够听懂,我们的研究要能够回应自己学科的核心问题。本书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历史人类学”学术取向,在丛书的总序《走向历史现场》中,笔者已经力图较有条理地表述“华南研究”群体的师承关系与学术思考,以及期待自己的工作“能够成为一个有着深远渊源和深厚积累的学术追求的一部分”的愿望,这里就不赘述了。
又次,“区域”可视为“国家”话语的具体表达形式。
毋庸讳言,对于习惯以“国家”作为研究单位的历史学家来说,宣称自己所做的是区域性研究,其工作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与同行们习惯理解的“国家”有所区隔的某些意涵。但我们还是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关于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国家的权力和使用文字的传统深入民间社会、具有极大差异的“区域社会”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的国度来说,区域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在其百姓成为“编户齐民”的过程中,都逐渐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了文化上的“根源”,并且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了具有“合理性”的解释。
正如本书所描述的,明清时期韩江中下游地区民间信仰传统的转化,以及同一时期发生的士大夫与读书人对诸多地方风俗习惯的重新解释,都反映了类似过程的普遍存在。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实际上蕴含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
要贴切深入地理解传统区域社会,既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都真正置于区域社会实际的历史场景之中,具体地体验历史时期当地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力图处在同一场景中理解过去,还要求研究者认真仔细地考辨、解读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熟悉、真切地了解王朝典章制度的规定及其变化。在思想方式上,面对着具体的历史过程与研究对象,切不可把“国家-地方”“全国-区域”“精英-民众”之类的分析工具,简单地外化为历史事实和社会关系本身,更不可以“贴标签”的方式对人物、事件、现象和制度等做非此即彼的分类。
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思路,即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实际上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的巨大的时空差异为前提的。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和其他读书人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在区域社会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地,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明白了这一点,才算在认识论意义上明了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最后,“区域”的界邻地区往往自成一个区域。
依照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等不同学科分支的标准,我们可以在地图上以明晰的界线区分不同的“区域”。但如果将“区域”作为一种社会史的分析工具,考虑到人的活动和内在发展脉络的建构,就会发现,这些被硬邦邦的边界线切割开来的区域界邻地区,往往自成一个有内在历史脉络的“区域”。
以与本书讨论的区域有大范围交集的粤、闽、湘、赣四省界邻地区为例,就自然地理的概念而言,这片地域分属韩江、东江、北江、湘江、赣江、闽江和九龙江等不同的流域;依照政治地理的概念,近千年间这个地域一直分属四个不同的省区,即使按清代食盐专卖的规定,这里也被分割到粤盐、闽盐和淮盐等不同的“盐区”;而根据施坚雅关于传统中国经济区域的划分,这一带正好是岭南区、东南沿海区、长江主干区和长江中游区四大经济区的交会处。
就是在这个可依照不同的地理学原则,被切割成多个区域的地域范围,生活着一个有着相同语言、相近习俗和历史记忆,内部交往相当密切的人群——客家人,如果我们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这个人群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就不难发现,粤、闽、湘、赣四省界邻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难能可贵的社会史研究“区域”。
本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在闽粤界邻的沿海地区和众多海岛之间,由于明清时期同一海上活动人群的流动、交往与上岸定居,也由于他们与明清朝廷、官府和官兵互动过程所产生的许多具有共同特点的问题,实际上也呈现自成一个“区域”的某些特质。
近年许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论著,其研究的地理范围也常常是这类看来属于不同区域交界的地方。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如果能真正超越“核心-边陲”“陆地-海洋”“化内-化外”“域内-域外”之类带有二元对立性质的概念,就有可能更具有理论张力,更富于洞察力和同情心,更好地理解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逻辑。
笔者从事韩江流域社会历史研究近三十年,一直与“华南研究”这群志同道合的同龄学者一起,强调要重视普通百姓的历史及其日常生活,重视田野研究和对历史现场的体验,重视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努力超越地方史和地方文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努力接近对区域社会史研究应有境界的理解。
我们强调学术研究要志存高远,要有理论方面的雄心,要注意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的现象,重视为从事区域社会研究的历史学者提供建构理论模型的借鉴,在理论分析中注意建立适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实际情形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同时,我们又相信,在起步阶段,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区域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具体地域、具体事件、具体村落和具体人物的研究,来表达对历史整体的理解。
现在这本书,可以视为这一学术追求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本文为陈春声所著《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一书导言内容,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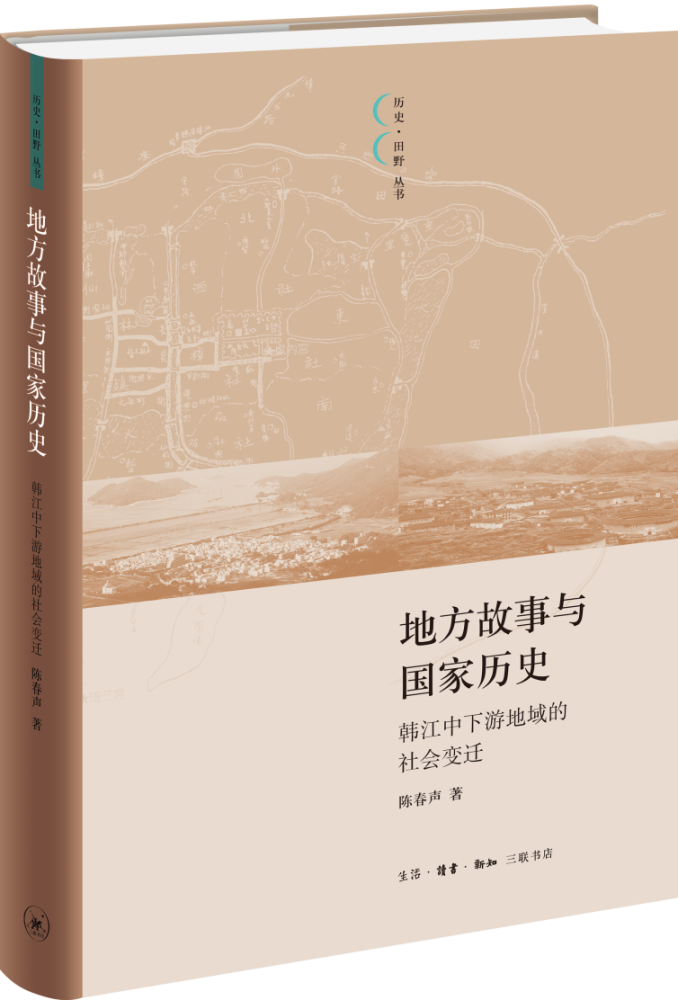
《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
陈春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6月
本书讲述了数百年间华南一条大江流经地域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及其社会组织变迁的若干故事,并试图以此反映作者对我们这个国家整体历史某些侧面及其相关机制的理解。对于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者来说,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直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书围绕着如何理解传统中国“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结合韩江中下游地域的历史,从天下、朝廷、官府和礼法四个方面展开了讨论。结合实际的生活经验,作者又考虑到一个更深刻、更根本的因素必须被关注,这就是“文教”。
此外,作者还指出了外部因素的作用,我们不但要了解中国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对传统上韩江中下游地区民众活动的周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贸易和金融制度也要有更深刻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