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性,“我”依然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独自一人
 2021-07-29
2021-07-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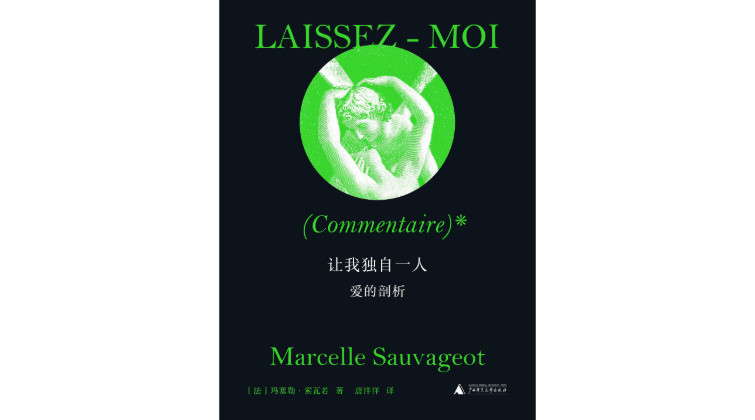
《让我独自一人》,作者:(法)玛塞勒·索瓦若,译者:唐洋洋,版本:一頁folio|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
一
有一点魔幻。正值一年一度的“520”,在某个培训班上,讲互联网的老师正充满激情地谈着“ 数字化城市”的未来;手机的朋友圈里一边是关于“躺平的时代”的热烈讨论,一边是各种各样的“520”商家文案;而我,在众声喧哗中读完了玛塞勒·索瓦若的《让我独自一人》。
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上,一般是找不到索瓦若的名字的,因为这是索瓦若唯一的作品。她于1900 年出生,1934 年罹患肺结核去世,其中差不多五年的时间都辗转在各家疗养院里,还没有来得及真正进入文学圈。有限的一点资料在不长的篇幅里就能说尽: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外省的中学老师,因为得了肺结核,后来不得不在疗养院休养,但是在住进疗养院的同时,遭遇了“被分手”,于是写下了这一部《让我独自一人》。确切地说,它并不是小说,而是四封从11 月到圣诞节前夜断断续续的“书信”——说是“书信”,只是因为它采取了书信的形式,而信中的“倾诉对象”正是让她遭受爱情打击的那个人。但同时,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因为她写下这几封所谓的信,并没有打算寄出去。因为这绝非她用来“挽回”爱情的祈求。
幸而索瓦若已经有半只脚跨进了文学圈,使得《让我独自一人》最终没有被埋没。她在巴黎准备大中教师资格考试的时候,交往了一众朋友,包括在那个时代显得极为先锋的超现实主义小群体。因为生病,也因为还保留些许古典的趣味,她最终并没有在超现实主义的标签下“出圈”;但就在她住在疗养院里,写下《让我独自一人》的时候,通过朋友勒内·克勒韦尔(René Crevel),她还能时不时听到一些有关超现实主义小团体的纷纷扰扰吵吵闹闹。理解了这种关联,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让我独自一人》中体现出来的对自由的执着和略显现代派的叙事手法。
因而《让我独自一人》没有遭受被遗弃的命运——尽管它来自“被分手”的疼痛。初版只印了163 册,在朋友圈内阅读,可过了一些时日,作者在弥留之际住进瑞士达沃斯的疗养院时,再版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索瓦若的朋友说服了批评家杜波(Du Bos)为知识出版社的这个版本作序,杜波甚至还去了索瓦若当时所在的疗养院,把自己写的序言读给她听。
达沃斯的肺结核疗养院里收留过很多文学家,早沃斯的肺结核疗养院里收留过很多文学家,早期有英国的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is Stevenson),稍晚一点有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 艾吕雅(Paul Eluard), 还有因为陪同患肺结核的妻子治疗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魔山》里弥漫着的忧伤的死亡气味,或许也算是给索瓦若的《让我独自一人》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注解吧,虽然索瓦若写下它的时候还没有住进达沃斯。索瓦若在杜波探访过后不久便去世了,并没有看到自己的书再版。从1933 年的初版到2004 年的最新一版,间隔了有七十年的时间。有意思的是,如果说索瓦若并没有进入文学史,这一部薄薄的、来自一个也算是默默无闻的——相较于波澜壮阔的法国文学史而言——“小女人”的,甚至还带有一点私密性的作品并没有完全坠入遗忘之中。自初版之后,七十年里又分别在1934 年、1936 年、1943 年、1986 年、1997 年出过五个版本,书名都沿用了初版时的“Commentaire”——直译过来就是“评注”,或者,如果针对的不是另一本书,而是某个事件,也可以对应汉语中的“记”, 算是一种“心得”——只是在 1943 年和 1997 年的版本中都加上了副标题:1943 年的版本加的副标题是“重现的纸页”,1997 年的版本加的副标题是“逝去的爱情”。的确,严格意义上来说“评注”并不能算是书名,它似乎更像是一个文本的品类:例如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翻译的时代》就是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评注”,他也的确在封面上标明了“un commentaire”。而恺撒的《高卢战记》用的也是“commentaire”一词,是记述,也是回溯,是解析,也是思考。2004年出版的版本不再沿用抽象的“commentaire”,而是选择了“Laissez-moi”(让我独自一人),将“commentaire”用作了副标题(在这一版的翻译中,被译作《爱的剖析》)。2004 年的新版在当年就卖出了六万册,似乎和开始不屑于爱情的新世纪的主旋律有些不甚相符。
的确,“评注”或者心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在爱情面前退后一步的女人,审视爱情结束前的过程。因为拉开了距离——当索瓦若在1930 年11 月7 日这封信的结尾处写道,“明天我会给你写信,我不能再用‘你’这个称呼,我会给你写信,但无法向你说出我在心里向你吐露的一切”,这个距离就已经真实无误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所以能够看清爱情,看清爱情中的(或者说爱情行将结束之际的)男人和女人。

《让我独自一人》外文版封面
二
看清爱情中的男人和女人之后,索瓦若得出的结论是:让我独自一人。让我独自一人是在两个层面上的宣告:第一个层面是爱情不再,“我”选择有尊严地独自一人,回顾并且正视自己的爱情,否则“我”曾经的爱情就失去了它全部的价值;第二个层面是,作为女性,而且是身患重病的女性,“我”依然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独自一人。
和所谓的情书不同的是,《让我独自一人》并没有呈现两个男女具体的恩怨情仇。没有故事,因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女主人公和人物。“评注”中的“你”、“您”和“我”都没有身份。除了间或闪现的“疗养院”“ 咳嗽声”“凡尔赛”让读者能够把书中的“我”和生活中的索瓦若联系起来,便再也没有其他与真实生活和真实经历的确切关联。而事实上,即便这些或许能够追寻的蛛丝马迹指向一个具体的人,指向一桩具体的爱与不爱,它们背后的具体指向说到底也是没有意义的。究竟是谁,是哪个“学院”里的哪个男人曾经爱过那个叫作玛塞勒·索瓦若的女人?又究竟为什么就暧昧地不爱了,写了信去,说是要和另一个女人结婚 ,说“我们依然是朋友”,这一切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要知道,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男人女人,在不爱了之后,都要冠冕堂皇地说,我们依然是朋友;是要知道,在爱情的迷雾褪去之后,清醒的女人看到的,是一个失去了光环的男人的样子。不是谩骂,不是怨怼,不是反击,而是简简单单的“认识”二字。当索瓦若说,“我很愿意失去理智,但也愿意把握失去理智的那一刻,不断探索意识的边界,直至失去意识。不应该缺席自己的幸福”时,我们不会怀疑自己是停留在她对于“失去理智的那一刻”的把握之中。
世间“情”之一字,之所以迷人,大约就是因为即便从所有的情事之中抽离所谓的共同规律——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未必是不可能的事情——都不足以提供任何可供借鉴的经验与警示。它会在不同的情势下、不同的男女间转化为不同的样态。我们热衷于描述它,无非也就是想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否有为彼此提供幸福的可能,以及这脆弱的幸福是如何破灭的。不是吗?如果没有幸福的体验,甚至,如果爱情只是满足生理上盲目而非理性的需求,人们又究竟为什么要去爱呢?我们有一万种更为便捷的途径能够得到满足。爱情当中有人,有人的主体存在,有受到语言规定、反过来又影响语言进而影响爱情的爱的经验,于是爱情便成为从真实世界到想象世界的往复循环,成为两个世界互相满足和丰盈的道路。
回忆也是想象世界的一部分,于是爱情,或者幸福,都属于过去式,属于回忆。索瓦若告诉我们,幸福就像是一种香味,“如果我们喜欢一种香味,就会尽力留住它,追寻它;我们不会任由自己陶醉其中,对它进行分析,渐渐沉浸其中,以至只能通过回忆,唤醒身体对它的感觉;当香味再次出现,我们会更缓慢、更轻柔地呼吸它,感受着最为微妙的气息”。同样的意思,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也有,有时它被概括成简单的一句话,比如“生命只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靠着回忆和幻想,很多意义浮现了,然后消失,消失之后又浮现”;有时它会形成一个永恒的场景,比如著名的小玛德莱娜蛋糕。但是《让我独自一人》决计不会像《追忆似水年华》一般有着用回忆的方式道尽人生的野心。它基本只关乎爱情。
所以它还是让我们看清楚了爱情里的一些小游戏、小欺骗。这一切在爱情不再的时候都清晰地浮现了出来。难道女性真的就是在爱情中目盲吗?非也,爱情中的目盲也只是选择性无视而已。现在睁开眼睛倒回头去看那时的“你”,就能清楚地看到“你”的真实模样:“你嘴唇微微上翘,露出略显发黑的牙齿,脑袋整个往前伸。你在阐述刚刚发现的高明见解时,或者想出了什么办法、把别人以为的奇思妙想贬低为平庸之见时,就会摆出这副神态。”然而尽管“我”很清楚这一点,“我”相信,爱情真正的价值并非在于爱上完美,成为完美,而是“通过缺点和不足,进入爱人的心灵,那颗常常因为效仿众人而被湮没的灵魂”。
《让我独自一人》应该也是凭借这种不乏理智的剖白而吸引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注意的吧。瓦莱里(Paul Valéry)认为它“展现了一种非同一般的精神生活,以一种奇特的、离开自己去看自己的方式”;克洛岱尔(Paul Claudel)也认为它“几乎可以说是女性写作的代表之一”;而当时名噪一时的右翼作家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也注意到了这本小册子,他不吝赞美地评价道:“所有喜欢真实与简单的小叙事的人都会喜欢上……这部如此丰满的作品,因为,无论如何,这首先是一部值得爱、关于爱的作品。”
但除了爱,还有尊严。女性的尊严。《让我独自一人》并不避讳女性的视角,甚至多少带着俏皮地说,“您信里的很多句子,唤醒了我这些‘女权主义’的想法” 。的确,似乎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处在哪种文化中,天下的男人都很难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即便女人欢欢喜喜地说上或是写上一句“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也不过是女人己选择的一种姿态而已,何况这样给自己找点乐趣的情话,又怎么能是一个真的“低到尘埃里”的女人写得出来的?若有一日,要把这样的女人逼得淡眉淡眼地再说上一句“那我是不爱了”,尽管在公开场合不会刻薄心里本来就看了个通透的男人,但心里未必不会拿出二人之间的智力差异来还自己一个独立的人格。所以张爱玲可以在分手后对落魄的胡兰成从经济上施以援手,而索瓦若也可以在“被分手”之后,要求对方归还自己的照片,并且泰然自若地说:“但这不是因为爱您,是因为我还想丰富自己,因为我不愿毁灭自己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不想再去提升自己,只是沉浸在爱人幼稚的爱慕里,任由他摆布。”
克拉拉·马尔罗(Clara Malraux)对此有精到的评价,她认为这一剖白“ 本该在女性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第一部由一个不驯服的女人写成的书;如男性目光一般准确,目光所及,亦敌亦友,没有分毫奴性。……是一部带着简洁的忧伤的书,直面死亡,直面装出一副权威态度的男性的弱点,一部充满尊严的书”。

《让我独自一人》外文版封面
三
《让我独自一人》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至今将近一个世纪。
三十年代初,法国还没有完全被拖入战争的旋涡,但是新一代的小说家已经感受到了危机的临近。超现实主义、塞利纳、马尔罗,等等,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但都宣告了和瓦莱里、纪德、普鲁斯特等上一代人的决裂,他们的作品显然更关注社会现实而不是文学现实。
看得出来,肺结核就像是一道特殊的屏障,既将索瓦若与喧嚣的生活隔离开来,也将她隔离在本应该属于她这一代人的写作之外,使得索瓦若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两代人的中间地带:她既不赞成后一代人对危机过分夸大,面对真正的、个体意义上的死亡——虽然超现实主义或者荒诞派笔下具有夸张意味的死亡很快就在战争中变成了现实——也没有就此停留在前一代人的文学自恋之中。形式的革新在索瓦若笔下没有任何故意为之的痕迹:例如不同人称叙事的交织使用,梦境与现实的出入自由;而作为主题的爱情在这里成了一个进入自己内心世界的入口,最关键的仍然是两千多年以前就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这也许是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让我独自一人》仍然没有失去价值的原因之一吧。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除了残酷的战争以外,应该都是索瓦若没有看见、也无法预见的。链霉素的发明,使得肺结核早就不再是轻易就能夺去生命从而也夺去爱情的“白色瘟疫”。战争爆发了,又结束了。但是,永远不会有一劳永逸的结束,人类还是一次次因为同样的贪婪,将自己裹挟进任何性质的秩序都解决不了的灾难里。人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又亲手炮制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以为自己已经无比强大的人类万万没料到的是,另一种侵袭肺部的“瘟疫”会猝不及防地跳出来,警告人类,你离“认识你自己”还相距甚远。
我们不用再重复什么“神的惩罚”之类的不着边际的废话。索瓦若在留下的不多的文字里也奇怪地做出了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回答。在对《最后的晚餐》的评论中,她谈到自己对这幅画作的不喜,掺杂着奇怪的忧伤:
他(耶稣)的微笑与眼神流露出幻灭。他刚说完牺牲与赎罪的妙言:“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喝吧,这是我的血。”他感到孤独,因为他知道没有人真的听懂。……他眼睛低垂,没看向任何人,而是不满希望消失后的虚空:他面容疲倦、苦涩,像是失去了信仰。在这里我们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祂缺席了。祂应当来这里,给其子以信心,给人类以光明,帮助他们理解自己,或只是相信自己。然而上帝留在了天堂,在窗外隐隐一抹天空之上。
来到人间的是耶稣,他孤身一人。
没有神能够指引我们,无论归根结底是谁的子民,人类注定是孤独的。这是索瓦若在《最后的晚餐》里读到的信息,也是她从“被分手”的爱情中得出的结论,又何尝不是人类在历经灾难之后可能得出的普遍适用的结论!然而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让我独自一人》:人类终将孤独的结论并不妨碍我们用尽一切气力找寻不孤独的可能,哪怕只是暂时的。这应该就是索瓦若提到那则日本传说时所想到的吧。她说:
一则日本传说声称,在人出生时,月亮会用一条红丝带把将来要结合的男女的脚系在一起。在生活中,这条丝带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两个人会互相寻找,如果找到了,那么属于他们的幸福就会降临大地;也有找不到的人,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充满忧虑,凄惨地死去:对他们而言,幸福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开始,那时他们会看到红丝带系住的是谁。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系住我的丝带;我觉得这个传说跟所有的传说一样,给了我们诗意的安慰。
诗意的安慰。所以,哪怕躺平的时代终将到来,也让我们站着爱吧,因为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需要安慰,需要确立有尊严的、不孤独的存在。女人在爱情中索取的尊严也许更接近人类的尊严的本质。
原作者|袁筱一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