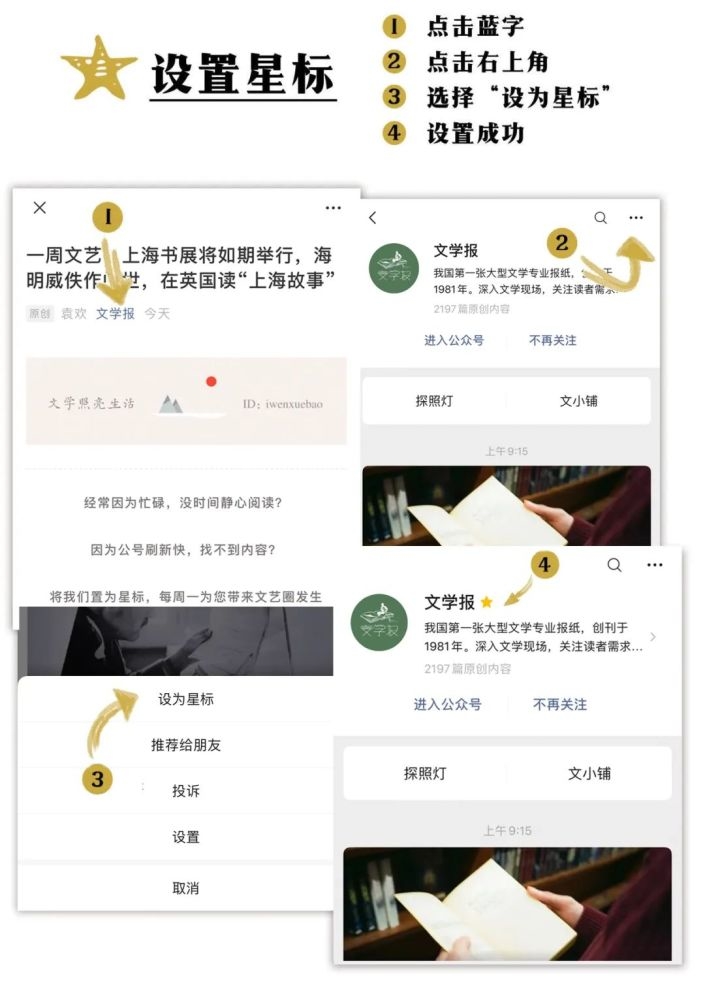“漫游者”孙甘露,在这两部作品中重拾缓慢的优雅,回望上海的时光流淌
 2021-07-23
2021-07-23

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办 | 纪录电影《天工苏作》聚焦苏州9项传统手工艺 | ......


从左到右:项静、孙甘露、罗岗、毛尖
“我第一次接触到‘缓慢’这个概念,是在本雅明的著作中,遥远而迟缓的土星,处在椭圆形轨道的最远端,它莅临的周期是如此漫长而缓慢。”作家孙甘露在《比“缓慢”更缓慢》一文中这样写道。而“缓慢”成为了切入他写作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了一种写作的姿态,他试图以此除去杂音和噪音,更加“从容地、适度地、低声地、诚恳地”退回到记忆最深处,探寻那些令灵魂震颤的部分。
7月18日,孙甘露与批评家罗岗、作家毛尖、青年评论家项静做客朵云书院·戏剧店,就“一个郊区诗人的上海时光”主题与读者展开分享。本次分享会围绕的两本书:一本文学评论与诗集《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完整收录孙甘露30余年阅读观影札记和诗歌创作。
另一本由世纪文景出版的随笔集《时光硬币的两面》则捕捉日常生活的微光,记录上海这座城的时光流转。互为映照的是,这两本书的核心都指向重拾缓慢的优雅,正如孙甘露所说:“我祈望我的书能唤起阅读和收藏的渴望,使人亲切地意识到与更广泛的世界的内在联系,甚至在这个影像时代的某个缝隙里,令我们乐于看见自己有一个掩卷沉思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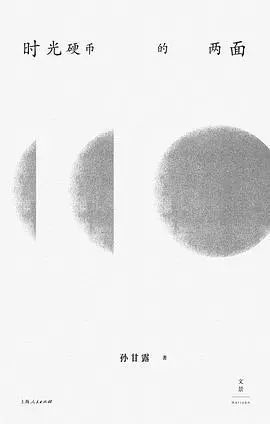

“我祈望我的书能唤起阅读和收藏的渴望,使人亲切地意识到与更广泛的世界的内在联系,甚至在这个影像时代的某个缝隙里,令我们乐于看见自己有一个掩卷沉思的形象。”
与“缓慢”相关的一个地理概念是郊区,孙甘露笑说“慢写作”可能来自朋友们的宽慰,但他说:“格雷厄姆·格林有一部自传《逃避之路》,里面有一句话类似于‘我们住在宇宙的郊区’。我们写作很多年以来关心的是中心和边缘,城市和乡村,核心主体偏离中心等,对写作者来说,这种偏离或者说跟不上趟,也可以说成是一种缓慢。”
对此,毛尖补充说他很喜欢一些边缘词汇,“这是他的表达,他的词汇表里有‘仿佛’、‘似乎’,很多不确定的东西。从边缘切入,是他对时空极为锋利的感受,所以他很少让自己处于时空的安全体或舒适地带中,可以说,他在边缘地带建构语词的大厦。”
人们形容孙甘露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在小说之外,他写诗。在他看来,诗歌写作不能说感性,它是一个不同的文体,可能涉及的是生活中或者思考中的不同念想。而从孙甘露的阅读来看,也存在着某种取向或巧合。他爱读艾略特这样具有标识性的诗人,但从感性层面来看,他说自己更偏向于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阅读他的诗歌,就像调频收音机,没对准频道时,可以听到原来的声音,但伴随着电流的杂音。”
他同时欣赏的另一位边缘性写作的作家是米兰·昆德拉,孙甘露在现场提及翻译了佩索阿的《惶然录》和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作家韩少功,和前不久刚完成了《韩少功论》的项静探讨了这一问题,项静说:“佩索阿住在一个小乡村,他却在思考宇宙。”她表示孙甘露和韩少功都很重视翻译文学,在当时,作为一名写作者,韩少功其实是选择和引进了一种文学传统。


米兰·昆德拉和费尔南多·佩索阿
“孙甘露特别喜欢翻译文学,这实际上涉及一个问题,翻译文学已成为现代汉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逐渐官方化的语言得以重新突破。”罗岗从语言的角度阐释了他对于孙甘露写作的想法,他用“第二次语言突破”来称呼以他为代表的作家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探索。“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第一次突破,但除了鲁迅等个别作家,大多数作家存在一个大问题:‘欧化八股’或‘学生腔’,要改变,有两条路,重回中国传统语言和回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声口叙事’。”他指出在后来的发展中,后者逐渐僵化,那么到上世纪80年代,孙甘露他们所做的就是以文化自觉回到一种诗化的、不欧化的书面语来。
对于语言的认知,孙甘露曾和罗岗有过深入的对谈,里面提及他认可克里斯蒂娃的观点——作家的工作就是将他内心的声音翻译出来,用语言将一种感官的、倔强的异质性翻译出来。作为这个意义上的翻译者,作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异类,一个最令人愤慨的外国人。我们大概就是马拉美所谓的“语言的局外人”,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普鲁斯特观察到的“对感性世界的翻译”。这样看来,“语言的局外人”或者说“做本民族语言的陌生者”是孙甘露所向往的一种写作状态。
罗岗认为《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时光硬币的两面》回到了中国的杂文传统,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评论或散文,而一个作家的语言脉络来自哪里,关乎作家的文学史定位,“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常会遇到提问:他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语言?他的诗歌和小说之间有什么关联?那我想,这两本书是一个很好的探索路径。”作家语言的“变”与“不变”中包含着很深的意蕴。


小读者参与活动现场
“缓慢”之外,本场分享会另一个关键词则是“上海”。罗岗说:“作家以‘城市的漫游者’身份,将自己‘铭刻’到上海这座城市中,参与文本创作之外的现实城市改造。”在毛尖看来,孙甘露有“四大发明”:他“发明”了陌生,“发明”了爱情,“发明”了时空,还“发明”了上海。
阅读孙甘露,她总是不止于一次,而阅读的反复带来的是无限的新意,“你进入爱情时它们通知你,你失恋时它们抚慰你。通过他的书写,我们陡然惊觉,啊,原来这就是爱情。”她认为在未来世界文学范畴里,真正参与竞争的文学类别是城市文学,而孙甘露“写出”了上海的惊艳。“罗岗将《上海流水》看成小说来读,这点特别重要。作家将生活中的词,从饭桌上召唤到我们的精神世界中。阅读这两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孙甘露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也在社会学意义上重新创造了上海这座城市。他是城市的发明者,像一名游走于城市里的行为艺术家。”她进一步说道:“因为上海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书写出来的空间,就像我们所在的朵云书店,还有思南读书会……上海的很多地标性文化地点都与他密不可分。”
项静接着毛尖的话,“写城市文学时,他还‘发明’了1970年代。”在这两本书中,有多篇文章回忆了那个年代,他将1970年代作为精神原点。“孙甘露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热爱杜拉斯那样的第一人称叙事,喜欢普鲁斯特内心的丛林和个人经验。这些不同的面向是如何融合到一个人身上的呢?”
孙甘露回应说:“如果用影视用语来说,1970年代是我电影中的决定性时刻。它塑造了我,即使走得再远,年龄再大,也依然要回望来处。当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塑造自我的瞬间,而写作者可能就是要揭示这些瞬间,我们回望生活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寻常之物,而这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尽管它的深处千帆过尽。”

文摘选读
比“缓慢”更缓慢(节选)
文丨孙甘露
如果不是一种修辞,那么,有什么比缓慢更缓慢呢?一本比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缓慢》更迟出版的小说?一种对更深的记忆的涉及?
我还记得在我的小说《呼吸》的封面上的引语:小说仿佛是一首渐慢曲……难道我是在说,我要越来越慢地退回到记忆的深处?那里存在着什么令我难以释怀的、使灵魂震颤不已的记忆吗?或者是因为缓慢的天性使我陷于想象,有什么无比珍贵的东西仅存于近乎静止的地方呢?
缓慢当然不是一种托词,我记得诗人柏桦那优雅迷茫的诗句:“啊,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一切!这里连可资比较的事物也不存在,这种自弃式的态度从来都是令人迷恋而又困惑的。
缓慢还关乎气息和声音,从容地、适度地、低声地、诚恳地,试图除去一切杂质和噪音地,因为“写作是需要百般矫揉造作而后才能掌握的一种才能”(菲利普·索莱尔斯)。
缓慢还涉及诸多事物的比较,地点,从一处移向另一处,捷克和法国,专家和昆虫,个人和公众。遗忘的喜剧,契柯西蒲斯基。因为记忆,人们总是遗忘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写作,一种离心运动,使我们日益远离我们的初衷。由南方向北方,由东方向西方,由小说向电影,由中文向译文,由边缘向中心。总之,写作使个人变成了它的形象。
有趣的缓慢论及的小说之一为《没有来日》。因为缓慢而没有来日?而使人沉溺于享乐主义?而陷入十八世纪式的错综的两性关系?缓慢涉及的另一部小说为修底罗·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征服和快乐,隐秘和泄漏,在这里落笔为文本身就是修辞和技巧。在这一点上我赞同昆德拉的意见,修底罗·拉克洛的著作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哦,缓慢还是温和的、疲倦的、歉意的、沉思的,譬如聂鲁达的诗句:“南方是一匹马,正以露珠和缓慢的树木加冕。”这可能是最缓慢的一刻,这是在向所有缓慢的时刻致意。哦,时间,黎曼空间中的时间,此刻,因为昆虫我想到了宇宙。
《缓慢》是一部清晰而又错综的乐曲,它比《不朽》更均衡地展示了昆德拉由一个捷克作家向法语作家的转换。那个热爱音乐的捷克人还在,他向我们展示的肢体依然是那么精致动人。
选摘自:《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主办方供图
1981·文学报40周年·2021

每天准时与我们遇见的小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