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读《教化》 |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高峰与终结
 2021-07-15
2021-07-15

编者按
耶格尔所著《教化》第一卷于1933年出版,借助古希腊语“paideia”所包含的诸多意味,以统一的视野考察了古希腊之全景,成为了那一时期德国乃至整体西方世界古典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为尚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痛经历-记忆中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提供了某种具有古典高贵性的精神慰藉。1936年,第一卷的修订版问世。1944年与1947年,《教化》的第二卷与第三卷相继出版。第二三卷虽然不及第一卷出版时带来的强大精神震撼,但是仍回响着第一卷开启的效果历史与精神影响的余波。《教化》第一卷分两编,大体上对应于古风时代与古典时代,第二卷聚焦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第三卷在对柏拉图作品继续讨论之外,兼及医学、色诺芬与修辞学-政治演说。在《教化》第一卷中,耶格尔为学之博大精审、深刻敏锐,在此卷得以充分展现,希腊精神世界的整体图景与恢弘气象跃然纸上,该书遂成为莱因哈特所言“第三次人文主义”的扛鼎之作,进而成为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命运的缩影。耶格尔以古希腊语“paideia”一词作为全书的命名乃至第三次人文主义的象征,从而使古典与现代的精神世界得以通过这种意义综合体连接在一起,标志着试图将古典理想与现代学术相结合,通过回溯古希腊的精神源头为深处危机的现代欧洲提供精神救赎的第三次人文主义的启航。但当耶格尔写作第二、第三卷时, 对于时代精神不断进步的信心已不复存在。透过他“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改造世界,而是理解世界”的自道,作为对于马克思那著名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颠倒,异常清晰地透露出无力改变世界的无奈。最后,本文作者指出:过去二十余年,西方古典学被较为系统地引介到汉语学界,激发了强烈的研究兴趣与思想反应,这显然并非仅出于“思古之幽情”,而始终伴随着对于中国自我文明传统的反思与问题意识:通过体会西方古典之博大精深,中国古典之真正高明精微者也更清晰地浮现出来。
本文原载于“六点图书”公众号。感谢白钢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教化》,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高峰与终结
文 | 白钢
耶格尔(Werner Jaeger)所著《教化》(Paideia)第一卷于1933年出版,借助古希腊语“paideia”所包含的诸多意味,以统一的视野考察了古希腊之全景,成为了那一时期德国乃至整体西方世界古典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为尚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痛经历-记忆中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提供了某种具有古典高贵性的精神慰藉。1936年,第一卷的修订版问世。不久,耶格尔离开德国,远赴重洋执教于哈佛大学古典系,在那里,他为《教化》第一卷加添了内容颇为丰富的大量注释,这使得1946年所出的英译版相对于此前的德文版,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1944年与1947年,《教化》的第二卷与第三卷相继出版。(如同耶格尔在英译本第二卷前言所说,英译本已经超越单纯的翻译,而是一本真正的英文著作。)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心境还是外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物非人亦非,第一卷出版时带来的那种精神震撼已不复有,但仍有由第一卷所开启的效果历史与精神影响的余波回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组织翻译出版的《教化》三卷本,是这部古典学巨著(opus magnum)在汉语世界的第一次完整呈现。
从结构而言,《教化》第一卷分两编,大体上对应于古风时代与古典时代,就涉及的题材而言,前者包含史诗(荷马、赫西俄德)、弦琴诗(伊奥尼亚和爱奥利亚诗歌、泰奥格尼斯、品达)、哲学(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政治思想(斯巴达传统与雅典传统),后者聚焦于以雅典为中心的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喜剧(阿里斯托芬)、智者派、史学(修昔底德)。耶格尔为学之博大精审、深刻敏锐,在此卷得以充分展现,希腊精神世界的整体图景与恢弘气象跃然纸上,该书遂成为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所言“第三次人文主义(dritter Humanismus)”的扛鼎之作,进而成为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命运的缩影。
德国人文主义的起源,可上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至《教化》第一卷发表的时代,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以1764年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出版的《古代艺术史》为标志,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欧洲民族更晚也更富于热诚地开启了将自我意识与希腊-罗马(特别是希腊)的古典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作自我命运之核心组成部分的精神历程。1800年,席勒的《希腊诸神》(G tter Griechenlands)修订版问世,是这场人文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象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有关希腊哲学的引言无法以人文主义加以涵盖,却在更深邃的精神层面上,流露出这种古典人文主义的内在气质:“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gebildet)的欧洲人心中,特别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heimatlich zumute)”,“我们之所以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乃是因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der gemeinschaftliche Geist der Heimatlichkeit)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这一阶段,古典语文学尚未与对于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哲学、艺术、历史的研究径然分离,它的存在更多是作为教养(paideia)的一部分而非专门性的学科研究(academia),从而被寄予对整体民族进行教育的期待。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由于在人文主义的第一阶段,古典理想与古典语文学的结合是如此自然而深切,以至于伴随着十九世纪学科分化的不断展开,二者间的疏离显得如此突兀而难以置信,却又无可避免。伴随着基于各种分立的学科原则与方法论对于古代世界的研究,原本作为理想而存在的古典世界,被分解为无数细小的局部而失去其整体性;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命运性精神纽带,被强调要与历史保持适当距离从而得以将历史作为客观对象加以考察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态度所取代(尽管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二者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古典语文学受到古典理想破灭与专业性-工具性特征不断强化的双重影响,故而整体民族教育者的定位不仅在现实层面不复存在,作为学科的自我意识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正是处于这种疏离趋势的日益强化的背景下,作为对于学科分化、学术发展乃至历史理性与时代进步的反思与反动,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式的古典人文主义通过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er Burckhardt)的《希腊文化史》与罗德(Erwin Rohde)的《灵魂》(Psyche),寻到了新的展现形态,其深度理论表达则出现于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之二《历史对于生活的利弊》序言中,作为厌倦于语文学家身份的哲人,他写道:“古典语文学如果不是具有在我们的时代里不合时宜地(unzeitgem ss)起作用的意义,亦即反对时代(gegen die Zeit),并由此作用于时代且但愿有益于一个未来时代(auf die Zeit und hoffentlich zu Gunsten einer kommenden Zeit)起作用的意义,它在我们的时代还会具有一种什么意义。”尼采之于这一阶段的人文主义,无论是其深刻、敏感与距离感,正如黑格尔之于其第一阶段。相对于第一阶段,此时的人文主义不复拥有政治热情,而更坚决地转向文化与艺术。

维拉莫维茨
作为尼采在古典学领域的毁灭性打击者,维拉莫维茨(Ulrich Friedrich Wichard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降最伟大的古典语文学家,他以近乎卓绝的学术能力,展现了古代希腊世界不同于人文主义理想的、极具张力的复杂面目与其背后的高贵伟大,将人文主义对于古典世界、古典作家、古典作品的虔诚转化为古典学家对于自我学术行为的虔诚(Andacht),从而标志着古典学研究中人文主义的终结。他对于普鲁士政治的高度认同,也与那一时期的人文主义的“非政治化”倾向清晰地区分开来。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战败后十余年的荒乱岁月,维拉莫维茨于1931年辞世,留下了或许是他全部学术生涯中最具思辨性的两卷本遗稿《希腊人的信仰》。两年后,耶格尔的《教化》第一卷出版,标志着试图将古典理想与现代学术相结合、通过回溯古希腊的精神源头为深处危机的现代欧洲提供精神救赎的第三次人文主义的启航。
以古希腊语“paideia”一词作为全书的命名乃至第三次人文主义的象征,当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paideia”一词源自“πα [孩子]”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动词“παιδε ειν[教育]”,代表着孩子通过接受教育而摆脱精神上作为孩子之存在的辩证过程。由于在古希腊语境中,除“孩子”之外,“πα ”一词还有“奴隶”之义,因而可以说,通过paideia所摆脱的,还包括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天然奴隶(φ σει δο λο ,《政治学》I.ii.7, 18)”状态。“paideia”一词包含着(或更确切地说,寄托着)彼此关联又各得其所的多重涵义,从而使古典与现代的精神世界得以通过这种意义综合体连接在一起。就大者言之,其意义域包含如下几个维度:
德语Er-ziehung,是拉丁语e-ducatio(英语education,法语educatio直接从其而来)之意译的产物,由表达强化涵义的前缀(拉丁语e-,德语er-)与源自动词“引导,牵引”(拉丁语ducere,德语ziehen)的名词组合而成,遵循这种构词结构,在汉语中对应之义为“教导”。《教化》第一章以“希腊人在人类教导史上的地位(Die Stellung der Griech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lichen Erziehung)”为题,可谓开宗明义。
德语Bildung,源自动词“bilden(构造,塑造)”,对应于古希腊语“τ πο [类型]”,“παρ δειγμα[原型,典范]”,其本意为“(依照典范)塑造,铸造”,引申为因塑造而成就的“教养”。《教化》的副标题“形塑古希腊人”正取此义,呼应于第一版序言所言“对希腊教养现象的本质认知(die Wesenserkenntnis des griechischen Bildungsph nomens)是当下每种教育知识与教育意愿的不可或缺的基础(eine unentbehrliche Grundlage)”。这一理念可上溯到柏拉图意义上灵魂的“ε πλαστον[可塑造性]”(《王制》377b),哲人进入政治领域,会将塑造自己( αυτ ν πλ ττειν)的方式运用于塑造他人的品格( θη)(《王制》500d)。在此意义上,耶格尔将柏拉图的学说称作是“人文主义”,一种致力于实现人类的本质图像(Wesendbild des Menschen)的教育。
德语Kultur,源自拉丁语cultura,由动词“colere[耕种]”演化而来,cultura意味着如同粮食或植物般被栽种、培育与收获。这一意味在汉语中正对应于“教育”。耶格尔将“Kultur”一词(在现代语境下它通常被译作“文化”),视作古希腊语“paideia”的对应,而英译本也将“古希腊文化的理想(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作为《教化》的副标题。显然,他联想到了普鲁塔克《论儿童的教育》一文正是以农艺(agri-cultura,本意为“土地的培育”)为例,说明教育中自然、学习、练习的三位一体关系。此文对于文艺复兴以降的人文主义传统影响极大,催生了“精神的培育(cultura animi)”式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
德语Psychagogie,源自古希腊语“ψυχαγωγ α[心灵感化]”,其本意为召唤身处冥府的灵魂,在柏拉图那里,被用于描绘修辞学穿透人心深达灵魂的力量(《斐德若》261a),这一意义上的paideia,是本书译名“教化”最恰当的对应。
因而,作为paideia之汉语译名的“教化”,包含着体现“教”之精神的“导”、“养”、“育”、“化”四重内涵,归之于“教化”,以其堪为“教导”、“教养”、“教育”之共同作用的果实。然若以paideia对应中国传统之“教”,则《易·观》彖言之“神道设教”,《中庸》之“修道之谓教”,又非paideia所能涵摄。
以paideia的理念为核心线索,耶格尔希望通过对古代希腊世界的追寻和探索,为精神上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欧洲寻到某种稳固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对他而言,精神漂浮不定属于尚未经教化的孩子,而稳定则是经由教化达到成熟的标志。因而,在《教化》第一卷中,充满着对于希腊精神之稳定性特征的寻找与论证。
面对荷马史诗,耶格尔将其中激烈的戏剧性冲突标示为它与其它类型的史诗作品的最大差别,盛赞荷马史诗中的每个人物都是完整的、活生生的个体,是高度真切的,令人仿佛可见可触,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浑然一体地结合在一起(lückenlos in sich zusammenh ngen),却有意识地忽略了,荷马史诗中最深刻的戏剧性冲突,正是源于核心人物之思想与行为的矛盾而非其一致性:战死于特洛伊而获得不凋谢的声名(κλ ο φθιτον)与从战争中抽身安然返乡(ν στο )的矛盾,在《伊利亚特》第九书中通过阿喀琉斯的自我思考呈现出来(IX, 412-416),此时的他从最初与阿伽门农决裂的意气冲动中摆脱出来,如同哲人般思考自身乃至人类的命运,构成了哈姆雷特式“生存还是毁灭”疑问的遥远先声;奥德修斯为了实现返乡的意愿,不惜拒绝了女神卡吕普索希望他作其丈夫获得永生的诱惑,但有着如此强烈意愿的他却并未拒绝作为女神卡吕普索的伴侣生活多年,直到赫尔墨斯的到来,面对各种人,他无一例外地以用谎言掩饰身份(从女神雅典娜的化身到他的儿子特里马库斯),甚至在在杀死求婚者后依然伪装为外乡人与妻子佩涅洛佩进行互相试探,这种复杂的人物性格,作为其思考和行动之内在矛盾的产物,正是《奥德赛》极令人着迷又令人困惑的特色所在。
耶格尔试图弱化乃至抹去这种矛盾,将荷马的作品界定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秩序世界,一种可供不断回溯的带有终极稳定性的典范(παρ δειγμα)与起源( ρχ )。耶格尔与他所属的人文主义传统并非全然不承认史诗内部的矛盾,甚至会将某些矛盾描绘为其最具魅力之处,却希望一切作为“变化与命运性发生(Wechsel und schicksalhaftes Geschehen)”的矛盾从属于他所理解与想象的“稳定与秩序(Dauer und Ordung)”,而不愿接受超越这种理解与想象的矛盾(例如史诗中人物之思想与行为的矛盾),生怕那样会动摇其作为古典理想的存在,削弱通过这种典范形象所维系的“稳定与秩序”。
赫西俄德
无独有偶,在对于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的讨论时,耶格尔特别强调了它所代表的希腊农民的精神状态,一种与荷马史诗所代表的贵族理想人格截然不同的存在,他将之称作“如土地般稳固的伦理(eine bodenst ndige Ethik)”,而赫西俄德的全部天才与成就,则被概括为“看到了他的社会生活和每一个同胞的生活赖以建立的不容动摇的基础(die unantastbaren Grundfesten)”。不论在荷马还是赫西俄德那里,在二者颇为不同的精神世界中,他都发现了希腊精神令人心仪的稳定性。
这种对稳定性的推崇与追求,也反映在他将 υσμ ( υθμ )的本义解释为“给运动变化加上锁链,给流动之物加上界限”,进而将认为,“希腊人在音乐和舞蹈中发现的节律背后的原初概念,不是流动(Flie en),而是停顿(Halt),是对运动变化的坚决限定(feste Begrenzung der Bewegung)”,为此,他不惜否定“ υθμ [节奏,节律]”与动词“ ω[流动]”之间的意义关联,而试图寻找一种新的词源学解释。
在描述希腊哲学的起源时,他又一次诉诸希腊精神的客观稳定特征,以一种黑格尔式的语调,判定东方的精神在其宗教诉求中直接沉入感觉的深渊,寻不到牢固的立足点(dort nirgendwo festen Boden findet),而希腊精神则通过认知外在宇宙的不变法则而寻找灵魂的内在法则,最终达到对于内在宇宙的客观观察(gelangt zur objektiven Anschauung eines inneren Kosmos)。
在另一处高度体现黑格尔风格的段落,希腊被描绘为某种独极特的无法取代也无法模拟的存在:作为一种古老的文明,希腊与同样古老或更为古老的东方文明相比,更富有自由的精神与主体性(通过个体观念与个体思想情感的张扬);而相对于赋予自由与主体性以至高地位的现代性文明,即便最富于个人意识与思想感情的希腊表达,也并没有那种纯粹的主观性,“希腊的个体性获得其自由与自我意识的活动空间,并非通过简单地解除对主观性的束缚(einfach dem Subjektiven die Zügel schie en l t),而是通过使其自身成为精神上客观的东西(da es sich geistig objektiviert)”。在此,古今之争与东西之别被同时触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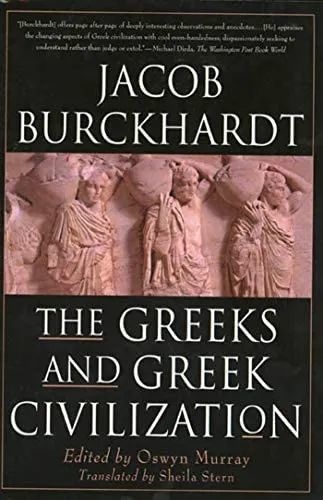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布克哈特著
在论及希腊城邦-国家(polis)与希腊文明的关联时,耶格尔极敏锐又极坚定地断言,城邦是希腊文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心(das allbeherrschende Zentrum),描述希腊城邦便是描述希腊生活的整体,进而,将希腊式的古典和谐命名为“政治人文主义”,把《教化》一书的目的描述为“在希腊的所有历史时期中追寻这一观念的发展,并以二者之间的严重对立为终结”。有趣的是,“政治人文主义(political humanism)”这一对全书带有根本纲领性质的概念,却并未见于正文,而是作为1946年新版卷一的注释出现,而正文中有关伦理和政治相结合是真正的教化的基本品格之一、高级教育与国家和共同体理念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古典希腊的本质特征之类的论述,乃至第二卷中所言“柏拉图的人文主义原则上不是非政治性的(nicht prinzipiell unpolitisch),尽管如此,其政治态度不由经验的现实所摆布,而由它以为真正实在的理念所支配”,倒更像是对它的注释。
这种“政治人文主义”,面对斯巴达与雅典时,呈现出颇为复杂的态度。斯巴达政体,对于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而言,是由哲人王吕库古创设的、体现其远见卓识的伟大作品,在耶格尔笔下,却被描绘为“事实上是更早更简单的共同体生活阶段的一种遗存(Fortdauer),具有特别紧密的族群联系与有欠发达的个体性(von besonders z her stammhafter Bindung und schwach entwickelter Individualisierung)”,从而将斯巴达政体以及相应的理想归结为古典时代希腊哲学家的想象与创造。象征着种族团结、公民团结、压抑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斯巴达,被视作“持彻底个人主义立场”的雅典之对立物,在不经意间被映射到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欧洲大陆,构成了对时代境遇的精神反思:相对于德国,俄国-苏联被认作斯巴达;相对于英法,德国被认作斯巴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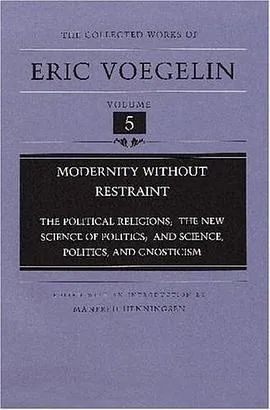
埃里克·沃格林 《没有约束的现代性》
这种古希腊在近现代欧洲的映射,绝非偶然。在品达与但丁、希腊僭主与美迪奇家族(他们同样喜爱并资助思想家与艺术家,代表着新的政治力量)、智者派运动与文艺复兴乃至启蒙运动之间,耶格尔发现了某种隐秘而深刻的精神对应。特别是对于欧里庇得斯,他不但继承了将其描绘为启蒙时代作家的看法,更把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为其作品的核心特质加以把握:当他将资产阶级化(Verbürgerlichung)之于欧里庇得斯时代的雅典与无产阶级化(Proletarisierung)对于他所处的欧洲相对比,并特别突出它的降格(Entwürdigung)特征时,古希腊的精神史与近代以来欧洲的精神史似乎融为一体。当他把喜剧描绘为雅典的审查制度(Zensorenamt)时,读者不禁要跟随他一起思考,是否有现代民主制度的审查制度,如果有,又该是如何实现的?
“雅典政治雄心最高的正当性证明——即使在他们失败之后——是教化(paideia)的理想,通过这一理想,雅典精神找到了它的最大安慰——即它自身永垂不朽的保证。”《教化》第一卷的结尾处,耶格尔表达了对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雅典的最高敬意,或许,在他心中,同时浮现的是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德国。

黑格尔
在第一卷中,耶格尔部分地承继着黑格尔式的历史观,试图勾勒作为整体的希腊精神不断自我演化的规律。他相信,通过萨拉米斯海战获得对于波斯入侵之决定性胜利的希腊,特别是雅典,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在诗歌中所发生的现实的精神活动,都不是通过神话,而是以纯粹的思想性形式(in rein gedankenhafter Form)得到表达的。”这种希腊精神“从神话(Mythos)到理性(Logos)”的演化进程,构成了德国人文主义之希腊认知-想象的核心。尽管事实上,神话非但在以悲剧与喜剧为代表的文学形式中,而且在最重要的希腊哲学作品中依然发挥着极重要的、无法为“纯粹的思想性形式”所取代的作用,而公元前6世纪后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也绝非由哲学思想(包括智者派的哲学)一统天下,包括狄奥尼索斯信仰与俄耳甫斯信仰在内的各种秘仪宗教,其影响力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较之此前更为强大活跃,阿里斯托芬的《蛙》与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都是深浸着秘仪宗教精神的经典之作。多茨(E.R.Dodds)所著《希腊人与非理性》(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1951)一书,深刻揭示出这种希腊精神长期被忽略的真实维度,从而在根基上动摇了《教化》所表达的单向度线性演进的理性主义希腊观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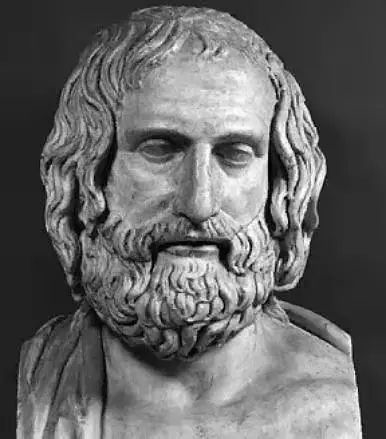
欧里庇德斯
当耶格尔写作第二、第三卷时, 对于时代精神不断进步的信心已不复存在。在第二卷序言中,他通过引用米南德(Menander)的两处诗文,表达了paideia作为古典世界之最后精神寄托的意义,“在失去此世的一切——国家、权力、自由乃至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生活——之后”。这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文主义者的幻灭与坚持。《教化》第二卷与第三卷以柏拉图哲学为主要探究对象,却试图以修昔底德式的客观性标准,创作出源于历史沉思精神的哲学剧(philosophical drama),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在其推崇的方法与追求的目标之间的根本差别:修昔底德不曾想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哲学或戏剧,而最能体现哲学剧精神的欧里庇得斯戏剧和柏拉图对话录,也绝不会采用修昔底德式的标准。透过他“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改造世界,而是理解世界”的自道,作为对于马克思那著名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颠倒,异常清晰地透露出无力改变世界的无奈。
相对于第一卷所述内容之纵深广博,第二卷聚焦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第三卷在对柏拉图作品继续讨论之外,兼及医学、色诺芬与修辞学-政治演说。尽管依然延续了第一卷的学术水准,却无法掩饰整体结构的严重失衡:柏拉图的哲学,虽然对于希腊精神世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此前paideia的集大成者,但必须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结合,作为希腊古典哲学的成熟与完成形态,方堪与第一卷所勾勒的诸多传统(诗歌、哲学、宗教、政治、戏剧、史学)构成一种在精神之深度与广延上的真正平衡;而即便对于柏拉图的哲学,《教化》第二、三卷也未能提供一种整全的视野,第二卷所重在《王制》,第三卷所重在《法义》,对后世的宇宙论乃至自然科学有极大意义的《蒂迈欧》,表达其对于“一”与“多”关系之最深刻思考的《巴门尼德》,与后世灵知派与基督教思想深度关联、阐发灵魂不朽观念的《斐多》,以“什么(谁)是哲学家”为主题的《泰阿泰德》、《智者》、《政治家》三部曲,都没有作专门的讨论,于柏拉图之天人之学可谓只得其半,这使得全书结构失衡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与之相比,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其卷二《城邦的世界》所涉及者大体对应于《教化》第一卷,卷三则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题,在讨论柏拉图的部分,除了《王制》与《法义》的呼应之外,还以《斐德若》与《政治家》、《蒂迈欧》与《克里提亚》为呼应,其结构相较《教化》第二、三卷更为合理。
《教化》第三卷中与修辞学和政治演说相关部分,重点讨论了伊索克拉底与德摩斯梯尼的思想,更以论德摩斯提尼的章节作为全书的终结:德摩斯提尼的政治演说被赋予了让自由城邦得以永恒的神圣光环,而他的自杀则被视作希腊古典时代终结的象征。无论是出于何种考量,这都使得整部《教化》结束得过于仓促与苍白。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一切伟大者必有伟大的开端,也必有伟大的终结。无论对于德摩斯梯尼的历史意义(特别是他对于“政治人文主义”的意义)作怎样的强调,他都不足以成为希腊古典时代这一伟大者终结的真正象征。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称作“人类的导师(Lehrer des Menschengeschlechts)”,在一部以“paideia”为主题和根本宗旨的著作中,如果有一个人适合作为自荷马以降的全部希腊paideia传统的终结象征,那只能是亚里士多德。耶格尔在1923年出版过《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这一专著,但他始终坚持将亚里士多德视作希腊化时代开启,而非希腊古典时代终结的象征。他没有意识到,希腊化时代在精神上的核心主线是广义的灵知派(Gnosis)运动,这与亚里士多德有着根本上的气质差异。在此意义上,他既没有为古典希腊时代寻到与其伟大相应的终结象征,又为希腊化时代设置了一个足够伟大但却并不十分相应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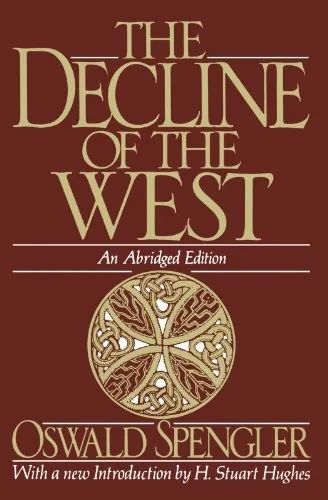
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教化》的这种显得有些突兀的结束方式,恰恰成为第三次人文主义命运的写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重大创痛,令持续长达数个世纪的有关西方引领人类进步的想象受到严重冲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构思于一战爆发的1914年,出版于战争出现决定性转折的1918年,以一种根本上有别于进步主义史观的文明论视野,将世界历史解释为诸文明体依各自的生命周期而升降演化的过程,用启示录式的语言,宣告了西方文明无可避免没落的命运,对于当时欧洲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教化》第一卷的问世,试图通过回溯欧洲与希腊世界的命运性关联,为处于历史长河之惊涛旋流的欧洲精神寻到某种绝对稳固的岛屿,从而不陷入斯宾格勒所预言的没落。它以古典语文学为载体,其整体历史基调似乎近于黑格尔,却由于迫切希望为欧洲找到精神归宿而失去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精髓:黑格尔不会执着于寻找历史长河中不动的岛屿,而会承认,在此长河中的一切岛屿自身也在漂浮。
因而,并不奇怪,《教化》第二、三卷从原有的历史观大步退却。坚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于思辨,而在于是否有足够坚定强大的内心。即便能够在理性上认知、接受带有典型黑格尔特征的历史原则—历史习惯于在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演进,真正的善是一种强大的能够自我实现的原则,它恰恰会借助各种恶的形态(包括人的一切恶的欲念、品行、习惯、实践)来实现自己,但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时代,这种理性原则往往无法与自身的情感、体会、记忆、认同有效地融合,甚至会呈现无法调和的对立情态。本希望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提供精神救赎的《教化》,当遭遇远比一战更为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能退回到把对于古典希腊的研究作为自身的慰藉。尽管书中多次提到“φιλοσοφο μεν νευ μαλακ α [我们思考哲学而不软弱]”的理想,但终究未能免于软弱。但源自古典的慰藉,虽未能让耶格尔的心变得足够坚强,却让其保持了基本的审慎与高贵,而未落入如福山“历史终结论”般对黑格尔主义的拙劣模仿。

《教化》
由《教化》开启的古典学通过回溯希腊之为希腊的“精神”为欧洲(西方)的危机寻找救赎的道路,通过斯奈尔的《精神的发现》得以延续和光大,但不再是以古典人文主义的方式。斯奈尔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白地表达了这种差异:“希腊性(Griechentum)的意义在这里将以不同于古典主义(Klassizismus)的道路加以探寻:我们想要追寻的不是一种完美的、无历史性的人类存在(Menschentum),而恰恰是希腊人所承担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精神的发现》在1946年的出版,标志着德国语文学在二战后的重生,也意味着以《教化》为标志的第三次人文主义的正式谢幕。
在《教化》与《精神的发现》之间一脉相承的对于希腊精神卓异于周边民族而纯然独立发展的假设与将“古典性”只局限于希腊-罗马世界的文明认同,又进一步被以布科特(Walter Burkert)与韦斯特(L.Martin West)为代表的具有更广阔整全视野的古典学学者所超越。布科特的《希腊宗教与文学的东方化时代》(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Sitzungsber. Heidelberg Philos.-hist. Klasse,1984)与韦斯特的《赫利孔的东方面目:古希腊神话与诗歌中的西亚元素》(The East Face of Helic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这两部里程碑式作品,通过展现早期希腊与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在精神深处的紧密关联,突破了长久以来作为古典学内核的希腊中心主义神话,从而令希腊的paideia传统在古典主义想象中被遗忘与隐藏的众多内容重新浮现出来。这里只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耶格尔将阿基罗库斯一首与自我对话的诗歌称作后世独白(Soliloquia)文体的胚胎时,他显然并不知道,在处于中王朝的埃及,自我与灵魂对话这种体裁就早已产生了《一个厌倦生活者与他灵魂的对话》这样成熟而深刻的作品,它记述了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人与其灵魂巴(b )的对话,他想要说服灵魂接受他结束生命,却被灵魂提醒自杀者不得入葬不得举行葬礼,继而灵魂试图劝慰他,通过寻找感官快乐可以忘记烦恼,最终灵魂向他保证,即便他决定自杀,灵魂也将与他同在.而在美索不达米亚、迦南与安纳托利亚的文学传统中,思考常被表述为发生在内心的对话。
古典的非唯一性与作为复数之古典传统的关联互动,使得文明论意义上的古今问题与东西问题无法被置于单一古典传统中颇为常见的“文”-“野”对立范式(在中国、印度、希腊的传统中皆有体现)加以考察。这对于浸润于某一特定古典传统、对其产生深切认同并将之与自我认同融为一体的古典爱好者而言,往往并不那么容易接受。过去二十余年,西方古典学被较为系统地引介到汉语学界,激发了强烈的研究兴趣与思想反应,这显然并非仅出于“思古之幽情”,而始终伴随着对于中国自我文明传统的反思与问题意识:通过体会西方古典之博大精深,中国古典之真正高明精微者也更清晰地浮现出来。伟大者之为伟大,恰需有其他伟大者的存在以作参鉴与砥砺。对于中国而言,无论希腊、希伯来,还是印度、伊朗、巴比伦、埃及,都是能让中国的古典精神更深切著明地回返自身、觉知自身、体证自身的伟大存在,都有着属于自我的paideia。
“它的光辉依然闪烁,结局尽管苦涩,但依然与之保持和谐(Ihr Glanz leuchtet noch einmal auf, und das Ende ist trotz seiner Bitterkeit in Harmonie mit ihr)。”《教化》第三卷结尾的话,也正适用于这部未能实现最初期待但依然保持自身价值的伟大作品,以及它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