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在课堂上文学其实是一种精神
 2021-06-28
2021-0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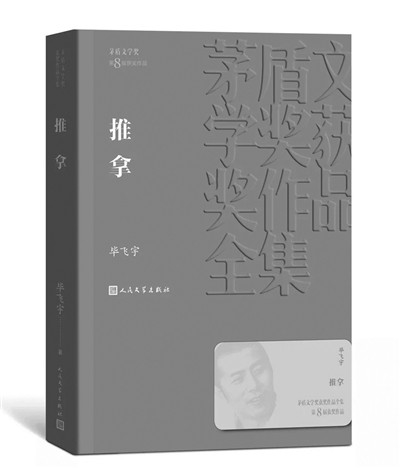


◎张英
毕飞宇是一个认真得严肃的作家,也是我尊重的兄长和朋友。
我说的认真指的是工作和公众场合,不管讲课还是办活动,他待人接物都事无巨细,会亲自盯到底,认真又细心。比如最近由他策划、在母校扬州大学举办的“格非作品研讨会”,还有在他老家兴化举行的“西川诗歌研讨会”、在他任教的南京大学举办的兴化业余作者系列改稿会,这些活动都要花很多精力,他不拿钱,完全是义务参与,算是对家乡和母校的回报。
严肃呢,则是指他的写作态度,爱惜自己羽毛,一个小说不修改、打磨到自己满意、实在改不动为止,不会轻易拿出去发表。
想法多的人,有一个特点,爱读书,作品少,精品多。50岁的时候,毕飞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自己的10卷本文集。作品集全部字数加起来,不到300万字,研究者很容易读完。这一点,倒是和余华很类似。
在我眼里,有两个毕飞宇,一个是活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沉迷于历史叙述与文学实验,被王朔、陈晓明看好的先锋文学作家,出版了《慌乱的指头》《上海往事》《祖宗》《那个夏季那个秋天》等作品;另外一个则从新世纪开始,在2000年后,从《地球上的王家庄》开始,从《青衣》《玉米》《玉秀》到《平原》《推拿》,重新调整自己的写作基点,回归现实主义,从语言到叙述和文体,视野回到故乡,书写当下的生活。
2013年,毕飞宇正式调入南京大学,担任特聘教授,主讲小说课。这些内容结集为《小说课》,到目前为止,销量超过了20万多册。这十年里,他写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和《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一个是对故乡生活的回忆,一个则是自己的小说与创作,算是总结。
2020年的最后一天,毕飞宇当选为江苏省作协主席。“我来到江苏作协的时候只有34岁,获得了一个特别宽松的创作空间。它温和、重才、不妒、相互提携,这个文化太好了。现如今我56岁,虽然做了主席,但我不拿工资,只是工作和服务,把这个文化和创作空间送给年轻的作家们 ”。
等待十三年的长篇小说
张英:你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非常节制。包括你也写诗,却没有发表过。小说也是,走红之后,并没有把很多之前的作品拿出来发表。
毕飞宇:我写过诗歌,一堆的手稿。稿子多了,我自己就知道了一件事,我是写小说的人,不应该去写诗。后来,你也知道,其实我是可以把那些诗歌拿出去发表的,可我都拒绝了。没必要的,我干吗去出这个丑呢。就是小说稿,我发表处女作之前的所有作品,我也一篇没有拿出发过。不要丢人,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张英: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少了一部分研究依据。
毕飞宇:我也曾经痛恨过编辑,觉得他们有眼无珠。后来我就不恨了,因为我知道了美学的标准。研究的依据和我没关系,我的创作只能以我的处女作作为参照,其他的,忘了吧。
张英:《推拿》拿了茅盾文学奖之后,13年里,我一直在等你的新长篇小说,但没有看到。
毕飞宇:那又怎么样呢?有一度我都不想写了。你知道不想写的感觉么?体能充沛,状态饱满,就是不想写了。我知道我这样的话不好理解,那就不指望你理解了。可我有惯性,一直没有离开我的电脑,我始终没有摆脱那种没有由头的希望,写了删,删了写,这些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手里有一个长篇,一直缠在手上,好吧,我决定把它写完。我想我可以写完。
张英:创作上的困难和障碍,在什么地方?
毕飞宇:我不知道,我就是不想写了,我看不到意义。我身边的人着急,说你不该浪费了你自己,可是,我又能如何?2008年,我写完了《推拿》,实际上,我在2009年就可以把新书拿出来了,可我昏了头,想休息一下,这一来我的新书就耽搁了。我不想抱怨什么,我只是谴责我自己,我应当在2009年把新书拿出来的。2009年,多么陌生的一个数据,多么陌生的一个时间点。错过了就错过了吧。
张英:你怎么样面对压力和焦虑?
毕飞宇:我有压力,我也焦虑,这个我必须要承认。可我现在没压力了,也没有焦虑,我就是晃悠,读书,健身,还有就是坐在电脑面前。我面对压力的时候就是给身体以负荷,这让我轻松了许多。我的生活里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钢铁,它们很重,好吧,那我就和它们对着干。我知道的,最终失败的只能是我,可那又怎么样呢?钢铁,你确实厉害,可你并没有压垮我。海明威的话,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
张英:上次采访余华,他很后悔,自己在身强力壮合适写长篇小说的时候,花了十多年时间去写随笔,在《读书》杂志开专栏。15年后再写《兄弟》,发现写长篇小说是个体力活,身体不如当初了。
毕飞宇:我理解余华,真的理解。可我不理解他的后悔,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在我看来,余华完全用不着遗憾,少写一个长篇又怎么样?如果没有那些随笔,你以为余华是完整的么?不是的。我不认为余华的随笔比不上他的小说,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像喜欢他的小说一样喜欢他的随笔。有一天,我问余华,你怎么那么会读书?余华的回答让我很不满意,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读者的感受,他们希望我一年一个长篇。这当然很好,可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我想一个人静下来,不可以么?可以的。我是去年的疫情期间获得精神上的顿悟的,外面的世界,你精彩去吧,我写我的,这总是可以的。我一下子就获得了能量,一直写到现在。
任作协主席是干义工
张英:去年最后一天,你当选新一届江苏作协主席。江苏是个文学大省,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作用?
毕飞宇:先让我感谢南京大学吧,我至今在南京大学拿工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我拿着南京大学的工资,做江苏作协的工作。意思是很清楚的,我永远是南京大学的一个教师。我如何看待我的工作?以一个作家的直觉做事。你说得对,江苏是一个文学大省,我能做好一个作家,就能做好一个主席;我不能做好一个作家,我就不能做好一个主席。我用作家的思维方式去对待我的工作,这是我唯一要提醒我自己的。以作家的方式面对作家,这就是我的作用,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承诺,也是我的局限。
我们江苏是文学的厚土,人才辈出是一个常态。我要告诉青年作家的是,不要急。作家的成长周期非常长,急了也没有用。我不会给青年作家特殊的关照,我只想把青年作家放到常态里去,你必须面对批评,你也必须面对赞美,这些你都要承受。好作家都是从常态底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常态就是日常生活。我爱年轻人,我的爱就是保持住常态,我不会把任何一个人搂在怀里。我最想对年轻作家说的是,我爱你们,可我不会打搅你们的常态。你在常态里成长了,我祝贺你,你在常态下倒了下去,好吧,我且行且珍惜。如果年轻人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你们可以把我换了。没有一个好作家是依靠主席的提携而成长的,我能保证的是我的公正、我的爱。
张英:你怎么看你的母校扬州大学成立毕飞宇研究中心?
毕飞宇:我的母校是个小学校,可是,现当代非常强,这个是有传统的。我的母校决定成立毕飞宇研究中心的时候,我就对母校的青年教师说了,“毕飞宇研究中心”无非就是两个走向,一,研究毕飞宇;二,研究中国的当代文学。哪个有意义?你们自己说。我们要做大事情,毕飞宇当然可以研究,可是,和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比较起来,那就太小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研讨会,是李敬泽,然后,是格非。这些都是挑战,扬州大学的研究中心必须要面对挑战,这个中心能不能面对挑战呢?我也不知道。
张英:老家兴化的毕飞宇工作室是什么时候开始搞的?
毕飞宇:2014年。毕飞宇工作室就做两件事,文学沙龙,还有图书馆。图书馆先不说,我们的小说沙龙已经办到第19期了。每一次都是给业余作者做小说研讨,研讨完了,作者再修改。其实我是知道的,许多作品在改完以后依然达不到发表的水准,可是,发表不发表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讨论。我们的讨论会请许多作家过来,余华、叶兆言、叶弥、贾梦玮、王大进,他们都来过。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小气的话,他们一分钱都没有拿,就是来讨论。
张英:这么多工作,南京大学的教学、毕飞宇工作室、在老家兴化的改稿会、扬州大学的小说沙龙,还有作协,会影响你的写作吗?
毕飞宇:这么说吧,迟子建、阿来、艾伟、东西、叶舟,他们都是作协的主席,他们的写作因为公益活动受影响了没有?没有。他们没有影响,我为什么就有影响?其实我是有依靠的,我在老家有一帮朋友,庞余亮、刘春龙、金倜、郭亚群,这是一个团队。他们很能干,几乎把具体的事情全做完了。我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参与一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有切身的体会,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渴望和别人交流,一直都没有找到。推己及人一下,我假定我老家的年轻作家也渴望和别人交流,我提供一个机会,就这样。
张英:传统社会,所有农村考出去的文臣武将,到老了一定要在老家做点公益事情,修路修桥,修庙办学。
毕飞宇:有点类似,有点类似。你知道,我在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农民有农民的潜意识,总想服务家乡,总希望家乡能好一点。我能做什么呢?一个穷酸的秀才,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秀才人情一张纸,我所做的,就是一张纸的事情。我希望老家的业余作家在这张纸上写点什么。
张英: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文学创作是一个感性,需要天赋的工作。
毕飞宇:天赋是必需的,哪一个做出一点成绩来的人没有一点天赋呢?可我很少说天赋,因为谈论天赋是没有意义的,老天给你多少,就在那里了,你能如何?我更看重后天,这个是一个变量,是可以通过后天改变的。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骄傲,体会到天赋了么,很酣。可是,我年纪越大,越不在意这个东西,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康德说了,人是人的目的。如何面对这个目的?这里头是千差万别的。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这样的假定,我很愚蠢,但是,我努力过了,我用自己做目的,我改变了我自己。
小说的精神是无中生有
张英:《小说课》大家都在谈论,你觉得你写了一部教科书么?
毕飞宇:不是,我反对这个说法,我自己对《小说课》的评价没那么高。道理很简单,我在上课的时候并不舒服。为什么呢?讲课是一个思路,写作是另一个思路。我在南京大学上课的时候时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在写作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想的?当然不是。写作是混沌的,它的进程极其幽暗,是理性不及的。可是,在课堂上,你要清晰,你要有你的逻辑性,这就矛盾了。我觉得我的《小说课》离写作的本质非常遥远,可我也无能为力,我不知道如何把一个作家最真实的状态呈现给同学。我很宿命,就看学生的缘分吧,他明白了,很好;他误解了,我万分的抱歉。
张英:这是当然的。可我觉得文学教育很重要,精读分析很重要。很多知名的作家,都是“一部好”作家,处女作和成名作就是他一辈子最好的作品,写作没有生长力和伸展性。
毕飞宇:你说得特别好,“伸展性”这个词很关键。感知会不会带来伸展性?想象会不会带来延展性?逻辑会不会带来延展性?文学史会不会带来延展性?天赋会不会带来延展性?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命运,要碰。可是我遗憾,我至今没有遇到一个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学生,是我没有慧眼吧。可我知道,他在,一定在,只是我还没有遇上罢了。
张英:去南大是怎样的机缘?
毕飞宇:我一直在南京大学做讲座,是丁帆教授邀请的。有一次,南京大学校长请了勒克莱齐奥吃饭,叫我去作陪。吃饭过程中,一个女教师问了一个问题:毕老师,你为什么不愿意到我们南大来?我很懵,哪里是我不愿意来,是我没有资格来。当时唱了一段南京大学“赞歌”,校长特别高兴,他说:“没想到毕老师对我们南京大学如此喜爱,那你就来吧。”我以为他开玩笑的,两个月之后,我就调到南京大学工作了。
可是,我来南京大学干什么呢?是王彬彬教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不要上课,就做讲座。这就好办了。讲课我做不到,那是系统的,仿佛一个工程,可是,做讲座很容易,它没有系统性,没有工程性。
张英:你在南大教书也快十年了,这边有写得好的学生吗?
毕飞宇:我不管这个,能写的也有几个,可我不在意。他们有可能现在写,有可能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再写,我没有必要死心眼。文学是一项长久的事,一个学生,他从我的手上起步,他没有从我的手上起步,我都可以接受。实际上,南京大学文学院还有一个影视戏剧学院,同学们对戏剧的兴趣更大,可我对戏剧是一个外行,我就给他们说一说虚构,其实挺好的。我的学生当中有一个庞羽,现在已经很有样子了,她未来会怎么样?看造化。
张英:复旦的王安忆教授也感叹,几届创作硕士毕业后,从事写作的人很少,一两个会留在媒体,更多人去做其他行当了,能坚持写小说的人很少。
毕飞宇:学生毕业之后到底去干啥,我其实不在意。我当然希望有一个青年作家在我的身边成长起来,可是,我也没那么偏执。学生不写小说,那又怎么样呢?无所谓。在我的书房里,文学就是写。在课堂上,文学其实是一种精神,敢创造,敢无中生有,这就很好了。小说是虚构,小说的精神是无中生有,一个孩子如果能勇于面对虚无,去创造,做什么都一样。事实上,我的课堂也不只是学生,还有许多“拉杆箱”,他们夜里面飞来,听完课,然后飞回去。这让我很满足,再怎么说,这是南京大学的文学课堂,有人从北京飞来,有人从广州飞来,有人从成都飞来,我还想怎么样?我已经非常满意了。他们写小说固然很好,不写又怎么样?你说能怎么样?
写作一定可教
张英:好像你父母都是老师。
毕飞宇:我父亲是个读私塾的人,一天物理都没有学过,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乡村的高中物理老师了,还是“文革”期间他自己在家自学的。他这样的人都能当高中物理老师,你想想不可笑吗?太搞笑了。
我的父母对我很不满意,在他们眼里,写小说不成体统。这么说吧,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得了鲁迅文学奖了,可我的父亲很不在意,他们觉得写个小说不算什么东西。直到我拿到了茅盾文学奖,他们才觉得这个儿子还可以,但是也没有多骄傲。
我的母亲始终认为他的儿子写小说很“不成器”。有一年,我母亲胃部做手术,在医院里面,她和一个老太太聊天。后来我进去了,我母亲没有介绍她的儿子是“一个作家”,我母亲说她儿子是“南京大学教授”,她很骄傲。这一下我就全明白了。
张英:这也挺好,你爸妈也是老师,老婆是老师,最后儿子也成了教授。
毕飞宇:对,他们很满足。感谢南大,我对我的父母有了一个交代。
张英:你大学毕业到南京特殊师范学校当过几年老师,直到调到《南京日报》当记者。到南大重新当老师,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毕飞宇:太不同了。在师范学校当教师的时候,我的第一份职业,基本上就是讲汉语知识,讲声母韵母,讲语法讲修辞,就干这个。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学校终于开了一门美学课,我自己编了一部美学的教材,那时候胆子大,什么都敢讲。现在看起来,当然很浅陋,非常浅陋。
南京大学当然不可能让我去讲汉语、讲美学,他们这方面的教授比我厉害的太多了。我的工作就是讲述小说的方法论,这个我还是可以的。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现在几乎不再信口开河,过去,我在外面演讲,从来不准备的,上去就说。现在不同了,我会好好地预备一个讲稿,我不能给南大丢人哪。
张英:有一个问题,你已经给出了答案:写作究竟可不可教,大学能否培养出作家?
毕飞宇:一定可教。你要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作家,我把他们叫做野生作家。这些野生作家并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就是靠着生活的积累,最终自成了体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今天的中国,野生作家的余地越来越小了,年轻的一代是很不同的,他们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大学不能培养作家,好吧,大学是培养校长的么?你说,哪一个大学培养校长了?可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校长,你能接受么?
张英:你的《小说课》,看完感觉和王安忆的复旦小说课很像,都是建立在文本感性和理性的分析精读上,这也是中文系要补的一课。通常在高校里面,很多时候你念的文学史,它不是作品史,很少有作品的意义存在。
毕飞宇:是的,你说得特别对,这是中文系需要补的一堂课。我尊重文学史,尊重文艺美学,可是,你如何“进入”文本,这一定是一个问题。我不会夸大《小说课》的意义,也不会妄自菲薄,毕竟,“作品的意义”是第一位的。
张英:这也是为什么写作作为一个学科能成立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课程,我们无法理解好莱坞的电影剧集为什么没有漏洞、为什么会成为内容工业,也无法解释严歌苓读写作硕士以后,成为最受欢迎的编剧的原因。
毕飞宇:写作当然是一个学科。许多人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要问问,数学系能培养几个数学家?哲学系又能培养了几个哲学家?杰出的人才总是少数的,你不能利用中文系的统计学去否定文学教育的价值。作家不可能一嘟噜一嘟噜地出现,你不能用这个逻辑去否定文学教育的意义。
张英:你的《小说课》里有两条线,一个是中国小说,一个是西方小说。开这门课的时候,就找好了脉络吗?
毕飞宇:我不会否定你的说法,中国小说、外国小说,它们确实不一样。可是,对我来说,这不是两条线,它们是一回事。小说就是小说。我们看西方小说,西方人也看我们的小说,东西方的小说早就构成了互文的关系,你不能否认它。作为一个使用汉语的人,我只能是汉语作家,不可能是法国作家或者哥伦比亚作家。但是,我想强调,小说的基础是虚构,它和语种无关,它是一种普世的方法论。对我来说,我没有必要寻找不同的脉络。小说是人类的梦,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梦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回忆、幻境、噩梦、春梦,还能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