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评《制造路易十四》|国王与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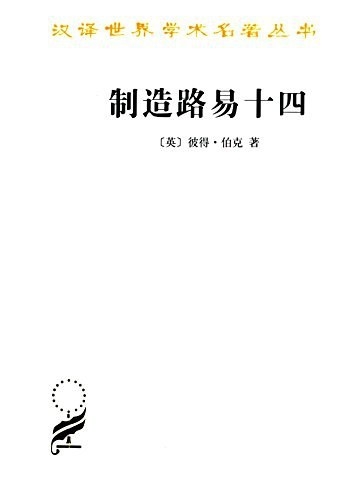
《制造路易十四》,[英国] 彼得·伯克著,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版,318页,29.00元
跟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趣旨不同,彼得·伯克在《制造路易十四》一书中主要采用“解构法”:全书十二个章节根据路易十四形象宣传的编年史安排,以此追溯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间举国上下对其公共形象的制造/塑造历程。作为“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作,本书最具当代启发性的研究是将路易十四的形象工程与历代政治家的宣传手法进行比较研究:如“华盛顿州”命名同“列宁格勒”一样,都是现代社会对领袖人物个人崇拜的具体表征。伯克认为这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恰恰说明礼制、神话和象征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同样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西方社会中特定神话和象征具有一定连续性和稳定性——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在经典著作《国王神迹》中揭示的那样。
伯克本人在一次访谈中曾说,“给《制造路易十四》换个书名,可以叫做《路易十四的政治戏剧》。”这一术语来自德国学者卢尼希(Johann Christian Lünig),后者在《历史与政治的剧场仪式》中将路易十四的表演称为“庆典式的戏剧”,并认为这种戏剧大有必要,因为“形象化的印象在平民百姓中……要比用以启智讲理的语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跟据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伟人制造”论:在这一出政治戏剧中,奢华仪典之功用,是将抽象的权力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形式——全部剧情都是围绕着国王一人进行,他独自高踞在舞台中央,法兰西其他任何贵族,哪怕是王弟及王太子,也仅是为他秉烛奉衣的配角或观众。对此,哲学家拉布吕耶尔(La Bruyere)曾形象地评论道:对君主来说,“华丽的辞藻”以及举办庆典活动和演出活动是“诱惑民众、以假象蒙骗他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使民众昏昏入睡”;犹如古罗马竞技场的斗兽表演,无非是为了“转移民众对政治的注意力”。
作为总导演和主角,太阳王(The Sun King)路易十四自导自演了这出皇家戏剧,把自己塑造成太阳“神”。伯克在书中详细回顾了当时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如何通过诗歌、音乐、戏剧等文学艺术样式,让普罗大众感受到国王路易的神姿英武。比如路易本人矮小且秃顶,但“路易大帝”却高大且头发浓密;路易本人的战绩显然好坏参半,但“路易大帝”却战无不胜,有如战神。的确,文学艺术家常常将路易刻画成阿波罗、马尔斯、赫拉克勒斯以及其他古典时期的神祇和英雄形象,时日既久,路易本人也就自以为是了。
本书原著封面准确传达出伯克的要旨:图片上路易十四打扮得像一位罗马皇帝,雄踞在骏马之上,在地平线的映衬下显得高大威猛,右手坚定地直指前方。但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一场面其实是人造(fabrication)的景观:事实上马匹和国王均是青铜像,一动不动,就像一件过于庞大的舞台道具,等待落幕后被清理。据说该图片的实物便是路易大帝广场的国王骑马雕像,“巨大到可以容纳二十人坐在马腹享用午餐——事实上,在雕像安装过程中,人们的确这么做了”。
如同当时的法国诗歌袭取意大利范本,路易十四的自我包装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其祖母(玛丽·德·美第奇)家族的影响。“祖国之父”科西莫·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圣三一广场竖立纪念柱,并搭建凯旋门,以自旌其功业。同时,由他“钦定”的撰史人不仅领取政府津贴,而且有权调阅官方文件,目的在于编写美化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史。此外,他还组建起佛罗伦萨学院和美术学院,作为舆论宣传的阵地——这两家学院日后也成为法兰西学术院和美术院的样板。
制造路易十四并非是个别人心血来潮,而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正像伯克在书中所说:“全知全能的君主形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官方形象表达了一种集体需要。”换言之,即制造路易十四迎合了当时正在谋求霸权的法国宣扬国威的需要。服务于这样的国家战略,从法兰西学术院到铭文院的文人雅士,竞相为路易十四歌功颂德,既是发自肺腑的衷心爱戴,也是讲政治识大体的明智之举。
在路易亲自部署之下,法兰西学术院于1635年宣告成立,沙普兰(Jean Chapelain)为首席院士。作为诗人和评论家的沙普兰,早年因赞美枢机主教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的一首颂诗而蜚声文坛,先是获得主教青睐,后来又被引荐入宫,成为国王的红人。沙普兰是文坛政治正确的代表人物——1662年,他在向权臣科尔贝递呈的一份报告中宣称,迄今学术院举办的一切文化艺术活动都是为了“铭记国王的丰功伟绩”。
为了进一步强化路易千古明君的形象,1663年,铭文院(全称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后改称法兰西文学院)应运而生,其主要职责是在路易十四纪念章上撰写题辞。艺术史家普雷奥(Maxime Préaud)在《图像王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版画》一文中写道,“从路易统治伊始,他就……认识到图像具有塑造认知的能力。”易言之,一旦民众将纹章、版画及壁画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视作路易的化身,路易十四就成为真正的太阳王——“用仁慈的光芒普照大地”。
铭文院具体负责描绘国王形象,这些铭文本身就是一种精致的艺术样式,要求文辞简洁,笔法端正,因此入选之人皆为当世文章大家,其手笔也远超一般文人墨客。以描绘围攻杜埃(1667)的纪念章为例,其像章正面显示路易十四矗立在堑壕的英武形象,上方铭文为:“作为统帅和士兵的国王”——极力渲染路易甘冒锋镝的英雄气概。又如纪念1681年法军攻占斯特拉斯堡的纪念章上刻有铭文“领受斯特拉斯堡”——“领受”二字大有深意(仿佛十九世纪美国人所谓“昭然天命”,宣示路易的领土扩张实乃天命所归)。再如颂扬1683年炮击阿尔及尔的纪念章上铭文镌刻“雷击阿尔及尔”——这是一种典雅的委婉语,暗指路易十四之赫赫威仪有如主神朱庇特。
在榜样的力量鼓舞下,外省亦仿效法兰西学术院和文学院的样式纷纷建立自己的学院。上述从巴黎到地方的“学院运动”,很快确立起以巴黎为中心的国家文化垄断体制。在名利的巨大诱惑面前,包括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吕里、勒沃、芒萨尔、勒诺特尔、勒布朗在内的文人艺术家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争先恐后进入“体制内”。通过各自的文艺创作,他们为荣耀国王和巩固君主专制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各地各级学院也成为由财政负担的官办文化机构,协助树立官方的政治权威,并负责引导社会思想和舆论导向。
仿佛上述机构在颂圣封神方面并未能满足国王的全部虚荣心,路易又下令从入选院士中再度拣选年富力强之人,组建培训机构(小学院),致力于培养后备人才——伯克在书中有个形象的比喻:他将为君主塑造光辉形象的小学院比作一间手工作坊,从这里源源不断地为全国输送有利于宣传国王崇高形象的作品。1663 年,在国王授意下,仍由沙普兰院士牵头负责拟定一份文人名单,遴选可为君主效劳的文坛耆宿和值得奖掖的新锐之士,并赏赐年金。重赏之下,众人在颂圣之时更是曲尽平生所学,谁也不肯甘居人后。
弗朗什-孔泰战役(1668)取得大捷后,莫里哀赋十四行诗一首讴歌这位“伟大的征服者”;高乃依则在国王从佛兰德凯旋之际,赞美他的伟大行动和他那“令人敬畏的勇气”,并嗔怪国王出征获胜神速,简直令诗人“来不及提笔为一次次胜利献诗称颂”。不仅于此,高乃依还将耶稣会士夏尔·德·拉吕的拉丁文诗歌译成法文,诗中将国王在征战中的统帅作用与圣路易在十字军东征中的历史功绩相提并论——于是国王在诸般头衔之上,又加上了“圣路易”的尊号。
为了强调路易的“天威”,许多时候文人不得不采用曲笔。比如1672年,荷兰人在法军跨越莱茵河后掘堤开坝,国土汪洋一片,从而使法军沦落泽国,难以展开任何军事行动,路易十四由是被迫率军撤出荷兰。老诗人德马雷(Desmarets de Saint-Sorlin)提及此事,宣称“掘堤开坝”乃是国王的英明决策(同时暗示荷兰人根本不可能想出如此妙招)——高乃依则更进一步,否认国王为达成和平协议进行过任何妥协,并断言国王(仿佛圣经中人物)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赐予”荷兰人和平——“你一开口,和平立现你的威力,世人皆见”。
尽管路易性喜阿谀奉承——诚如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在宫廷回忆录中所说:“路易十四的虚荣心永无止境且毫不克制”,但赤裸裸的“颂词”并不能讨得他的欢心。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设法塞进了五十八个恭维国王的形容词——从“可爱”到“虔诚”,结果遭到耻笑。相比而言,大诗人则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Despréaux)在名诗《论国王》(1665年)中仅用一句诗行(“路易十四一到,你们的城墙即倒”),便胜过平庸诗人的千言万语(并因此获得两千金路易的年金赏赐)。
当然,路易对“颂圣”的要求并不局限于法兰西境内。在科尔贝的运作下——这位财政大臣像之前的红衣主教马扎林一样,“不仅监管财政,而且监管文学”——包括“外籍院士”在内的文人齐心协力,将颂扬路易十四的书籍和文章译成德、意、英、荷等欧洲文字,并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出版刊行。路易尤其看重意大利文版本,因为他想要借此机会令意大利的教皇以及都灵、摩德纳等公国对他“刮目相看”——据说他曾为此目的私下贿赂摩德纳公爵秘书希罗拉莫·格拉齐亚尼,要他在公爵面前替自己“美言”。
毫不奇怪,国王的好大喜功注定他有时候难免被人当“枪”使。以废止《南特敕令》为例:这是其祖父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的一条敕令,也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有关宗教宽容的法令。该敕令承认法国境内新教胡格诺派的信仰自由,并在法律上规定该派享有和天主教同等的公民权利。以教士波舒哀为首的耶稣会士一直在暗中怂恿国王下旨,甚至刻意将巴黎耶稣会大学改名为路易大帝学院,以此取悦国王。路易十四于1685年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宣布新教为非法,《南特敕令》亦因此而被废除。大批胡格诺派工匠及商业精英流亡他国,给法国政治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而教士们则奔走相告——波舒哀在演讲中称颂路易十四为“迪奥多西一世再世、马西昂再世、查理曼再世”。
既然是君主专制,一切出于“圣意”的重大决策和法令断然容不得他人置喙。据史书记载,科尔贝遵旨“取消了史学家梅泽雷(Francois Eudes de Mézeray)的年金,因为他曾公开非议政府征收的人头税和盐税”。另外,极有个别胆敢腹诽的文人遭举报后也被逐出法兰西学术院——如果说年金制是一种施恩制度,那么学院制则是恩威并用,其严厉的“规训与惩罚”加速推动了文人身份的廷臣化。而规训的对象也不仅限于文人,而是进一步扩展至科学技术人士。1666年,奥比涅克修道院院长发表演讲,恳请政府批准建立法兰西科学院,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会对民众思想及心理层面产生可操控性的影响。“在领导国家的技巧方面,科学不仅仅起到指导的作用,它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使民众顺从君主的必要法则……因此开明君主通过支持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悄无声息地为民众套上一副隐性的枷锁,而且那是一副镶着金边的美丽枷锁。民众为科学的光环所倾倒,在丝毫感觉不到任何束缚的同时,却被牢牢地掌控,心甘情愿地沉浸于对国家的顺从之中。”——由此打造出一种由官方扶持的人文与科学相结合的精英文化,这一种文化与政治天然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身在其中之人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对文人进行管控的同时,路易十四对书籍出版行业也实行严厉的控制措施,禁绝“坏书”(mauvais livre) 在国内出版流通。由黎塞留创办的、每周两期的《法兰西公报》垄断皇家政治信息的发布,但在报道政治事务时官腔十足,按照政治需要取舍和剪裁信息;每月一期的《时尚信使报》则以巨幅版面登载国王的活动:举凡生日庆典、接见使节,以及慰问巡察等日常事务,无不加以详细报道。相反,“投石党”(Fronde)时代一度盛行的地下宣传手册一律遭到取缔,其作者被放逐——如著名无神论者、法国启蒙运动之父培尔(Pierre Bayle) 。面对这一“大清洗”的严峻形势,众多印刷出版商在意图明确的遏制方略下被迫宣告社会性死亡。万马齐喑,专制政府成为社会唯一的动员和组织力量,而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则遭到严重压制。诚如托克维尔所言,没有政府的首肯,哪怕成立最小的独立社团也不可能。“要言之,它(政府)丝毫不愿公民以任何方式,卷入到对他们自身事务进展的监察之中。它宁愿要贫乏也不要竞争。”
取代上述地下宣传册的是官方刻意打造的“蓝色文库”。根据历史学家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的说法,此类图书“向读者展现出一片奇景之地,那是一片使广大农民远离现实生活困苦,不再忍饥挨饿的世外桃源;更是服从日益沉重的社会道德枷锁,身受学校、法律及警察机构严密管控的市井小民之辈短暂的栖息之所”。因此,透过神话故事和浪漫的人物传奇,这类书籍的普及仿佛给整个社会了注射了一剂“镇静剂”,成为向民众灌输宗教、道德及社会规范的有力工具。
在以上各类文化活动中,路易不仅是幕后推手,许多时候,他甚至走上前台充当“裁判官”。以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界最著名的“古今之争”为例。在十七世纪以前,“古典(classique)”一词多用于形容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经典。时至路易十四时代,崇尚希罗经典的院士如布瓦洛、拉封丹、拉布吕耶尔等与反对派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丰特奈尔等人发生激烈论战。1687年,佩罗在法兰西学院当众宣读其诗作《路易大帝的世纪》:有感于崇古派作家在论战中的声势,佩罗在诗中强调,只有崇今派作者才能准确把握路易十四王朝史无前例的辉煌意义。作为《灰姑娘》《蓝胡子》《睡美人》等经典童话的原创者,佩罗是崇今派的坚定捍卫者,为日后法语文学及法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方向。然而在当时,他的这一大胆“妄断”却引发了文坛权威人士的强力反驳。为首的便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诗人拉辛(Jean Racine)。
1661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拉辛写下两百四十行的长篇颂诗 《塞纳的水仙》(La Nymphe de la Seine),题献给法兰西王后。这首颂诗紧扣国王入城仪式“和平凯旋”这一政治主题,得到沙普兰的激赏。1666年,拉辛的悲剧《亚历山大大帝》出版,卷首题辞“谨以此书献给路易十四国王”。1674年,路易十四亲临观看拉辛悲剧《伊菲革涅亚》首演,显示出对诗人异乎寻常的垂青。1677年,拉辛完成另外一部著名悲剧《费德尔》(Phèdre),随后与布瓦洛一道被任命为路易十四的史官。1678、1683和1687年,拉辛前后三次跟随国王出征根特、阿尔萨斯、卢森堡等地,为历史著述搜集战争史料。1690年,拉辛被任命为国王侍臣。1694年,又拔擢担任国王私人秘书,其荣宠可谓盛极一时。
拉辛与布瓦洛交情深厚,其悲剧创作实践也是布洛瓦古典诗学理论的明证,二人同为崇古派主将。然而不幸的是,拉辛这位一向善于体察圣意的御用诗人和史官这一次却和布瓦洛一样站错了队。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路易十四成为这场大论辩的终结者。在路易的直接干预下(据说国王曾单独召见布瓦洛,夸奖他的诗艺,并表示愿与诗人切磋诗艺——“记住,我永远有半个小时是留给你的”,令后者感激涕零),崇今派大获全胜。事实上,无论是佩罗还是拉辛,一干当事人无不心知肚明:这一场论战并不仅仅是文学争论,而是思想战线的交锋。他们完全明白论战的政治意义:如果路易大帝时代比奥古斯都时代更好的话,那么路易十四自然也就比奥古斯都更强。说到底,国王才是这一场古今大战的顶层设计师。拉辛聪明一世,到晚年却选择站在国王的对立面,其结局令人唏嘘。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评价拉辛说:“路易十四欣赏他的出众才华,任命他为宫内侍从,让他数次伴君出行,几番龙体欠安时赐他在国王寝室守夜的殊荣,并授予他丰厚的俸禄。然而,拉辛唯恐不能讨君王欢心,乃至为此郁郁而终。”——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路易晚年由于穷兵黩武,国库虚空,太阳王之封号早已名存实亡。目睹路易十四对荣耀的渴望致使大量臣民陷入一种“原始的、无政府的悲惨状态”,拉辛“哀民生之多艰”,乃向路易上书谏言:国王的成就已十分辉煌,堪称千古一帝,因此当下该是与民生息之时。诗人本是一片拳拳忠君爱民之心,不料逢彼之怒。据说路易十四览书后痛斥书生干政:“他懂得写好诗就什么都懂吗? 他是个大诗人就想当大臣吗?”至此,诗人此前享有的恩宠悉数被取消——拉辛与国王日益疏远,并被禁止出入宫廷——伏尔泰所谓“郁郁而终”,或由此而发。
其实,从路易十四角度看,如果说文人拉辛此前论战中的站队错误尚可谓其情可原,此后对国王治国理政方略提出讽喻则其心可诛——是可忍孰不可忍。说到底,被制造的太阳王亦只是七情六欲的凡人,正如伯克在卷首引帕斯卡尔名言:“对某人或某个特殊人物所怀有的崇敬之情实乃源自想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