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叛逆者》原著作者畀愚:唯有家国与爱情不可辜负

43集的影视剧《叛逆者》在更新至29集的时候终于出现了《叛逆者》原著中最开头的情景:“中弹之后,林楠笙开始失去知觉。他不知道自己是躺在一口棺材里离开上海的,也不知道那架日本运输机在启德机场一降落就有一辆救护车载着他呼啸而去。”

《叛逆者》29集出现的中弹情节是书中的伊始。
从开播以来,这部集结了朱一龙、童瑶、王志文、王志等演员的讲述不同政党的情报人员在复杂的斗争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真真假假、生死离别的年代谍战剧就踏上一条“爆火”之路,而这部剧“最初的起点”是畀愚的一部中篇小说——《叛逆者》,这部同名小说集中共包含了四个故事:《叛逆者》《邮差》《氰化钾》《胭脂》。

书影
每一部“爆掉”的电视剧的余波都会深深震荡跟它有关的一切人:从演员到导演到原著作者,一部剧多大程度地再现原著要看造化,有照本宣科者,也有完全只是借个梗概者。但是《叛逆者》有趣的点在于,包括导演周游在内的7位编剧对原著人物和故事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最明显的就是将书中的“顾慎言”一分为二:拆成顾慎言和陈默群两个人物,而王副站长在原著中着墨不多,但在剧中非常出彩,原著中,林楠笙受困于爱情,和朱怡贞和蓝小姐有很多感情纠葛,但在剧中,林楠笙这个人物更纯白、也更神通,符合一部爽剧大男主需要具备的那种“美强惨”的人设。
我们可以想象《叛逆者》原著是一座乐高积木搭成的房子,而影视剧《叛逆者》则是将这座乐高房子拆成一块块积木重新搭,一些桥段出现的位置会有很大的偏差,人物的故事线索也被拆开重置:比如书中,林楠笙和蓝小姐是恋爱同居的;因为顾慎言这个人物一分为二了,他的复杂性其实被两个更为显性的人物分担了,这就冲淡了这个人物的张力;林楠笙中弹以后性命堪忧,在原著中有种亡命天涯的不羁,没有剧中的那种执着和脆弱感。

朱一龙诠释的林楠笙。
但是有趣的是,《叛逆者》剧作又是那样尊重和承续了原作的核心要义,比如对于“叛逆者”题意的解读:
《叛逆者》不同于一般的年代剧的所谓波澜壮阔、还原史实,无论是剧还是书,都不是向外发散的,所有的标的都指向人的困境、人的信仰和人的选择,有一种向内的收缩性。所有的人都站在一种强烈的不确定和晦暗不明的处境中,牵动着读者和观众的是对他们身份的猜测:“陈逆”还有没有回头路、林楠笙什么时候选择成为共产党……
但是从原著小说《叛逆者》中,你或许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最简单痛快的答案。人的变化在极其细微处,就像你抛出的一个“你为什么而爱一个人”这个天问,“你究竟相信谁,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的理想是什么?”也需要在一次次和现实的对撞中逐渐确认,而在一个混乱的时代,找到一个能透出光亮的出口又尤为困难。

左秋明

以书中的几个角色来看,左秋明在书中有非常惨烈的牺牲:被日本剖开肚子拿走他吞下的情报后,左秋明选择用手掰开伤口把自己的血一点点放干死亡。林楠笙是在后来看到左秋明曾见过老纪的照片,才知道自己的挚友可能早就投向共产党。纪中原告诉林楠笙的是:“他不是为谁工作,他只是在尽一名中国特工的职责”;而书中顾慎言的一个重要的人生指南是:“任何组织,一旦把忠于个人或者某个集团作为精神支柱,今天的悲剧就在所难免”;孟安南这个人物的痛苦则在于“自从跟随顾慎言由越南来到香港,他踏上中国这块土地快有十六年了,顶着一个军统特工的名头,却从没为他们干过一件事。相反,他每天在做的,正是他父母未竟的事业(孟安南的父母曾经都是胡志明的追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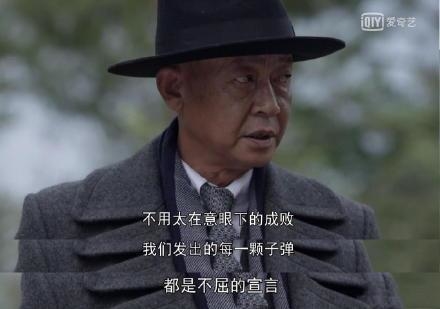
王志文饰演的顾慎言。
正如孟安南问朱怡贞的那一句“这个人的身份对你就这么重要吗?”这是《叛逆者》故事中所有人的痛苦和悲剧。
最近,澎湃新闻也专访了《叛逆者》原著作者畀愚。
这个小说中所谓的叛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
澎湃新闻:可不可以谈一下是怎样构思《叛逆者》这个故事的。比如是否是读到某一段历史、或者是某一位人物,让你很有感触?或者是最开始可能这个故事只是随手写下的一个故事片段,然后逐渐丰满的?
畀愚:写这个小说之前,我刚完成了《邮递员》,受到了一些影视公司的青睐,也开始明确了在那个阶段的写作方向。当时,恰好有人找我去改编《潜伏》的电影版,可能是电视剧太精彩、太深入人心的缘故吧,就最终放弃了。不过呢,一个人物形象却开始渐渐清晰,就是林楠笙。其实,在我看来,林楠笙就是《邮递员》里徐仲良这个人物的某种延伸。《邮》是讲一个少年的成长,在国破家亡后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怎样在救亡斗争中形成坚定的革命信仰的,唯有家国与爱情不可辜负。林楠笙也是一样,他在茫茫的暗夜里寻着那点光,在血雨腥风中寻找光明,最终走向光明。他同样是唯有家国与爱情不可辜负。
我经常把写小说比作是一次孕育,可能就是一点点的外因进入,与你脑袋里一直存在的那些思绪碰撞、结合,就像着床一样,渐渐会有了故事,有了人物,这个故事与人物慢慢地成型,慢慢地丰富起来,一个小说就形成了。
澎湃新闻:之前访谈中你有介绍过,顾慎言是唯一一个有原型的人物——戴笠的助手余乐醒。对你而言有原型的人物(即顾慎言)和完全虚构的人物写作起来各自的难点是怎样的?
畀愚:说顾慎言的原型是余乐醒,这也不尽然。我只是需要这样一个人物,作为背叛的一种类型,他恰好与余乐醒有着相似的人生背景,都有留学的经历,又都背叛过初心。其实,民国这个时代是非常独特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东西方文化两相交融,又相互挤压。我只是把一个时代的特征集中到这样一个人物身上。
难点倒说不上有,对于一个职业写作者来说,塑造一个人物无非就是这个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澎湃新闻:接上一个问题,在书中,因为有汪精卫、丁默邨这些“实有其人”的人物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庆祝香港停战协定签署这样的节点,都会让读者患有“考据癖”,将这些真实的人物和背景写进小说中,你是怎样考虑的?
畀愚:我写了十年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其实写的就是大历史下的小人生,那些被历史车轮无情碾压的人们。写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过“考据”什么,但把虚构的人物与事件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是我的个人喜好。小说不就是个真实的谎言吗?要做好它,就得让每一个人信以为真,像个说书人那样告诉人们,在那些历史的瞬间,有这样一些人,是以这种方式、这样地生活与生存着的。因为,历史的瞬间往往也是最能改变一个人全部的人生,那些蚍蛶般的个体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我想,书写他们就是写作的意义。

澎湃新闻:因为现在故事叫做《叛逆者》,本来以为只是林楠笙“叛逆”,但是读书下来发现很多人物在特定的情境下其实都有叛逆的倾向,你怎样解读“叛逆”这个题意呢?
畀愚:笼统地说,叛逆就是人性中的一种,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叛逆的基因。比如,我们把青春期又叫叛逆期。
这个小说中所谓的叛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选择权应该是作为人最起码的权利吧。只不过,在那样的时代里是不容易的,选择的结果往往是会以生命与名誉为代价的,但是他们还是从各自的内心出发,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在不同信仰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这部电视剧曾出过一份海报,上面印了两句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想,这是对这小说中“叛逆”这个词最好的诠释了。为了追寻光明,哪怕是去飞蛾扑火。这种血性与勇气,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
澎湃新闻:在小说《叛逆者》中也可以看到所有人的亦敌亦友的关系,比如顾慎言建议林楠笙“参照中共的情报网体制的组织结构”,需要日本空军的情报时,中共的情报员朱怡贞需要和军统的林楠笙交换情报。还有很反讽的桥段,比如小说里,丁默邨和顾慎言的一段谈话:
你要救的是什么人?
一个下属。
为了一个下属,你深更半夜闯进我家里?
此人现在在仁济医院的急救室里。
我可以帮你让他永远闭嘴。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
丁默邨笑了,说,慎言兄,你本质上还是个共产党人。
畀愚:这是事实,也是有史实可以支撑的。我想,人类的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有一个模糊地带的。我们稍稍了解一点历史与政治的话,就会理解,当孩子们已经打得头破血流时,他们的家长可能还在牌桌上淡笑风生。
当时的上海更是这样,远东的情报中心,每个阵营里都是充满了各种博弈,各种交易层出不穷。套用那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利益。

林楠笙是一叶孤舟
澎湃新闻:我们可以谈谈具体的人物,剧中的林楠笙被塑造得更纯净,这也是很多谍战剧中喜欢的、一个清清白白的新人,一步步成长蜕变,但是在你的故事中,其实林楠笙和朱怡贞在大学里就有一段显得有些露骨的师生恋,被女方母亲拆散的六年后与朱怡贞接头,又有非常直接的同居,还一度去风月场所,为什么会塑造这样一个没有被“纯化”的林楠笙?
畀愚:其实,我们都明白,性是不肮脏的,肮脏的往往是思想。两个情投意合的男女间一定要守身如玉,这才是真正爱情吗?一旦两情相悦了,这爱情就有杂质了吗?我想肯定不是的,有杂质的是我们的偏见。
首先,我塑造的林楠笙是一个人,有血有肉。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人的,东西方的神话里好像也没有。是人,他就得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我们还可以试想一下,当一个人在无望的时候,每天面临着死亡,晚上睡下去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到太阳,他会怎样去做?
另外,我们再去回顾一下,民国是个怎么样的社会?它的风气、风尚与风化是怎样的?其实,那个时代里的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回忆录、传记、日记、信札。通过那些,我们就可见一斑。所以,我这样塑造了林楠笙这个人物,只是为了让他更像一个人,更像一个那个时代里、那种处境下的真实的人。

澎湃新闻:还有就是林楠笙的改变感觉更多是被身边的人指引,尤其是顾慎言、朱怡贞,然后他好像也花了很多精力与两位女性周旋,好像没有太多笔墨是落在他自身的觉醒,让林楠笙最后说“我是你们当年费尽心机想让我成为的人”显得有些突兀,林楠笙好像更像是一个串起各种人物的引子。
畀愚:我想,觉醒肯定不是一个人一觉醒来就大彻大悟了。首先得是有所发觉,才会开始清醒、有所认识。林楠笙身处在一个黑暗的制度里,他从左秋明、顾慎言的死亡里,从蓝小姐的遭遇里,看清那个制度的黑暗与龌龊,而对爱情的追求也逐渐成了他对光明的向往。
另外,一个人觉醒也好,改变也好,确实是一种心理过程,但这是需要外化成行动的,用行动来证明这种变化。林楠笙是个特工,是个行动者。他的行为就是对自己觉醒最好的证明。应该说,林楠笙是茫茫大海里的一叶孤舟,他在黑暗中行进,经历了各种风雨后,找到了海平面上的那缕曙光,于是他有了前进的方向。同理,我们也一样,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会经历各式的人与事,最终来呈现与完成一段属于我们的人生。
另外,熟悉我的读者都了解,我对人物是基本上不作心理描写的。我不必要告诉读者,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我只会用他的行为来表达他的内心。我想,这也是给了阅读者去了解与体会这个人物的空间,而不是先行地去框定他们的思维方向。
一千个观众有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不是更好吗?让读者以自己的理解来丰富这个人物。
澎湃新闻:朱怡贞好像是故事里最坚定于自己的组织和信仰的人,您写作这个女性角色时怎样考虑?
畀愚:应该说,这个小说里的每个人都是坚定的,只不过是发现当追寻的信仰与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偏差时,他们作出的选择不同。我的理解是,这也是一种坚定,需要更大的勇气。
朱怡贞只是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经历了生死考验、经历被误解、饱受了爱情的煎熬。正是这些磨难,使她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更加的初心不改。
澎湃新闻:无论是书中还是剧中,都有很多体现文学和文化的内容,比如剧中,老纪曾一度伪装成是图书馆的管理员,顾慎言对接的一个“中间人”是旧书店的老板,所以暗号被用书传递,出现了许多古籍;林楠笙为了接近朱怡贞,读了《铁流》等书籍;书中,顾慎言喜欢读波德莱尔,你也写到顾慎言手握着一卷宋版的《忘忧清乐集》,无论在读小说还是看剧的时候,虽然这些书承担着用其中的标注和密码母本破译密报的作用,但在紧张的谍战故事中,这些内容有一种冲淡和风雅。甚至剧中因为拉长了故事,更强化了这种风格。
你的这种设置是否是个人趣味所在?还是比如这是史料中有记载桥段?
畀愚:个人的趣味基本上没有。我对诗歌的热情也有限,根本不会下围棋。我只是需要顾慎言这个人物这样子,有学识、有涵养,他还喜欢喝白兰地、抽雪茄,听京剧。他就是那个年代是的一个“海龟”,在为国民政府工作,但又恪守着传统。纪中原在小说中的人设是朵云轩的篆印师,在福佑路上开了家装裱店,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手工匠人的结合体。那个时代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生活所迫也好,怀才不遇也好,但对纪中原来说,这只是一种身份的伪装。
说句题外话,有一次我逛古玩市场,看到一些二三十年代的饭店里的账本,上面那些字写得真的是好,堪比我们今天的书法家。
提供一个思想的起点就够了
澎湃新闻:不知道你是否有看剧,或者剧方跟你沟通,现在剧中,书里面的顾慎言其实是拆成了两个人——陈默群和顾慎言,你怎样看拆开的这两个人物?
畀愚:我还没看,我没有追剧的习惯,我是想等播到差不多时,集中两三天一口气刷完它。所以,我也不清楚陈默群这个人是怎样设定的,但我一位朋友很赞赏王阳的表演,说从他演的那个人物的眼神里能嗅出血腥味来。哈哈,等我看的时候,我一定要验证一下。
不过,也有看过了全部剧集的朋友告诉我,说越到后面越精彩。

陈默群与王世安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感觉是,剧中好像是对小说中的故事进行了拆解,虽然和原来的结构和故事有了很大的偏差,但总是可以看到书中故事的影子,你怎样看待、或者是否接受现在的影视剧中呈现的这个版本?
畀愚:虽然没看,但这里不存在接受与不接受的问题。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编剧还是制作方,他们所付出的精力与时间,一定是为了让故事更精彩,人物更丰富,让观众更喜欢。现在的收视率也证明了这一点。昨晚就有网友私信我,发了份图表给我,上面显示的收视率都破二了。我很高兴。
澎湃新闻:现在小说改编影视剧有很多种形式,有的是用很短篇的小说来改,就是借一个故事梗概,有的则是“还原”原作,比如《那不勒斯四部曲》《使女的故事》,你作为创作者,更倾向于自己的作品被以哪种形式改编?
畀愚:我自己就是个创作者,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在跑马场里跑马。既然是创作,就必然需要有天马行空般的创造力,抛开一切的束缚,朝着目标一往无前。我以前就说过,作为一名原著作者,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内核,就好比拿出了一把茶叶,你想把它泡成一杯什么样的茶?用什么样的杯子?倒多少的水?这水多少度?其实已经不是那把茶叶的事了。我可能更关心的是物尽其用吧,就是我的这部小说能被充分地运用,能够提供一个思想的起点,这就足矣了。
澎湃新闻:因为你一直关注民国这个阶段的历史,也写了很多故事,可不可以谈谈《叛逆者》在你的创作中是否是比较独特的,还是只是很幸运被编剧和导演们看到并改编的?
畀愚:对我来说,它也不算独特吧。在我看来那部《江河东流》或可算独特,最近刚出版,讲了一个人的成长蜕变与自我救赎,是个堂吉诃德式的故事。
我整整十年一直在写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都是以中篇为主。因为我喜欢电影,所以这十年里也一直在尝试小说电影化的创作,就是让文字更多地能呈现出一种画面感,在故事的处理上更接近于电影的表述。
对生活有所经历的人都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么多幸运的。所有你看似的幸与运,其实都是付出了无数努力与汗水后的结果。我们不是常说吗?机会只降临在有准备的人身上。
澎湃新闻:你的写作让我有一种观感是,人物直接出场,不介绍人物和铺垫背景;而且对话没有标点,让故事推进地很快,你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一种写作?其实是会给读者造成一些阅读的压力。
畀愚:每个人的阅读感受都不一样,这也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吧。比如,某些事物落在某些人身上是压力,在另外的人身上可能是快感呢?比如跑步,我就不喜欢,觉得累,但有人会上瘾,一天不跑就无所适从。存在皆合理,这话不一定准确,但既然存在了,那肯定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作为一名写作者也好,作为一部作品也好,我从不奢望被所有的人喜欢、接受。让喜欢你的人去喜欢你,让讨厌你的人去讨厌你,这不很好吗?人生就是这样子的,让每个人自由地选择,而我们只需要坦然地去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