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
 2021-06-05
2021-06-05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
文 | 于文舲
谁都不会否认,“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的形态包罗万象,有清新内敛的,也有轰轰烈烈的,有温情朴素的,也有匪夷所思的,如果要为“爱”建一座博物馆,每个小格子里放一样标本的话,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恐怕都容纳不下。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于是人们用文学和回忆来实现它。像《春山谣》这样的小说,大概就是博物馆里并不起眼但余味悠长的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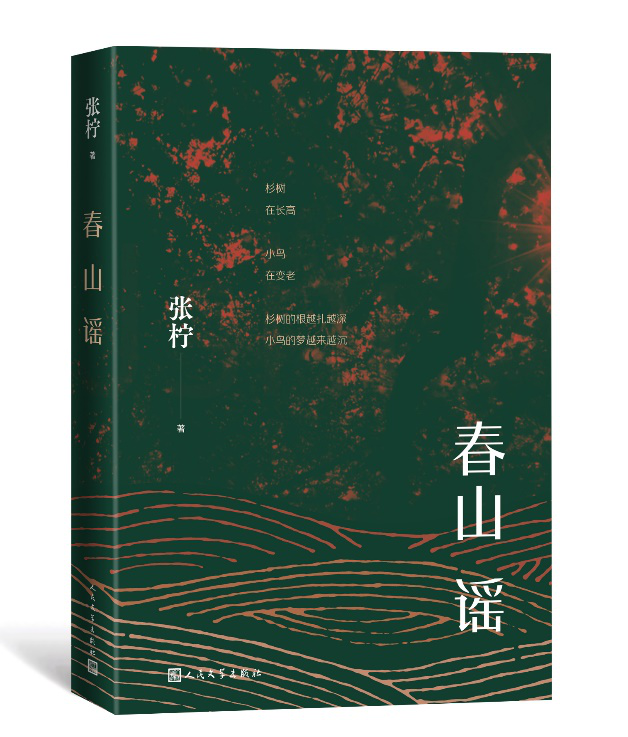
张柠《春山谣》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3月
《春山谣》书写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生活。一群上海青年,来到长江中游一个叫作春山岭的乡村,新的环境让他们感到震撼,新的生活时刻在考验着他们。与此同时,原本寂静的山村、小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乡村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交织,在青年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增加了文学内部的张力。这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无论当地人还是外来者,面对人生轨迹的突变,人们心底的“爱”又与命运,与处境,与利益,与关系,与机遇,与所有的一切因素牵绊在一起,那么当然可以说,写“爱”就是写一切。他们“爱”的方式,就是他们处理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方式。
小说里有几对典型的情感关系:
首先是上海青年顾秋林与陆伊青涩懵懂的爱恋。顾秋林的手风琴和陆伊的歌唱舞蹈,他们的书信和诗歌,他们相互试探的眼神,还有那些说出或没有说出的心里话,始终飘扬在大地上空。这是小说中最纯粹的情感,它来自萌动的生命力,是对纯真、善良和美的向往。它看似犹疑、脆弱,总是被刻意地压制着,但生长的冲动是怎么也压制不住的,爱与被爱的冲动像无处不在的星火,闪耀,跳动,给人以希望。
其次是春山镇医生马约伯与李瑰芬跨越生死的分分合合。当冲动逐渐消失,人生沉淀下来的是什么?曾经赫赫有名的军医,患难夫妻,在战火中生死与共,他们如今的平淡、默许与愧疚,离婚又合葬,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其实也都是爱的应有之义。马约伯要面对的,不仅有历史的迷雾更有现实的无奈,他选择承担一切,这是一种苍茫的情感,如乡村一般深厚扎实,他们定居在春山岭,而这里,也是他们的归宿,他们爱的最终的见证。
此外还有林场场长彭击修与游仙桃、徐芳兵的纠葛。如果说前面两种爱情相对古典,它们关乎人生的来路和去处,更具有抒情性的话,三十岁的彭击修在爱情中的左右摇摆则更具有社会性,更理性,更复杂。这里凸显着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身份上的不甘与情感上的不舍、不得相互纠缠,他越是想战胜情敌,就越是战胜不了自己,越是想把握自己的人生,就越是在爱的漩涡中进退两难。
当然小说所写的不只有爱情,还有亲情、友情,爱也不光是温暖和甜蜜的,还常常夹杂着一些酸楚,惊慌,甚至是残酷,五味杂陈。但还不仅仅是这些。闻一多曾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春山谣》正是用诗意的笔调、饱满的情绪,用一段段散发着旧日气息的情感故事,诠释了这一点。作为天赋的爱,是从生命中涌出来的,它绵延在时间里,成为一切行动的底色,也成为小说的基调。这就是文字的情感性,或者说诗性。谁是写就这一切的诗人?小说主人公、文学青年顾秋林是。在他背后,千千万万的同代人也是。这是一部关于“50后”的青春小史诗。纵使命运有轻重缓急、高低起伏,但这背后总有什么东西,在抚慰着我们。
也不只是抚慰,还有理解。当我们发现,小说遵循的逻辑就是爱的逻辑,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终能够体味到幸福的人恰恰是孑然一身的顾秋林。他内心的爱最完满。我们说现实无论如何都会有缺憾,而顾秋林的爱,在回忆中。现实剥离了他的一切,迫使他走进回忆,而回忆修复了一切。这是一种向内的爱。由此我想到了张柠的上一部长篇小说《三城记》,在塑造“80后”主人公的时候,小说寄寓的是一种不断打开自我、切实地去爱的能力。向外的爱,也需要勇气。同样是写青春,“爱”却不同,它从一种需求、能力,还原成生命力,更成为一种向往。我惊讶于不同代人爱的方式如此迥异。那么能够说,我们真的理解“爱”,理解“人”吗?或许只有回到时间里,才能找到答案。
把人还给时间,把文学交给记忆,用本心去聆听一首旧日的歌谣。
“此后的几十年里,顾秋林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那是三件很小的事,但也可以说是三件很大的事:卖香烟,想陆伊,写诗歌。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伙伴,有人发财了,有人亏本了;有人升迁了,有人下岗了;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只有顾秋林没有变。他生活着,爱着,写着爱的颂歌。”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部书写一代人青春的小史诗,真正的主题是爱。

张柠,作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春山谣》,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感伤故事集》,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等。
附:张柠创作谈
《青春都一样,命运各不同》
这是我的长篇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一个青春故事。《三城记》是子辈的青春故事,《春山谣》是父辈的青春故事。父子两代人,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遭遇的问题截然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截然不同。他们的梦想天差地别,一代人渴望着倦鸟归林,另一代人试图上天入地。两相比较,饶有趣味。其中隐含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刻印记,隐含着命运在不同代际的身体和心灵上镌刻的印痕。在此仿用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句式:青春都一样,命运各不同。
小说写了一群十五六岁的城市青年,离开父母和家乡,来到长江中游一个叫春山岭的地方,跟那里的农民、回乡青年、村镇上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一起生活。从熟悉的城市迁到陌生的村野,从吃饱喝足的日子到缺衣少食的日子,这对他们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是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用汗水、眼泪以及身体中的每一点能量,与大自然的能量发生交换。他们吃的每一粒谷子和每一棵菜蔬,都是这种能量交换的结果。他们离开石头街道来到泥土和草地上,亲见谷子发芽,秧苗长成,稻花飘香,谷粒灌浆,稻子金黄。他们感受到了这种能量循环过程中蕴含的道理,不是书本上的道理,是镌写在大地和泥土上的生命的道理。他们也尝到了劳累和辛苦、孤独和悲苦的滋味,看到爱恨情仇的生长消息,遇见了人的纯洁和愚昧,感受到了命运的侥幸和无奈。经过自然的或者诗的教导,也经过残酷的人心的历练,从五谷不分的懵懂少年,成长为自食其力的青年。
我想强调的是,《春山谣》写的不只是那些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还有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当地农民和回乡青年,还有机关公职人员、医生、教师等村镇小知识分子。农民和乡镇工作人员的故事篇幅不小,也激起了一波波叙事高潮。当地农民、回乡知青、公职人员,并不是顾秋林、陆伊、程南英等知识青年的陪衬和道具。他们携带的习俗、文化、生活、劳作经验,同样是我着墨很多的地方。通过他们,我试图复活20世纪70年代的某些历史场景和生活景观。所以,《春山谣》既可以说是青年的成长故事,也可以说是乡镇小知识分子的命运故事,更是传统乡土熟人社会里的农民遭遇陌生人和接受陌生文化的故事。三条故事线索扭结在一起,构成一幅20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横断面的画卷。
作为那段渐渐被淡忘的历史的旁观者,我把亲眼目睹过的生活场景和经验,转换成小说中的故事场景和艺术细节。回忆中的碎片图案,通过记忆组合起来,转换成小说中跳跃着的艺术情节。回忆和虚构互相催化,让春山岭的草儿长了出来,鸟儿飞了起来。一边是抽茧剥丝,一边是穿梭编织,逝去的青春在故事中得以复活。艺术劳动的整个过程,携带着欣喜和愉悦,也伴随着感伤和悲痛。除了感恩,别无言语。顺便预告,正在写作的《江东梦》,讲述的是顾明笛的祖辈的青春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