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非虚构写作的王尧,如何突破与瓦解想象中的“八十年代”?
 2021-05-19
2021-05-19

张烨、耿占春、焦典获“2020中国·星星年度诗歌奖” | 张怡微上图讲座谈现代散文与情感教育 | ......


在随笔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出版十余年后,王尧在《雨花》推出了“时代与肖像”专栏。专栏包括《我的腿迈不出去》《李先生的文言文》《奶奶和她的小镇》《那是初恋吗》等十二篇文章。涉及人物与事件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上卷多有提及。专栏的面世,足见作者对于那个年代的事物与记忆还有着未及展开的部分,在十余年后,再以回溯的文字予以铺陈和巩固。我们不妨把专栏看成是《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一书的“续写”,也是作者对于人与乡村、时代、文学等关系命题的精神“反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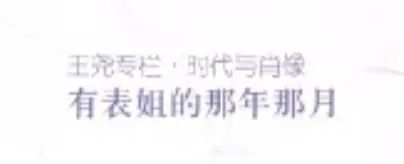
0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于农村的知识分子,个人生活无法回避的一个沉重主题必定是“逃离”农村。面对与生俱来的“不平等”,逃离是对于生存压迫的反抗,对于命运的绝地反击。撰写《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一书时,王尧试图在文本中重返故乡,却深感“无能为力”。三十年来背井离乡的感觉不曾淡去,作者声称:“是我想逃离那个村庄的,那个年代不想离开故乡的人肯定是狗日的。”
逃离的途径寥寥,“从军提干”或者“书包翻身”,对于普通的农家子弟都殊为不易。我们也可以从文本中体会一下《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作者对于“逃离”的渴望:我已经无法说清楚那个村庄是什么。在重新返回我生活的历史时,我只是清楚地知道,我想离开它。

年轻人逃离乡土的愿望是如此一致而迫切,而他们萌生逃离之意的源头和起点,又似乎与某一个有着“市民”户口的女同学有关。城里女孩赋予“城乡差别”一词具体而微的内容和色彩,还有重量。城市文明的渗透与入侵给沉寂的乡村生活撕开了一条口子。这里的贫穷、单调和乏味,以及乡村少年根深蒂固的自卑和看不见未来的恐惧,让他们逃离的念头开始萌芽。“知青”这一极具时代特色的群体现象,又在乡村少年的“逃离”计划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远方的城市有效地刺激并勾引起主体的内心欲望,身份、物质、权力等等……知青短暂的到来和离去,在“我”内心掀起了“风暴”:“知青们走了,他们让我隐约地明白,与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种命运,远不如努力地逃离土地,去试着改变一下什么。”
作为逃离乡村的成功者,逃离不是终结,而是“故事”的开始。逃离故土之后带来的亲情、血缘等世俗伦理关系的疏离,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引起主体不可遏制的愧疚情感或忧患意识。远离乡村的知识分子于是开始一遍遍地文字返乡,精神返乡。同时,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返乡的无效和虚伪。《时代与肖像》这样的作品,正是对于蔓延一时的文学“怀乡病”等现象的批判和证伪,一方面揭示了那样一种“不假思索”的书写,唤起文学的警醒,免于沉溺在平庸的返乡和怀旧之作,淹没于个人生活的鸡零狗碎当中;同时也是从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命运的重新打开、审视和清理的过程。

王尧有感于自身独特的文明背景,那就是祖辈曾经生活过的小镇和老街——虽然不是亲历,但与小镇相关的历史始终是“拖在我身后的背影”。在祖辈居住的小镇上,“我”被人称作“二少爷的孙子”或“闻二小姐的孙子”,小镇的繁文缛节都渗透在“我”家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大家都尊奉的规矩,就是“小镇文明的面貌之一”。至死都要留在小镇的“我奶奶”,“其实也在延续一种和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是一种生活秩序”。在城市和城市文明距离自己还太远的时候,“小镇文明”更早地在“我”心中确立其地位。“城”与“乡”的差别,和“镇”与“乡”的差别几乎是同质化的,同样可以让“我”这个乡村之子在面对它时“产生自卑和耻辱”,同样可以“彻底摧毁你的内心”。只有在离开乡村,进入更广阔的城市空间后,“我”与小镇的紧张关系才得到了淡化与和解。在通往乡村的“河码头”被废弃的同时,承载着小镇文明的“老街”也慢慢消失了。
文字的返乡可以视作作者心理的代偿,但这样的返乡总是“形而上”的,是一种虚拟的“切肤之感”。“我”的回顾与张望只是试图重现此前乡村与小镇的历史,不过那“历史”只能在记忆中被塑造,而无法具有现实的呼吸。
02
十余年前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是作者的“觉醒”和“清算”之作。这是作者在脱离乡村三十年后为表达乡村经验而发出的声音,可以视作表达欲望和话语权的觉醒。作者的诉求是简单而直接的,那就是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让包裹得太紧的自我得以裸露——“我现在只想用写作的方式清算自己,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总习惯清算别人。”这样的写作初衷自有其时代背景。作者的创作是有着自己朝向的,就是“那些八十年代的统一论述和宏大叙事”,与前者比较,作者称自己的这本书是“一次删除后的还原”。
作为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成长史,《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以边缘和内在的视角,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平凡世界,一个更为广阔的“八十年代”。有论者肯定其意义,“给一个人的‘细语’或者‘私语’以‘说’的权力和机会”,同时也提出,“我们也相信这个‘八十年代’之于王尧个人精神成长的意义——‘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是王尧的高度也是他的限度,是他的远方也是他的尽头。但我们要追问的是此‘八十年代’除了立此存照的意义,在现时代真的能瓦解彼‘八十年代’吗?”


八十年代年轻人的购书阅读场景
新作《时代与肖像》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这里的“时代”已经不再局限于“八十年代”,而是延伸到了当下。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作者写道,“我有我的‘闰土’”。这个捞水草的“老四”,终身滞留在乡村,滞留在渐去渐远的农耕文明中,成为逃离农村的“我”回望过去的参照物。而十余年后,作者在《疼痛的记忆》中重新回想起一起捞水草的少年同伴,想起“余同学”,观点开始发生游移,“当时我已经知道鲁迅笔下的闰土,但我觉得我眼前的余同学不是闰土。他是谁呢?”其实,与鲁迅《故乡》里的“迅哥儿”不同,“我”并非小镇大户人家的“少爷”,如果没有凭借一己之力离开乡村,“我”可能会和“老四”一样,成为他人的“闰土”;而“余同学”和“老四”又不同,多年后,他和“我”在村头重逢,其状态与被生活重担压垮的“闰土”极具反差。作者重写乡村,重写自己的生活史和成长史,不是为了真实复现自己的少年乡村;而是在多年以后,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重新审度与乡村有关的人物、事件和记忆,调整自己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里的角度和视野,改写部分章节和论断。可以说,作者的专栏新作是突破和部分地瓦解了当初的“八十年代”。
随之而变化的是,与《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相比,“时代与肖像”专栏中的语言和情感基调开始趋于松弛、缓和。如果说旧作有着明确的叙事方向,新作则显得非常轻松,“我很少用‘乡愁’这个词,写作‘时代与肖像’也不是抒发乡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十多年前那个语词锋利、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面貌悄然隐匿了,不再强调冲突,也不再主张话语权力。而是用一种充满细节、闲谈式的文体,来叙述一段段温暖或苍凉的往事。作为一个“抒情的现实主义者”,作者赋予文本具有特殊时代气息的爱和“哀愁”。这样的“朝花夕拾”既没有眺望,也没有企图,显得细密而纯粹。
03
无论是改写,还是重写,“时代与肖像”给作者之前的非虚构写作蒙上了一层滤镜,很多年前看似真实的东西,经过时间的提纯和主体阅历的过滤,开始呈现虚拟的质感。“日常生活叙事都是对现实的一种描绘和发现,同时也是对于现实的一种重写和改造,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现实的面貌,也赋予了现实新的形态,或者说使世界呈现为新的现实。”
如果说,“时代与肖像” 是在内容的扩充和更新上部分消解了旧文本反映过往现实的客观性,“纸上的生活”专栏则直接撑破了非虚构表达的基本形式:虚构的叙述主体,以及明显超出作者日常生活边界的人与事件的叙述等等。小镇、老街、石板街、码头、石油钻井队的井架、向日葵……那些似曾相识的日常与细节,动辄在作者的“纸上”生活中出没,虚实难辨。

“尽管关于写作可以打造一个与现实平行的世界已经是陈词滥调,但我相信,许多奇迹和意外是在虚构的记忆中发生的。沉积的记忆其实是发霉的,虚构让它长出新芽甚至开花结果。”吊诡之处在于,当作者坦承文本的“虚构”性时,个人的阅读体验却径自走向了相反的结论。这或许与专栏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去故事化”的结构叙事有关。在对生活场景和真实细节的整理爬梳中,作者进行着一种复刻式的写作:其中有细枝末节,有人物,笔触温和、谨慎、克制,没有强烈的情感倾向,甚至缺少“合理想象”。作者强烈的个人叙事风格使得对于文本是否虚构的界定也变得犹疑不决。
我们在讨论“非虚构”时,始终是与“虚构”保持一种对话与联系。即便“非虚构”出于对事物或事件的忠诚而复刻了所见所闻,然而这所见所闻也是透过特定个体或群体的眼睛和耳朵来获取的。我们固然能在某一时刻用文字记录下确凿无误的颜色、声音和气味,但却无法保证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不为心灵或外在意识形态所左右,无法保证经过个人情感和思想浸润的颜色、声音和气味就是那“唯一”的“客观实在”。所以,在笔者看来,“非虚构”这一文体,大概只能是从主观上的不虚构出发,无限远离虚构,却无法抵达绝对的不虚构。

其实,对作者来说,“虚构”或“非虚构”,不在于如何界定,而在于如何选择。其近年来的小说和专栏创作,集中体现了他对于文体的自由选择和探索。一直以来,作者对于“文章”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做学术的同时,我一直心仪博大、悠久、浑厚、美丽的中国散文传统,迷恋文章。相比之下,我写文章的兴趣远高过做学术论文。因为在学院中,我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职业,但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兴趣,我深知放弃自己兴趣的痛苦,许多人现在便处于这样的痛苦之中。以现在这样分配精力的方式,我写散文随笔的数量可能会有一天超过学术论著。我常常为此兴奋不已。”在学术和创作之间,创作是他的兴趣所在。在他早期的专著《乡关何处》中,他提出了“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这一观点,多年来,作者在学术研究之外,始终坚持散文随笔的写作。在通过这一类非虚构文体自由表达世界与自我之后,作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停下来,他对于“文体自由”的追求又有了明确的方向——对于虚构文体(包括小说)的尝试与冒险。
多年来锲而不舍的创作经历,为作者的“文体自由”划分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挣脱学术桎梏,不让日常、细节、情怀等等基本的文学活性物质被条条框框所拘,实现“跨界”的自由;其次,渴望延续古老的“文章”传统,但又不囿于传统,实现“形式”的自由;再者,无论是采取何种文体形式,都要赋予每一种形式个人的思想、语言和气息,避免堕入平庸和重复的境地,实现“审美”的自由。综合以上种种,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作者的话:文体的自由对我来说不是小事。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摄图网、出版书影
1981·文学报40周年·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