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杰x包慧怡x陆大鹏:在“世界史热”的背后|译想论坛

近十年来,中国出版界出现了一股“世界史热”。在市面上,越来越多介绍世界史的优秀著作被翻译出版,并受到读者的热捧。其实,这股“世界史热”不仅体现在出版界上,也体现在学术界上。“世界史热”的成因或许与中国和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以及中国人对世界史有极大需求有关。但是,在“世界史热”的背后,“世界史”的概念或许更值得我们探讨。什么是世界史?世界史就是除本国以外世界的历史吗?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又能从世界史中得到哪些观察历史的角度?
5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共同推出第四届译想论坛(2021)的译论二“历史之镜——世界史热在中国”,我们邀请来了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包慧怡、译者陆大鹏、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蔡伟杰,与大家谈谈中国出版界的“世界史热”。以下对谈实录有所删节。
嘉宾 | 蔡伟杰、包慧怡、陆大鹏
整理 | 徐悦东

活动现场,左起:陆大鹏、包慧怡、蔡伟杰。
世界史不仅是除中国以外世界的历史
蔡伟杰: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武汉和各位谈 “世界史热在中国”。我知道陆大鹏一直在甲骨文和其他地方翻译了许多世界史著作。所以,我们想请他谈一谈他在历史翻译里面的经验。包老师不仅创作了很多诗歌,本身也做过很多文学翻译,而且她研究中世纪的欧洲文学,这其实和世界史有很大关系。我们也可以请她谈一谈文学和翻译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先来简单地讲一下这场论坛的主题,也谈一些我的想法。就在前几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邀请了复旦大学的葛兆光老师和中山大学的刘志伟老师针对“什么才是好的学术书”做了一场对谈。葛兆光特意提到,在2010年之后,整个中国出版界出现了一股“世界史热”。有许多外国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被引进到中国。我在深圳大学讲授世界史,尤其是与内亚相关的历史。我发现在学术界里,从2011年开始,教育部就把世界史提升到历史学里的一级学科,与中国史、考古学平起平坐了。所以,不仅在出版界有“世界史热”,学界、教育界也同样有“世界史热”。
2008年北京奥运后,有非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借着这个机会,很多中国人也接触到不少外国人。这是“世界史热”的大背景——中国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紧密,中国人对世界各地的历史也越来越好奇。当然,在我们讲到世界史时,总会对世界史有不同的定义。刘文敏曾经谈过,所谓的“世界史”,一般是英语“World History”的对译。但实际上,这个词在美国有着专门的用法。在1960年代之后,美国有一批学者不满于过去的历史书写方法——特别是19世纪晚期以来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所书写的历史。他们期望能够书写一种更加具有整合性的历史。
所以,他们开始写一种在时间上尺度更大、在定义上强调跨区域、跨时代互相连接的历史。比如,有人研究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兴起或西方世界崛起的原因。历史学家开始谈论这种具有世界性尺度的问题。他们所强调的实际上是更加具有整合性的历史,而不只是本国以外世界的历史。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的学科分类体系深受苏联影响,世界史更像是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历史。我观察到,在中国大陆早期的一些世界史课里,很少会提中国在世界史里的位置或者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连接。用刘文敏老师的话说,中国大陆的世界史和美国强调整合性的“World History”不一样,更好的翻译应该是“History of the World”,即是中国以外世界的历史。但是,中国在世界史里的地位又很重要。
如今,前面讲到的这两种世界史取向在中国都有引进。我记得甲骨文出过《伟大的海》,它就是以海洋作为全球性的连接点来写全球史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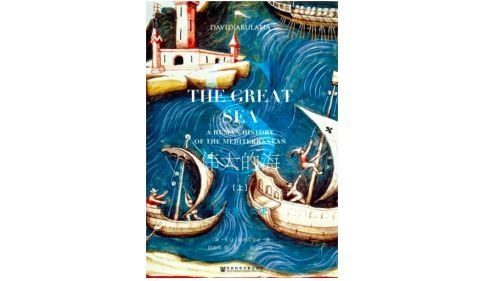
《伟大的海》,[英]大卫 阿布拉菲亚著,徐家玲译,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7月。
陆大鹏:这个作者就是剑桥大学的戴维·阿布拉菲亚,他写了一本不限于地中海,而限于四大洋的新书,有更宏观的视角。
蔡伟杰:这书的中国大陆版译者徐家玲是非常权威的专家。我认识陆老师是因为《地中海史诗三部曲》中的《1453》,这书和我的研究比较相似。我感觉陆老师译的英国、德国的历史,如《条顿骑士团》,不是像我前面讲的具有连接性质的世界史,而更加像区域性的世界史,但这也很重要。在中国,这两种历史是要齐头并进地引荐的。我们请陆老师来谈一谈,作为专业译者,你所观察到的译著有什么特色?你自己在翻译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有没有给其他从业者的一些建议?
陆大鹏:感谢伟杰老师的介绍。我本身是学英国文学的,只是历史的业余爱好者。我是靠爱来做翻译的。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19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世界史概念会说成“Global History”,也就是全球史?
蔡伟杰: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谈的。
对于原创性的无限推崇是特别现代的东西
陆大鹏:那我就不班门弄斧了。我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外国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外国文学,后来我一直对西方文学和历史感兴趣。在我上大学,学的是英国文学。因为我比较失败,我就到出版社工作。我并不是说只要失败就可以到出版社工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的个人经历。
一方面,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我就做一些翻译工作。这样我能找到一门自己不讨厌又能挣钱的工作;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我对得到一些读者朋友的认可还是感到蛮高兴的。所以,我还在继续翻译工作,其中的很多技术细节也不足为外人道也。
很巧,包老师是学者、诗人,也是翻译家;伟杰老师既有学术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做翻译方面的工作。其实我很好奇,你们两位都有不同的身份。作为学者,你们要强调自己的原创性,一定要有新发现、新创见。在我们一般人的理解里,翻译工作就像月亮一样,是在借助太阳的光芒,译者是不会有太多原创性的。我几乎从来没有做过具有原创性的工作。我很好奇,你们两位学者对原创性以及翻译工作中的派生或衍生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在请两位老师回答之前,我想先请教包慧怡老师。包老师是中古英语文学的专家,我自己也蛮喜欢读这些文学作品的。以前,我读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及相关作品时,我记得和乔叟被差不多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称他为“这个时代最伟大、了不起的翻译家”。我读到这句时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乔叟是大诗人、文学家,说他是翻译家是不是在黑他,在骂他?

陆大鹏
乔叟翻译了中世纪的畅销哲学书《哲学的慰藉》,还翻译过法国的《玫瑰传奇》。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也有几个故事基本参考或借鉴了薄伽丘的《十日谈》。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格外强调他是翻译家,是不是讽刺他没有原创性?是不是因为他的很多材料都是从别人的书里来的?
包慧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对于原创性无限推崇的迷思是特别现代的东西。中世纪的人是恰恰相反的。我们知道英语的作者“Author”这词来自拉丁文的“Auctor”。这个词与自为、自治有关。
中世纪的文化是基于手抄本的古书传统文化。当时没有印刷书,也没有今天的播客,更没有电台。所以,得手抄本者得天下。制作手抄本是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因为这需要动物的羊皮、牛皮。几十个僧侣在缮写室里合作,一天的进展只有一点点。做一本手抄本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就形成了对古书的崇拜。

乔叟
乔叟在他不太为人所熟的《梦幻诗》里说“总之,我得到一切都来自于Old Book”,他写的《The Legend of Good Women》(《女杰传》)的开头说:我不过是个拾穗人,前人的译本和他们的著作翻开在我面前,我不过是在里面寻找一些东西。我们经常会说,乔叟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作者和第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作者,所以我们不能只从字面上听乔叟的话。从字面上来看,他拥有中世纪作家典型的自谦——原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声称我的一切来自于古书,如果这本书来自三本书的结晶,那就很好了,如果是来自300本书的结晶,那就更好了。
在中世纪,你要保证你写的书具有权威性,不要说这本书是我写的,因为读者会觉得,你写的有什么了不起?你是谁?所以,你要说你写的书里是在多少古书的传统下写出来的,那样的话读者读这本书的性价比就没有问题。在这一点上乔叟也遵循了传统——我们称之为“假谦卑”的传统。诗歌也有这样的传统,很多诗人会说自己“没有办法描述接下来见到的美景”,但接下来他就描述了300行。
回到陆老师的问题。中世纪的人们对于作者和译者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划分。这最早能追溯到西方翻译家的守护神圣哲罗姆(Saint Jerome),他是四大拉丁教父之一。我们很容易辨识他,他戴着红色斗笠一样的主教帽,还带了一头狮子。那狮子在他在沙漠里翻译《圣经》的时候,曾经为他拔过爪子。圣哲罗姆是第一个把希腊文和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通行本《圣经》的人,该《圣经》的中文名叫《武加大圣经》(Vulgate)。这是中世纪那1000年中,西方人使用最多的一本圣经。因此,我们叫他“翻译家的守护圣徒”。他的圣人日9月30日现定为“国际翻译家日”。
圣哲罗姆是创、艺、演三位一体的工作者。他是优秀的希伯来语和通俗希腊文学者、训诂者、语言学家;他熟悉很多辨经学、释经学的传统,也是一位神学家。这都是他身为学者的素养。他本人在皈依宗教之前又是文艺青年,很喜欢写诗。他爱着维吉尔,也喜欢奥维德。他写了很多异教爱情诗,在一心翻译《圣经》后,因为过的时间太长,他就不太提起以前的诗,也不再继续写了。
他在创作上的实践给予了他非常生动的语言表达,这让他翻译的通行本《圣经》能够通用1000年。所以,他既是作家又是译者,还是学者。而且,他并不觉得这是需要拿出来说的事情。其实,在中世纪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里,即使每个人的侧重点可能不太一样,但像阿奎纳、达尔伯特,还有但丁,乔叟等人,都是在作家、译者和学者三个领域里同时工作的。
乔叟编撰自己作品的时候,他在一首短诗里面骂他的誊抄工。他的誊抄工叫亚当,他说:亚当,你不好好誊抄我的《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和《波伊提乌斯》——一本是他的著作,一本是他的译作。他诅咒他的誊抄工:你再不好好誊,我就诅咒你美丽的头发下生出头皮癣。我们可以想象,他骂亚当,因为亚当错得太多了,导致他不得不又刮又擦。乔叟明明是作家,却不得不替他底下的抄写员返工,这本身是一种特权,因为大部分作家是雇不起抄写员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乔叟没有区分他的译作和他的著作,他甚至把他的著作摆在了译作前面,好像它们是一对双生子一样,让他带着同样的爱怜、爱惜的护犊子口气去说话。他们当时没有对原创性的迷思。
另外,中世纪的书本身是流动的建筑。我们说羊皮纸是一刀纸,很多书就是几刀纸组成“folio”。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抄本都是被反复装订过的。比如,我拿着这个抄本,觉得内容会比那本更合适,我就会把它拆下来,重新订个封面把它们订在一起。当时,书并不存在着印刷术所赋予的固定性,上一本书在哪里结束了,下一本书就在哪里开始。书本身就处于流动的状况里。

包慧怡
在这种情况下,你强调原创性也没有用,因为你是控制不了文本的。一般来说,手抄本的旁边会写有页缘话,这些话很有趣。抄写者会在上面说:“天气冷,工资少,面包硬”,还有“圣母保佑我,这一天终于结束了”之类的话。我们可以在页缘看到很多鲜活的东西,比如画着很多狒狒、小丑、蜗牛、怪兽。更有趣的是,他们还有评注的传统。比如,手抄本里写:“奥古斯丁说过……”旁边就会有人很调皮地画一只手或奥古斯丁的Q版图像,然后在下面写“我从来没有写过这句话”。手抄本中心的文本不断地被页缘搔痒、搁置、解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没有办法声称自己就是上帝。作者要做好准备,因为羊皮会朽化,抄本是敞开的,不断会有人加入这个共同成为作者的过程中。
我们今天说一个作家没有原创性是一种很大的冒犯。我们说一个作家抄袭,更是不得了的指控。我们不能说中世纪的作家抄袭,因为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把一个人封为神,重要的是在文化总体不断地扩容状况下,把知识不断地流传下去。我觉得,这里面有让人安心的事情。个体可以放松一点,不那么在意自己的作者主权,这何尝不是一种解放。当然,我也意识到,在今天这样是不太可行的。
陆大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世纪对原创性的迷思不像今天这么执著。这是否意味着从印刷术开始之后,人们可以比较便宜地大规模复制书籍后,原创性就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这是否会和印刷术有关系?
包慧怡:我觉得这有一定关系的。在古腾堡发明西方近代活字印刷术后的30多年,英国有个叫威廉·卡波斯顿的精明商人,在伦敦成立了第一个印刷所。他当时选择印刷的两个文本是他精心挑选的——一个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这也是乔叟成为“英国文学之父”的一个很硬的理由。乔叟的本子足够多,也有足够多的人读它;另外他还选择了《亚瑟王之死》——15世纪晚期,一个叫托马斯·马洛礼的人写了这本书。这两个选择都是非常讨巧的,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在法国、意大利漫游的人,他很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书。
但我觉得,他选这两本书的原因之一是这两本书都有可考的作者。从此以后,大家有了一个可以在历史当中进行谈论的作者,大家可以围绕作者生平展开讨论。从此,大家把作者从混沌当中打捞了出来。
这个事情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在文艺复兴的早期现代,莎士比亚也没有非常执著于署名。在生前,他的剧本是从来没有出版过的。BBC在 2016年的轻喜剧《鹊起之鸦》(Upstart Crow)里黑莎士比亚说:剧本有什么了不起,演员腥臭的呼吸赋予了它们生命,下一阵风就会把它们吹走。莎士比亚的剧本应该是历史上最经典的剧本,他却没有成为经典的意识。
在莎士比亚死了七年之后,他的两个友人帮他出第一对台本。他自己生前出版的书是诗集。他觉得,诗是可以放心地把它归入威廉·莎士比亚名字之下的。他确实把诗看得比较重要。莎士比亚是特别现实的人,在1592-1594年,伦敦闹瘟疫,他写不了剧本,而他又有三个孩子和一个老婆要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写诗献给一个美少年——也是他的庇护人南安普顿伯爵。既然写诗献给伯爵,那就必须要署名了。我以最现实的恶意去揣测这个事情,当然,这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莎士比亚真的有一种对自己才华很不在意的心态。在要拿钱的情况下,他才署名。作者的主体性应该放在印刷史以及经济文化物体载体中去研究,这比我们在这儿主观臆测可能会更有意义一些,因为这可能涉及很多领域。
全球史和世界史有什么区别?
陆大鹏:在活动开始之前,我的领导让我多给甲骨文做广告,但说了半天和甲骨文好像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得赶紧拉回来。蔡老师,刚才我问你关于World History和Global History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我们现在说的Global History和你说的1960年代以来美国的World History——跨越民族国家疆界,强调世界整合性的概念——是一个概念吗?
蔡伟杰:Global History是比较新近的词。实际上,它的用法在各个地方都不同。在羽田正的新书《全球化与世界史》里,羽田正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但他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全球史的。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讲Global History。
关于全球史的写法有很多种。一种是刚刚讲的,世界史不是讲自身以外的世界史,而要讲的有连接的或有整合性的历史。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全球史和1960年以来,尤其在美国逐渐新兴的世界史是比较类似的。
有人会觉得,全球史要写的是世界全球化,即“Globalization”之后的历史。这种历史只能是1492年之后的历史,因为那时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旧大陆开始与新大陆有比较制度性的、规律性的交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只能在1492年后才有办法出现。这样的Global History变得更加狭义。在1492年之前,各个世界是比较隔绝的,至少在新旧大陆之间是隔绝的。这样的历史不足以称为Global History。
这两种全球史都有人在谈论。我前面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就和Global History更适合一起谈。因为这是全球史的脉络。羽田正在书里还回应了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写的《全球史是什么》的观点。这本书最早出版的是德文版,后来又出版了英文版。英文版出的时间比较晚,他做大幅的增订,因为有人针对康拉德提出的所谓“全球史”或者“全球史”的做法提出了一些看法。
全球史可以怎么做?康拉德或奥尔森会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些特定的东西去谈。比如,有一些讲法是,我们可以从“物质”出发去谈,“物是连接人类的一种方式”,人通过交换物件或者使用东西。
陆大鹏:就像最近很火的《棉花帝国》是吧?

《棉花帝国》,[美]斯文·贝克特著,徐轶杰/杨燕译,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3月。
蔡伟杰:对,我们可以挖掘棉花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当中的历史,并把它放到这个框架里来谈。
还有一种可以谈的方向是帝国。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帝国”是长期存在的政治形式。甲骨文也翻译过各帝国专门的历史。具有比较性框架的书有《世界帝国史》以及最近的《历史上的大帝国》。帝国是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形式。
另外,还有比较大的取向,比如《伟大的海》就用海洋来书写历史。除此之外,还有《横渡孟加拉湾》、《印度洋史》这样的写法。还有的书是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出发来写历史,比如《第五次开始》。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拉到600万年,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经历过哪几次重大的发展节点,比如技术发展。我们可以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连接上其他问题。在古代史领域,沙伊德尔在《不平等社会》里就是这样做的。他研究不平等在各个文明里是怎样出现的,并研究为什么不平等会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情况。回到甲骨文出版的书,奥斯特哈默尔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就非常宏大地谈19世纪为什么很重要,这是以全球史的角度去书写时代的写法。全球史或者世界史有很多种写法,大家一直在探索怎样写比较适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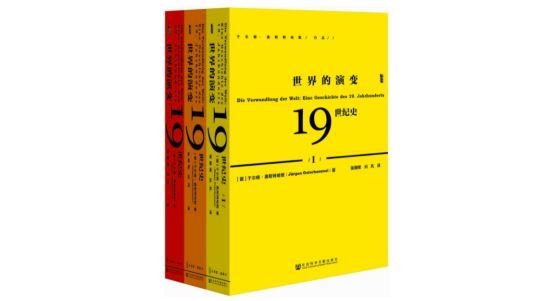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德]尤尔根·奥斯特哈默尔著,强朝晖/刘风译,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
民族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时间也就几百年。民族国家是相对来说比较新颖的政治形式。如果我们用帝国作为时间单位,时间尺度就可以拉到至少两三千年。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时间尺度甚至能拉到600万年。
写大历史的作者会从150亿年前宇宙大爆炸一直写到今天的人类。时间尺度不同,重要的东西也不同。对于民族国家或者现在的世界来说,“二战”“一战”很重要。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到150亿年之间,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我们一直在探索,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拿来作为史料,或者说什么样的学科可以拿来探索。
所以,一位历史学者如果要撰写这样的著作,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准备是要选好角度。你要选择有意义的角度,这个角度是能够帮助你解释想要处理的主题,而且还能够连接起来很多不同的现象。这是做历史研究先要做好的准备。根据你要用到的技能,你再去学习这样的技能。比如,若你要处理语言文字的材料,你就要学习相关的语言。但如果你做史前史,语言训练就不是那么重要,但你需要去辨别这根骨头是人的还是什么动物的。在有了选择之后,我们再去做相应的准备。这是现在学者面对全球史挑战时,应该具备的素养和认知。
反驳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书写,会不会矫枉过正?
陆大鹏:相比之下,以前那种传统的强调政治,尤其是外交的历史写作都显得非常简单了。
顺便借这个话题再请教蔡老师一个问题:我自己蛮喜欢读羽田正的书。奥斯特哈默尔、麦克尼尔的很多书我也读过一些。我的直观感受是,全球史写作比较强调反西方中心、去西方中心,格外强调西方以外的世界——强调美洲、非洲、亚洲。以前,传统史学会认为西方很重要,现在好像反过来了,他们格外强调西方以外的世界。比如,我刚看了约翰·达尔文写的《帖木儿之后》,那本书格外的强调,在西方大航海时代崛起的同时,东方的明清、奥斯曼帝国、伊朗都有很好的发展。作者会格外强调西方以外的因素。这是在反驳过去的西方中心论,但这会不会有矫枉过正的危险?
蔡伟杰:对我来说,这里面没有什么矫枉过正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如果真的矫枉过正的话,就会有新的东西来处理这个问题。你刚才说的《帖木儿之后》,该书认为在西方兴起而东方并没有衰落,这的确是一种处理方式。
另一种处理方式是,西方的崛起实际上是偶然的情况。黄中宪翻译的《大分流》说,西方和东方的历史发展轨迹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分流,实际上是历史的偶然。特别是,作者强调英国的殖民行为,英国人发现了原料和新市场,突破了原本英国的限制,所以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偶然,西方不是一定会变成这样的。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都可以更具体地去看,西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包慧怡:两位老师是从史学的反思去看待这个问题的,确实是这样。从历史写作的癖好和审美的本能来说,我自己从最古早的、最原初的历史写作里就可以看出西方对东方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有很多矛盾在里面。
我们拿中世纪古早地图来说,他们T-O型的地图将东方定位为最高。我们现在的地图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T-O型的地图是圆形的,T是地中海的三大水系,外面是一个想象中的外环海。地图的最高点是东方,拉丁文写作oriens,因此在英文里orient还有定位的意思。
西方人认为,东方是人类历史开始的地方,是伊甸园所在的地方,也是最终基督审判人类,时间的开始和终结的地方。他们心中终极的精神首都耶路撒冷也属于东方的范畴。所以,在他们的地图上,圆心是耶路撒冷,有了这个点,这个世界才可以被化解,才可以被铺展开来。
他们一直把东方作为精神上的终极首都,又认为那是物质上富庶丰硕之地。对早期中世纪人来说,他们的历史和文学没有那么泾渭分明,history和story往往在一起的,讲得好的story就成了history,或者说history是通过 story来记录的。历史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10世纪有一本古英语书叫《东方奇谈》,它里面有的是真实的成分,比如巴比伦等一些地方的记载。但它在面对那些位于亚洲的东方文明城市显得很矛盾,它认为那些城市是财富之地——这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东方有着文化和物质上的双重迷恋,还有漫游式的向往——同时,它又会把财富之城跟七宗罪里的傲慢、骄傲、贪婪联系在一起,这些王国的财富和他们的堕落在一起。
与此同时,对中世纪的人来说,文化上的东方还包括了处于欧洲南方的非洲。比如,《东方奇谈》里有一半在写非洲城市。同样是东方,其内部也是有阶级的。西方人对东方城市的呈现显得高大上,却把非洲描写成群魔乱舞的怪兽出没之地:狗头人、野猪怪,还有那种头长在肚子上,我们叫做刑天的人。他们认为那种人在东方的大地上漫游。他们失去了信仰,因为他们内心扭曲,所以其外在也被扭曲。
在人类基因里,人们既想要肯定本地的家园,同时对他乡、别处、他者始终有着完全不可获知的向往且畏惧。对西方来说,东方是他们异域恐惧症集中爆发的地方,同时又是他们内心深处或想象力朝圣的终点。所以,若去掉《荷马史诗》中所有关于东方的描述,《荷马史诗》该多么枯淡无味。
对这一点来说,有时候世界史是一个概念。有些学者或史学家会说,世界主义这个词(“cosmopolitanism”)并不是只指康德以后的世界主义。他们会说,在一些早期的古早文本里,虽然大家不会谈世界主义这种词,但也有着世界主义。
《贝尔武夫》中出现了23种不同的族裔。虽然它是古英文写的历史,但它竟然没有出现英国人。它写了斯堪的纳维亚的丹麦人、瑞典人等族裔,以及这些不同的地方之间英雄的来往。他们认为这是英语文学最早的文本。我们今天肯定不会称其为世界史,但他们认为,其实这就体现了很多世界史的视角。因为这里面呈现出那时的人们是如何体现他乡的,还有那时的人们认为自己是谁的看法、对怪兽的观点、对于异域他乡和遥远东方城市的看法。与其说《贝尔武夫》如何忠诚地描写了东方,不如说它体现了西方人自己的焦虑、恐惧和希望。
如果把世界史的线拉得更长一点,我们可以把各种泛历史文本都纳入到考虑范围。这可能不是真历史学科的“history”,但还存在着很多游离在历史和虚构间的文本。这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的一部分。
从世界史去看中国,也能刷新我们对中国史的认知
观众:请问蔡老师,年鉴学派对历史学的看法和美国全球史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区别?
蔡伟杰:实际上,年鉴学派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年鉴学派一直在变动。他们一开始认为,过去的历史研究过于强调政治,因此,他们要从经济或者社会的角度来写历史,而且他们强调,他们要写一种所谓的整体史。这种写法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历史写作本身的反思。
以刚才说的罗杰·克劳利为例子,他所写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我们刚才讲的全球史观点的一种应用。实际上,地中海本身不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地方,它是一个区域。学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18、19世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书写的历史局限性,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历史写作去描述更全面的人类经验。
后来,美国的全球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年鉴史学的影响,只是他们走得更远。年鉴学派也受到全球史的影响。年鉴学派也一直在变。在第三代的时候,很多人开始研究心态史,后来他们的做法更加多元,他们将环境史也都统统放进来了。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互相影响的。
观众:蔡老师您好!我是多米尼克·利芬的《Empire :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的译者。我很想听到您怎么评价这本书?这本书非常契合今天三位老师的分享,它把一个国家的历史放在世界背景下,用对比的角度来研究。作者从俄罗斯16世纪中期崛起,一直写到苏联解体,因为他认为,俄罗斯帝国历史是不可分裂的。这个作者认为帝国不必然会被民族国家所取代。他写这本书的背景是2000年,当时正是欧盟兴盛的时候,一些小的国家可能会联合形成经济共同体,但这本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您认为他的观点还适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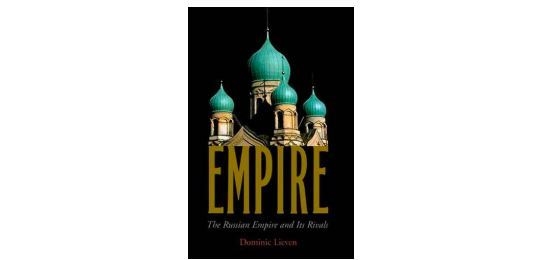
《Empire :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美]多米尼克·利芬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蔡伟杰:这本书有机会被翻译到中文世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刚才讲,全球史的视角里有几种取向,物、区域、时代、不同学科,甚至大历史,还有环境,还包括您刚才讲的帝国,帝国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即便在今天以民族国家为主的世界里,帝国还是存在的。
我们该怎样去定义帝国?早期罗马帝国很明显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皇帝死了以后由他儿子继位。罗马的皇帝在很多时候是选出来的。美国的总统也是选出来的。所以,并不是说私相授受才是帝国。帝国更多是权力差异的政治结果。帝国有文明的中心,底下有多元的民族,帝国中心和底下的臣民存在着一个接续性差异。
在这种定义下,帝国史是很有生命力的写作。刚刚你提到的这本书就是一种比较帝国的写作方法。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作者好像觉得,只有西方的帝国才是帝国,他认为最标准的帝国是罗马帝国。而且,他所列举的国家或多或少和罗马有关。奥斯曼帝国推翻了东罗马帝国。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罗斯认为自己是罗马的继承人,是东正教的保护者。俄罗斯帝国的标志是双头鹰,两个头看着不同的方向,一边看着西边,另外一个头在看东边。实际上俄罗斯就是横跨欧亚的帝国,它的标识可以看出来它的帝国性质。
这个是这本书的好处,也是这本书的局限所在。作者没有将相对更广阔的帝国,比如亚洲甚至美洲的帝国,纳入到比较的范畴里面来。这也很正常,因为他的关注点是俄罗斯。所以,每一个作者在选择写作目标和受众时是有取舍的,他不可能在一本书里什么都写。我还是非常期待这本书的出版。
观众:蔡老师,您怎样看待新清史在国内引起的争议?您不想回答也没关系。
蔡伟杰:感谢您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放在帝国史的脉络里讲。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清朝是不是一个帝国?这个问题有时候不能特别开放地进行讨论。一提起帝国大家会想到帝国主义。大家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受害者,中国本身不是帝国,而是被侵略的国家。或者说,中国不是西方式的,走资本主义向外扩张,为经济利益向外找寻原料和倾销产品的市场,通过经济剥削殖民地的帝国。但实际上,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西方有类似的地方。中国不可能跟西方一模一样。我们所讲到的西方帝国,他们彼此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和英国不一样,但中国和俄罗斯就非常类似。俄罗斯帝国往中亚扩张不完全是出自经济利益。很多时候,俄罗斯人会说,中亚的游牧民族持续骚扰俄罗斯边疆,他们还会掠夺俄罗斯人当奴隶。清代早期还存在着非常多的奴隶贸易。奴隶贸易很早就在中亚和欧洲存在了。所以,俄罗斯人使用了这种说法,这也是他们扩张的借口。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自己是自卫。中国学者也说,中国向内亚扩张也是出于自卫。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和俄罗斯向内亚扩张的动机就很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