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新锐作家萨曼塔·施维伯林:游走于幻想与现实之间

步入萨曼塔·施维伯林(Samanta Schweblin)构筑的文学世界有如堕入一场亦真亦幻的梦魇。在这位阿根廷新锐作家身上不难窥见胡利奥·科塔萨尔、比奥伊·卡萨雷斯、奥拉西奥·基罗加等拉美文学巨匠的笔锋,她以“幻想式风格”延续了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文学传统,在写作技法上又师从弗兰兹·卡夫卡、弗兰纳里·奥康纳、约翰·契佛等欧美作家,并注入她个人对生活、创作的观察与思考,铸就了在拉美大陆乃至世界文坛独树一帜的“施维伯林式”风格。“她手中挥舞的带子很细很轻,其文学分量却很重”,在短篇小说集《吃鸟的女孩》(Pájaros en la boca,2009)的寥寥数页间,萨曼塔·施维伯林用她集冷峻、诡谲和癫狂于一身的文字,引领读者穿梭于现实和奇幻的渐近线之间。

萨曼塔·施维伯林
坠入“短叙事”的迷宫
萨曼塔·施维伯林于1978年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旅居墨西哥、意大利和中国,现定居柏林。她的作品不以数量取胜,但自出版以来屡获重量级奖项,在全球被翻译成超过20种语言。2001年,其处女短篇小说集《骚动的核心》便赢得当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奖”一等奖;《吃鸟的女孩》则被授予2008年度“美洲之家奖”;《七座空房子》获“里维拉·德尔·杜埃罗短篇小说国际奖”,其中短篇小说《没有运气的男人》荣膺2012年度“胡安·鲁尔福国际短篇小说奖”。施维伯林业已成为阿根廷当代青年作家中的领军人物,被巴尔加斯·略萨等文学大家视作西班牙语文学最具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声音,令人震惊,荒诞,自信。”2010年,《格兰塔》以如上评语将其归入22位“最佳西班牙语青年小说家”之列;2017年,施维伯林又入选第二代“波哥大39人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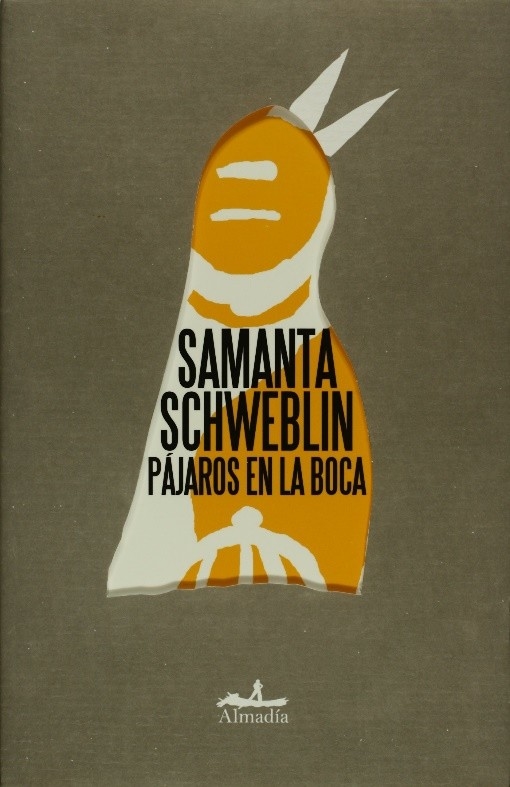
2010年西班牙语版《吃鸟的女孩》
萨曼塔·施维伯林以短篇小说写作见长,这一比起长篇而言不甚受出版商青睐的文体是施维伯林文学生涯的起点与初衷,亦是她笔耕不辍的动力所在。不乏文学编辑将短篇叙事视作打造长篇前的过渡或“练手”,施维伯林对此并不苟同。对于这位阿根廷当代作家而言,内容的厚度远甚于长度,灵感的恣意翻跃并不受制于场地的辽阔与否。正如王安忆在“短经典”总序中所言,“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收录于《吃鸟的女孩》中的每一则故事虽篇幅短小,却灵动、饱满,富有生命力。汪曾祺亦曾有一个精妙比喻:长篇如“蟒蛇”,短篇像“蚯蚓”——后者虽小,却善于松土。萨曼塔·施维伯林笔下富有张力的一则则短篇故事正如灵活轻盈的蚯蚓,在不经意的时刻侵蚀、松动了庸常,令读者在措手不及间坠入一座座深不可测的文学迷宫。
潜伏于日常角落的恐怖
生吞活鸟的少女转过头,她面容羞赧,眼神惊恐,嘴角与下巴血迹斑斑;怀有身孕的女人千方百计寻求疗法延迟生产,最终“轻柔地把她吐了出来”;求子心切的夫妇每晚雷打不动地在荒原上举行诡秘仪式,他们喜出望外地得知另一对与自己境况相似的夫妻已有所得,却无从揭晓其“猎物”的真面目;在校门口等待女儿放学的父亲碾死一只蝴蝶,随即成群结队、色彩各异的蝴蝶如旋风般席卷而来;男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用乱棍打死一条狗,转而发现自己身陷被狗群吞噬的险境……这一则则短小精悍、扣人心悬的故事构成萨曼塔·施维伯林的短篇小说集《吃鸟的女孩》。

《吃鸟的女孩》
《吃鸟的女孩》全书弥漫着一种哥特式的暗黑、诡诞氛围,但诚如作家本人所言,“在我的小说中寻找幽灵、女巫和平行世界的读者可能会大失所望。”施维伯林书写的“恐怖”并不耽迷于传统惊悚小说中充斥的各色血腥、灵异和科幻元素,而更注重挖掘精细入微的日常琐碎中那些怪异的、疯狂的、转瞬即逝的画面,执着于探索都市人际关系中的灰暗地带。她笔下的故事不是“猛火煮”,也非“慢火温”:小说往往始于日常一幕,以不疾不徐的调子向读者娓娓道来,却又悄无声息地在某一时刻将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活碎片拉至令人匪夷所思的荒诞场景,一如《伊尔曼》中再寻常不过的乡间酒馆忽然间成为一桩离奇“凶杀案”的案发现场;《地下》里温馨的小酒吧与荒芜的旷野、“我”身边讲故事的老人与故事中人间蒸发的挖矿孩童们如重叠的光影,难以辨析。
家庭尤其是萨曼塔·施维伯林笔触和目光所及的焦点,家庭关系及其中包含的两性和代际关系是萨曼塔·施维伯林作品偏爱的取景位,她从个人视角重新审视了家庭场域这一被狭隘文学观念视作“女性写作”的专属范畴,并由家庭望向社会和时代,坦言“家庭,一如其他社会单元,既可以塑造一个个体,亦可造成人性的畸变。”施维伯林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家庭生活场景中剥离出超乎寻常的、危险的、吊诡的元素,她所构筑的家庭空间不再是私密的避风港、温情的保护伞,而摇身一变成为充斥着死亡气息和潜在威胁的陌生荒原,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如果说一名优秀写作者往往是“雌雄同体”,萨曼塔·施维伯林则凭借其简洁却有力的笔触,天然而非刻意地颠覆了对于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的刻板印象。
平滑表象下的多维解读
施维伯林的文字精炼、平实,不动声色的叙述语调却呈现出力透纸背、直抵人心的感染力。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电影系的求学经历或许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施维伯林日后的文学创作,她直白的行文富有极强的视觉性和画面感,充满戏剧张力。“我的第一幅艺术创作。我细致地描摹了塞西莉娅惊恐的双眼,额头上一滴滴冒出的冷汗,她眼前的粗糙不平的地面,我的手指紧紧揪住她的头皮。之后,鲜血四溅。”《以头撞地》中看似轻描淡写的寥寥几笔与背后渗透的粗粝似斧的暴力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短篇小说的艺术张力。
萨曼塔·施维伯林对小说人物的心理细节着墨不多,却始终在与故事外的读者进行一场微妙的心理博弈:每当你屏气凝神,陷入阅读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不可自拔时,小说却在任一时刻戛然而止。“我们必须减速。这样下去我们可能会撞死某只正要横穿马路的野兽。这时我想到,也许其中会有那一个:属于我们的那个。但保尔依然猛踩油门,从他充满恐惧的眼神中,我看出他也想到了这种可能。”《荒原上》自始至终未曾揭开“属于我们的那个”的真面目,又或许故事的另一半早已写在读者心中。施维伯林仿佛以这种方式发出邀约,请读者根据自身的理解与期待续上这根断了的弦。诚如作家坦言,怪诞、不安与暴力并非她的写作预设,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故事结束后反注在读者身上的恐惧。
小说中的多处留白与富有延展性的意象并非施维伯林故弄玄虚以招徕读者的噱头,而蕴含着更深刻的精神内核:读者对于小说中各类象征的解读实则是其内心世界的投射,令恐惧滋生的邪恶与危险的土壤从来不来自于外界,而深深埋伏于每一位阅读者的脑海之中。“测试的内容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用棍子打死一条狗。是为了看看你有没有胆量日后来些更狠的。”《杀死一条狗》中对动物无缘由的虐杀不免令人回溯那段阿根廷难以释怀与愈合的创伤记忆;“而妈妈则回敬他说,既然爸爸跟他的朋友过得这么惬意,她又为何不能跟圣诞老人做朋友呢?”又有多少同床异梦的伴侣在《圣诞老人上门来》隐晦的字里行间窥见自己的影子。在看似平滑无隙的表象下,写作者与阅读者悄然达成一种难以名状的默契。
游走在现实与幻梦间
萨曼塔·施维伯林这位阿根廷文坛新锐的作品素来以奇幻色彩浓重著称,但她拒绝一切标签化的刻板印象,对于自己所书写的“奇幻”持有独到见解,其小说中一系列离奇古怪的元素的运用亦极富个人特色。作家本人曾在访谈中提及她所欣赏的“魔幻”,即她从阿根廷文学传统中继承的一种区别于魔幻现实主义、具备可能性与可接近性的“另类”奇幻。施维伯林不止一次强调,她笔下的怪诞事件、主人公陷入的极端境地看似是小说家异想天开的产物,但绝非不着边际、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具备切实发生的可能性——抑或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悄然发生在我们所处的现实维度,抑或潜伏于内心某一处隐秘的角落、植根于潜意识之中。这条幻想与现实的渐近线便是萨曼塔·施维伯林一贯以来的写作兴趣所在,也是她期望通过其作品引发人们思考的。在她看来,现实与幻想的界限本身便具备文化属性,是主流文化、教育体系、社会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合力构建和界定的结果。或许正因如此,施维伯林的书中有不少关于孩童、疯子、醉汉、病人的故事,盖因在儿童世界或疯癫者的视角下,幻想和现实不再如此泾渭分明。

《营救距离》
施维伯林惯于将熟悉的地域空间陌生化,把我们身边本应亲密无间的家庭成员“非人化”,将其异化为形形色色的“他者”、“野兽”和“怪物”,他们以不为人理解的“出格”行为破坏并挑战常规和秩序,因种种“不正常”的症候而沦落至被社会文化忽视与排斥的对象,从而隐形、徘徊于主流社会之外。“我想着既然还有人吃人的现象存在,那么人吃鸟相比之下也不算那么糟。从自然学的角度来看,这比吸毒对健康的损害要小,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要隐藏这种怪癖,也比掩盖十三岁少女怀孕的丑闻要来得容易。但我确信,一直到我拉开车门的那一刻为止,我一直在喃喃自语地重复着‘她吃鸟,她吃鸟,她吃鸟……’”《吃鸟的女孩》中被离异的父母视作异类的少女终日将自己关在房间,她“从早到晚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双腿并拢,手放在膝盖上”,空洞的目光望向窗外,仿佛一只被囚禁在笼中、失去生命力的鸟儿——正如那些被她吞食的活鸟一般。如此,家庭与鸟笼、吃鸟的女孩与被吃的鸟在萨曼塔·施维伯林的笔下构成了一种颇为诡异的对应关系,这种熟悉与陌生之间的冲突和拉扯彰显了一种“暗恐”效果,令人读来如坐针毡、不寒而栗。
正如评论家丹尼尔·阿拉尔孔所言,萨曼塔·施维伯林的叙事“大胆,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美”。这位阿根廷小说家在生活与创作之间跳转,在现实与幻想的“灰色地带”之间游走,她颇具侵略性和颠覆感的写作风格及“重口味”的故事内容令不少书迷直呼过瘾,也令部分读者深感不适,但这正是萨曼塔·施维伯林眼中文学的功用和力量:以诗意的方式抵达庸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乃至熟视无睹的现实,重构文明与蛮荒、人性与兽性、理智与疯癫的界限。在文学这一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施维伯林的文字带领我们暂时抛却文明的枷锁,逃脱现实的桎梏,去贴近死亡的深渊;去触碰潜藏于内心深处却不为我们所自知的恐惧、愤怒与仇恨;去为压抑在“正常”表面下的种种“不正常”情绪——痛苦、焦虑、不满、妒忌、疯狂、欲念——提供一个宣泄口,再安然无恙地回归我们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