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和离开北京 都是为了我的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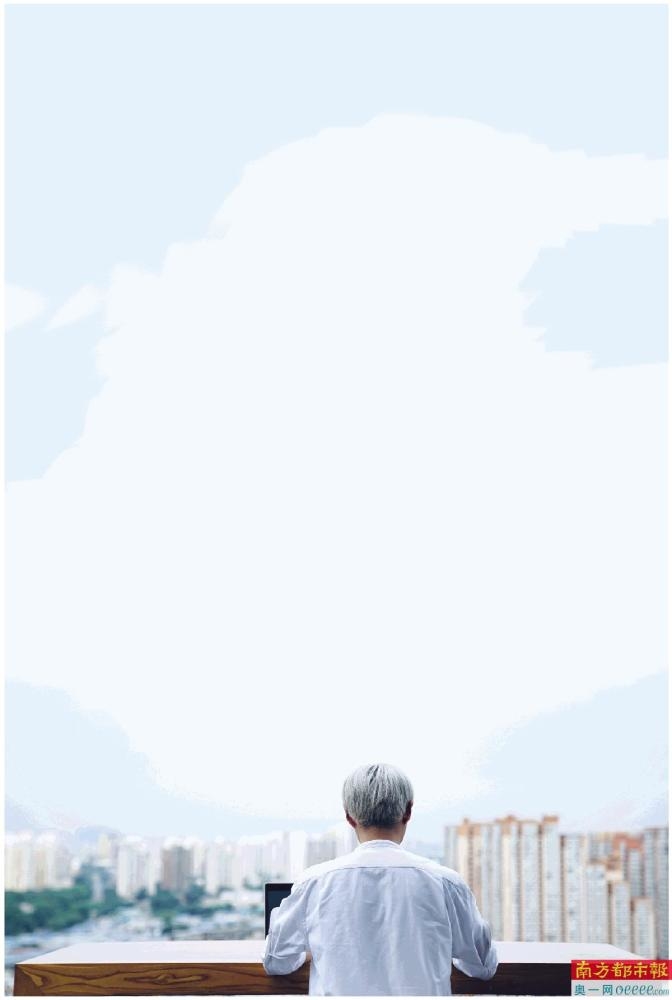
我开始北漂是在2015年夏天,背包里有两身换洗衣服,钱包装了1000块钱,一到北京就开始找工作。
一次面试完,我在马路上被一个男人拦住,问地铁站在哪儿,又说借钱坐地铁,我给了他一些零钱,他继续说他的同事撞了人,钱包被扣下了,还需要转长途去公司拿钱,想干脆向我借100块。他五十出头,面容憔悴,把驾驶证往我手里塞,并抬起巴掌扇在自己脸上,发誓赌咒。我借给了他,也没要驾驶证,只留了电话,走了一段路才回味过来:我被骗了。
那晚,我在网吧写面试稿,写完已是深夜,走出网吧抽了一根烟,回味着北京赋予我的第一次失落。此后我再未施舍过任何人。
一天要写五篇伪原创的稿子
幸运的是,我面试成功了,工作是撰稿,一天要写五篇伪原创的稿子。宿舍在一个叫崔各庄的地方,15号线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点,走出地铁口,路两边是荒野,目及之处没有超过三层的建筑,扭头眺望,还能看见光鲜通明的望京SOHO。人行道的灯影昏黄,货车撞散漫空的浑浊,三两粒灰尘融化在嘴里,我告诉老家的朋友,这就是北京的味道。
我开始喝酒,每晚都喝,为挤地铁而喝,为每天睁眼就欠公司五篇稿子而喝,为不能去别处而喝,归根到底发现这一切都能用钱解决,然后恍然,原来我竟是被钱驱使,为穷而喝。
不久后我换了工作,新公司在西二旗,三层小楼,专门留出一间当员工宿舍,里面有一张属于我的小床。我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坐在工位上干活,中午叫一份外卖,吃完眯一会儿。办公室里大多时候是安静的,大家习惯戴耳机,用打字交流。等7点一到,同事们打卡下班,我关掉与工作相关的窗口,一天过去。
某天夜里下起了大雨,一直持续到早上,同事们冒雨来到公司,脱下湿透的鞋,赤脚在地板上走,院外的月季跟竹子东歪西倒,下午3点的墙头不见熟悉的黑猫走过。到了晚上雨还没停,我望着窗外的雨忽而愕然,这样的生活竟然已经维持了10个月。时间这个概念,快慢是人的主观感觉,是每天同样的生活让大脑麻木,继而将同样的姿势、呼吸、事件折叠到一起,把记忆给压缩了。在下大雨的那个下午,我有种流泪的冲动,强烈又匆匆,我突然想吃辣的火锅,喝烈的白酒,汤锅翻滚白烟,仰脖把酒饮尽,就着落地玻璃打个电话,随便给谁,告诉他北京的雨不停地下,不停地下。
因为没有勇气面对次日的生活,我每天都会熬夜,总在凌晨后推开小屋的门,把手总发出刺耳的嘎吱声,摸索着在小床上躺下去,心脏咚咚响,铁架床都跟着震颤。多少次我都觉得要死了,可每次都还活着,活得好好的,在活下来后询问自己,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很亢奋,那么愿意去忙碌,愿意为一句话而笑。我得不到答案,便以最消极最极端的方式来应对,就是不应对。我把一切都交给时间,时间不会解决问题,但会让问题过去。
刚搬新家 总是找不到回去的路
后来公司搬家在即,我那一张床铺也没有了,我和同事跑遍了近邻公司的两条地铁线找房子,要么贵,要么小,疲累地坐在马路边上抽烟,汗水一颗颗地掉在牛仔裤上,把烟滴湿了,吸到肺里很是辛辣,觉得生活真难。后来终于在回龙观找到了间合适的,对西二旗科技园的白领来说,回龙观的房子就像是搭配薯条的番茄酱。每晚5点到8点的后厂村路上,上班族们褪去了流量的光环和KPI的压迫,骑着小电驴穿梭在宝马奔驰间,狠狠地将那些年薪百万的小资甩在身后,迅捷得犹如上班时敲打键盘的手。
刚搬新家的那段时间,我总是找不到回去的路,不是提前下车,就是坐过了站,出门买个东西还得绕个半个小区找楼牌号。搬到回龙观两个月后,时间是来北京整一年,我才能顺利地找到家门,也终于生了来北京后的第一场病,视线模糊,听力下降,清鼻涕流得跟自来水似的。
渐渐地,我对一切感到麻木。例如回家,先掏出钥匙,一把开楼道门,灯光应声而响,墙壁上被人涂鸦“我们爱面包,我们爱奶酪,我们要的是彼此相爱”;一把打开家门,进去的那一刻眼前一黑,三室两厅的房子除我外还有两户,但门都紧闭着,光从门缝里渗出来,一股冷漠的人情味儿往鼻孔里钻;最后一把,用手机照着打开自己的卧室门,屋里东西的摆放位置,和早上匆匆出门时完全吻合。弃读韩寒多年,却又发觉“三重门”这个名字取得巧妙。
我躺在床上,听见租户在卫生间打开莲蓬头,热水在管道流动的声音传到卧室,像墙壁在哭泣。那时我就知道,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需要一个清静的地方解决些什么。
回老家住进了没网的老房子
2016年的十一假期,我回到老家,母亲见到我很是高兴,她做了卤面,厨房还炖着一锅清鸡汤,这正是我在北京经常想吃的东西,可真正吃到嘴边,仿佛胃口又没那么大了。晚上,我去散步,看一切都是旧的样子,新的感受,小镇坐落在古黄河金堤以北,算是没拖GDP的后腿,居民有钱后纷纷买房学车。新区规划得也十分成功,一座座小区拔地而起,什么上海城、津都府、大理苑、南海花园……三流的房地产文案覆盖了一条又一条的街,让人不知身在何处。
回家第二天我不忍楼上装修的叨扰,去老房子那儿躲了一下午,房间里的物件都已搬走,只剩下床,还有松散的书桌和一堆旧书。我翻着那堆书,想起小时候,不知觉地睡着了,醒来天已黑了,睁着眼什么也看不到,觉得好久没有如此舒适自在过,决定立即辞职回来。我偏执地想,若一个人如果只能满足过去的自己,那么活着便毫无意义!可因为受不了一处的疲累而选择另一处的清宁,这算逃避吗?
我回到北京后,再三踌躇,冬寒凛冽时,跟公司提出了辞职。同事说她有个朋友突然消失了,再次出现时他已经在北京某寺庙出家了,问他什么感觉,朋友就说山下太乱了,感觉你也要出家似的。我还没有看得那么透,只是回家。
当初我因野心而来到北京,如今又因为在北京疲于生计,写作的野心无处安放,而告别了北京。我一个人搬进了老家的老房子,没有网络,无人做伴,听着电脑里缓存的老歌,一本书打发一天的时光。闲暇的日子里,我开始与自己对话,想象有人问我为什么离开北京,我想出的回答是:大家都急需金钱去换取自由,可金钱有限,自由更有限,我拼不过,所以选择先避一会儿。若对方接着问总不能一直这样避下去吧?我会再说:如果面对一件困难而有意义的事时退缩,那是逃离;如果面对的是力所能及却觉得煎熬的事情,选择离开很符合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再说“避”这个字眼本就不具有持久性,那只是成长路上暂时的脱靶。
回到北京扮演一个逃离的人
而后几年,我又漂泊了几个地方,四维上下,疲累无可细说。每一个地方都呆不长,转去下一个地方前,都会回到老家,偶尔也会途经北京。逃离是一颗特效药,用得次数越多,药效越稀薄,明知道终要于某一个地方扔掉药瓶,但不知道是哪里。一追寻意义,意义就不存在,一踏上路途,归处就在身后闪耀。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例如我继续写作,例如姑姑去世,例如悼念姑姑的文章,获得了一个写作奖项。活动方要根据我在北京的真实经历,拍一个短片。于是我又来到北京,不停地在镜头内走来走去,扮演一个曾经逃离的人。
拍摄期间,北京疫情暴发。一夜之间,北京进入一级戒备状态,武警封路,日料店焚毁鱼生,新闻频道日夜播报。
最后一个场景,我们来到了定福庄的快递宿舍,拍的是我在北京住上下铺的日子。院子里停了一排快递三轮车,没有人。听说刚拉走几十号人,做核酸检测。场景布置得很用心,崭新的书桌,纯色的床铺,比我当时的房间好很多。道具还带来了一只猫,不是黑色的,是只大眼睛的橘猫,它被吓坏了。
我坐在下铺打开电脑,敲打文字,摄像机对着我,服化道在画外准备,导演和监制在屋外盯着显示器。他们记录我的同时,我也在记录着他们,意义之上重叠意义,经历之后重现经历,我们互相记录,美化某个时刻,再将这一切嫁接于某个概念,等着某天被打破,或者遗忘。
作者:刘酿苦,河南滑县人,曾获2019年今日头条全国新写作大赛一等奖。








